《酷儿》剧情介绍
影片改编自威廉·S·巴勒斯的同名半自传性质小说,讲述1950年代的墨西哥城,40多岁的美国侨民William Lee(丹尼尔·克雷格 Daniel Craig 饰)身处一个小小的美国人社群,但过着独居生活。而年轻的学生Eugene Allerton(德鲁·斯塔基 Drew Starkey 饰)的到来,让Lee重新开始追求与别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一个很默瑞的圣诞节复制娇妻踮起脚尖靠近你选错亲家嫁对郎我的名字查干淖尔姑娘灵瞳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第二季第一分队第四季熟男有惑西部英雄约拿·哈克斯寻宝假期2:自然召唤圣诞树暴力成性东京单身男子谜寻隔壁的男孩伦敦呼叫阿坝一家人歼毒先锋零四年夏天八月钱潮石田和朝仓疯狂丑小鸭鬼讯号2:灵异透视地狱之轮第一季佛罗里达乐园公司可不是学校新世代逆袭篇阿拉丁神灯荣誉勋章
《酷儿》长篇影评
1 ) 观影笔记
故事简介:威尼斯电影节口碑电影。
电影讲述20世纪40年代末的墨西哥城,深陷毒瘾与过往悲剧的作家比尔·李,邂逅了神秘迷人的尤金,他被尤金深深吸引,在追求中逐渐迷失自我。
为与尤金建立更紧密联系,比尔说服其一同踏上前往亚马逊寻找致幻植物的冒险之旅,途中经历诸多奇幻与不安,最终独自被回忆与痴迷折磨,展现出爱与成瘾下人性的挣扎与自我毁灭。
观者吐槽中:应该说本片的底色是非常张扬的,观者也从没预期007绅士特工在退休后会迎来如此猛烈的假期。
丹尼尔·克雷格的演绎堪称一绝,他成功地打破了以往的形象束缚,将比尔·李这个复杂而矛盾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故事性,让观者仿佛能透过他的表演看到比尔灵魂深处的痛苦、渴望与绝望。
他不仅仅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更是在向观者展示一个真实存在于人性深处的灵魂。
德鲁·斯塔基与克雷格的对手戏也毫不逊色,他将尤金的冷漠与神秘演绎得恰到好处,与克雷格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化学反应,使得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充斥着张力和欲望。
从电影的主题深度来看,本片无疑是一次对人性深渊的勇敢探索。
影片围绕着痴迷、自我毁灭以及欲望的核心主题展开,将主角比尔·李内心深处的黑暗与挣扎赤裸裸地呈现于观者眼前。
比尔对尤金那近乎疯狂的迷恋,不仅仅是对爱情的渴望,更像是他在填补内心巨大空洞的一种尝试。
这种痴迷逐渐吞噬他的理智与生活,使他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在面对无法掌控的情感时的脆弱与无奈。
同时,电影以战后此类亚文化为背景,巧妙地处理了身份认同这一复杂议题,以一种细腻且多元的视角展现了人性中对亲密关系的普遍需求,打破了性取向作为定义人性唯一特质的刻板印象。
而致幻场景的设置更是一大亮点,它如同一场意识的冒险,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引领观者一同探寻人类感知的边界以及内心深处隐藏的真实。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禁思考,所谓的真实究竟是客观存在的世界,还是我们内心深处主观构建的幻象?
在视觉呈现方面,《酷儿》堪称一场视觉盛宴。
摄影师的镜头仿佛具有魔力,每一个画面都像是一扇通往角色内心世界的窗户。
从墨西哥城肮脏却充满生活气息的街道,到亚马逊丛林中神秘而危险的小屋,影片通过细腻的光影处理和独特的构图,营造出一种既真实又超现实的氛围。
尤其是在展现比尔的痴迷时,闪回与清醒梦的无缝切换,让观者仿佛能亲身感受到他内心的狂热与挣扎,仿佛我们也一同陷入了他那无法自拔的情感漩涡。
应该承认,本片是一部极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电影,让观者在观影的过程中不得不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恐惧和挣扎。
对于那些渴望挑战自我、追求独特电影体验的观者来说,电影无疑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
2 ) 酷儿 | 对于被爱的渴望与幻觉
期待了太久,终于看到瓜导的新作酷儿。
本文涉及剧透和纯个人解读 剧情是可以一句话总结系列。
一个叫李的美国男人在墨西哥城遇到了名为阿勒顿的青年并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可阿勒顿始终若即若离。
李邀请阿勒顿一同去南美寻找雅热(yage),据说这种植物可以增强心灵感应。
于是两人拜访在丛林中的植物学家,并共同体会了雅热的滋味……2小时15分钟的片长,观影过程不算享受。
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后劲很强的作品。
浪漫,沉迷与超现实电影其实以一种克制的方式地表达李的沉迷,对这段关系更多的是事实描写,把评价留给观众。
第一章中很浪漫的场景是李突然看到人群中一闪而过的青年男人,在摇滚乐中,命中注定的相遇。
看到他的具体某一时刻,时间好像凝固了。
并非心脏停跳,而是世界上所有人或事都在停滞中慢动作,唯独他鲜活。
李希望最好能够永远停留在那一秒。
在流速变慢的空间中,对他的喜爱,或者说痴迷无限扩大。
甚至只是凝视,思想生出一只手抚摸他心爱的男孩。
我记忆比较深的原著里曾写过李想要进入他的身体,不是取代,而是成为和融合。
随着两人关系进一步发展,来到李的公寓,音乐戛然而止。
沉默,像两人之间的氛围。
当手真实触碰在阿勒顿的腹部,沿着肋骨一路向下。
而阿勒顿的手放在他手上,看似紧握透露出紧张和隐含的拒绝,最终纠结到最后还是放手接受。
李得到了他想要的。
但对于阿勒顿没有拒绝的背后是挣扎。
阿勒顿有一种随性的性感,来源是自由。
他没有任何亲密关系,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
像是天空中美丽又灵巧的鸟,令人着迷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越是无法获得越是令人无法自拔。
他在服下雅热之后吐露心声说到I am not queer. I’m disembodied,正是他对自己酷儿身份的不认可或逃避。
原著中,李帮他赎回高昂相机的桥段被轻轻带过,只剩叫住他的那句“尤金”和男人端着相机一去不回头的背影。
那一刻我和李都从心底里知道:搞砸了。
一开始就是一场单恋,能得到片刻欢愉已值得庆幸。
非要附加上金钱的价值企图绑住他。
他本来不欠你的。
李可能也不是爱阿勒顿,更多的是对他身体的渴求。
阿勒顿对他越是冷淡疏离,给点甜头他越是想要紧紧抓住。
控制欲一向是最坏的东西。
电影对原著的改编与瓜导的个人风格前大半部分就是对原著的改编,第三章对于使用雅热后的改编。
吐出还在跳动的心脏我感觉是想说两人终于彼此实现心灵互通,而两个人肉体的融合代表两个人灵魂链接。
这种表达对我来说还是太过于超现实,以至于有些抽象了。
第四章是对李的人物形象的盖棺定论——一个疯狂且脆弱孤独的瘾君子。
自己趴在宾馆外面眼睛贴着窗户往里面看,酒店里的‘李’走向一个房间。
红色的毒蛇咬住自己的尾巴绕成无穷,眼睛里却有泪水流出来。
而床上的睡着的年轻男人项链上的金色蜈蚣活了起来,在颈间爬动。
阿勒顿拿出玻璃杯放在头上,李开枪,男人应声而倒,玻璃杯滚落。
杀死了所爱之人,他却释怀地笑。
此处可能是想要瓜导在映射原著作者William失手抢杀自己妻子的事实,李本就是作者本人精神意志的投射。
“李。
”被谁唤回远方的思绪,老态龙钟的男人蜷缩着将身体依靠在床上。
在生命走向静止的时刻,最怀念的感受,还是那晚他毒瘾发作病的很重,青年男人侧着身子主动贴紧,赤裸的腿缠上自己的。
那是一种可以假装被爱,肉体与灵魂交融的感觉。
原著小说里的我-李,给人的感觉是反感多过共情,但电影里的李让人有些怜悯,即使他对阿勒顿的痴迷是病态,但还是会让很多人在其中看到自己。
我说的当然不是毒瘾,性狂热,时代背景下对自己酷儿身份的挣扎,偶尔对自己的超常的痴迷和过失罪行的罪恶感。
而是爱上不可能的人的无力和自我厌弃,对被理解的渴望,对爱人的占有和控制欲,对孤独的恐惧。
另一处有趣的改编,把科特博士性转了,在热带丛林里女性才是一家之主反而设计的更科学。
原声太太太赞了,本片的服化道和场景布置都是非常用心,毕竟是50年代的故事,要合理又充满美感地展示时代背景并不是一件简单事。
阿勒顿和李在一起的时候,穿的衣服就是纯粹性感(也是因为Drew又高又瘦,且身材比例好)对身体线条一览无余。
李的衬衫西装看得出面料好,裁剪也很考究完全不暴露。
初登场的棉麻西服构成这个人物轻浮的初印象。
种种服饰的细节已能够侧面显示出两人的经济情况,或者说阶级身份。
选角虽不太符合我心里的原著形象,阿勒顿年龄上应该更小更瘦,毕竟多次用青春期,孩童等的相关形容词。
而李本应该更没魅力且令人无法忍受,而Daniel身材健硕且性感Drew和Daniel之间缺少的化学反应,恰好符合角色之间看似亲密却疏离的关系。
反而是豁牙墨西哥当地小伙是对的感觉。
看演员表才发现是Omar。
怎么这么帅!
缺了牙齿并不影响性感,拉丁美人独特的味道。
平常就是看起来很憨厚的傻大个,结果都和007演起床戏来了(未必是享受。
个人吐槽(题外话)再说一百遍,什么时候能停止使用直人演queer,就像不再允许出柜者试验异性恋一样?
现如今的好莱坞为首的影视行业就是出柜了约等于再也演不了异性恋,除非自己出资当导演或制片人,才能跳脱自己的queer身份。
对于有迹象的“直人”,也是秉持着疑柜从有的态度,一律打成透明柜。
但是直人似乎可以肆无忌惮地演性少数角色,甚至因牺牲大,豁得出去而被敬佩。
却从不见有人说queer演出异性恋是献身。
既然做不到就别再标榜平权
3 ) 幻影的追逐?
你恨死你自己年老,酗酒,药物成瘾。
那个年幼的男孩,他戴着眼镜,穿着和你年幼时一样的服装,宣扬你曾说坚信的理念。
“爱我吧”你说。
看似你是那个祈求者,其实你是捕食者,毕竟你更加年长,更加博学,更加富有。
你高谈阔论理论,他垂头听着,他是那么包容,他接受你的一切,他接受所有人的一切。
你不想提,但是他让你想起了母亲,你酒吧里同样是酷儿的朋友是不是提过对母亲的依恋?
于是你诱惑他,肉体交融,那股欢愉之下藏着某种错位感。
你很明白那不完全是你想要的,你只不过是想借着交叠的两片组织去追求别的些什么。
你想要更多,你的灵魂伸出一只手触碰他的脸颊,于是你去寻找那传说中可以使你们灵魂交融的死藤水。
多么失望啊,灵魂交融之后你终于意识到他是全然陌生的另一个客体。
你最终也为男孩戴上了那条千足虫的项链,为他打上客体的标签,和一开始的另一个全然陌生的男孩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自己,其他所有人不都是一具空洞的肉体吗?
毕竟这就是你可以触碰到的全部了。
生活像一条衔尾蛇,最后你又再次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
生出一只眼睛,你往你的过去看去,就如往你自己心中看去。
躺在床上,最后他也不过就是你自我意识的投影。
你不理解为什么之前苦苦追求一个幻影,呼吁着别人来给予你一个正当的理由,难道你没有爱自己的能力吗?
你恨他,你恨自己,你想爱啊,但你表达爱的途径是死亡。
他的脸被你抹杀了,但那双腿却一直缠绕着你,最后一刻,你意识到那是你自己了吗?
4 ) Queer
这部电影被低估了——它探讨了孤独、欲望、对深层精神连接的渴望,以及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的权力失衡。
我欣赏导演在呈现李的内心世界时所采用的艺术化手法,通过充满意象的闪回镜头,展现了他复杂的心理状态。
蜈蚣。
吞噬自身的蛇。
服用Yagé后灵与肉的结合。
最终,他幻想自己枪杀了爱人。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回忆起爱人曾经用脚轻触自己身体的瞬间。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当我看到主角做出那些愚蠢的举动,只为了吸引年轻恋人的注意时,我开始想象他的孤独——他渴望连接,渴望被真正理解。
他幻想着借助一种神秘的植物,与那个年轻恋人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而对方不过是在利用他,以换取自己的利益。
孤独会让人渴望连接,渴望身体的触碰。
我看到孤独如何一点点吞噬一个人。
那些从未经历过这种绝境的人,或许会轻蔑地将这部电影当作另一个“年老同性恋渴望年轻肉体”的故事。
但在我看来,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深刻的悲哀——一种关于年老性少数群体的深切悲怆。
这种悲哀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暗,而在观影的过程中,我感觉心中的积雪又厚了一层。
5 ) 如果感兴趣可以一读的背景知识
书影评: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6413357?dt_dapp=1电影短评: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6384977?dt_dapp=1因为同时看了原著和电影,现在两者已在头脑里混合,并生产加工出一部各取所长的完美版本,导致本来就不客观的评价更加不客观了。
前两天去逛了旧金山的垮掉派博物馆(The Beat Museum),专门关注了一下巴勒斯的部分,也确实获得了一些新东西。
本文为一些背景信息和解读的分享,如果对我的影评和书影评感兴趣,可以点以上两个链接阅读。
The Beat MuseumLee其实是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母姓,他甚至用这个名字出版过作品,所以Queer的主角William Lee相当于是原封不动的他自己。
这个故事,以及巴勒斯的另一本代表作Junky,其实是根据他和Lewis Marker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改编的,如果把小说和他的书信和日记并排对比的话,会发现他除了改动名字之外并没有编造太多内容。
博物馆里的巴勒斯展柜电影的开头有一幕画面是巴勒斯写给Lewis Marker的诗,描写了他(在自我视角下)一厢情愿的、绝望的爱与付出,内容如下:
To M.I gave you all I had.I got no stash left.Kick this one cold.You can't turn me on.You got a route different from mine.You can't fix me if you want to.I let it happen like I let the habit happen.I knew it would hurt.I didn't care.O.K. So you won't.So you can't.Nothing to come down with.Kick it cold.I won't be sick forever.Muscles twitch to rest.The gut unknots and turns over."I'm hungry"Some habits take your gut along on the way outLike a mushroom bullet.So I'm cured so I'm off.Where can I go alone?What I got left to take anywhere?I gave it all to you, You never wanted it.You never asked me anything.It was my idea.You say I got no grounds to complain.Maybe not. I don't know.Brought it on myself.I guess I did.I'm no accidental citizen walking down Accident Street And a brick falls on his sconce.I'm no Innocent Bystander bystanding when the riot starts.Lacted the only way I could act.I end up nowhere with nothing.Please don't lecture me because you are lucky and I'm not.Please don't hurt me so I can't help wanting to hurt you.At least wish me luck.And let me stay ready to help you any way I can.P.S. It looks like he won't even wish me luck or say good-bye.
Lewis Marker and William Burroughs电影中最令观众费解的部分大概是第三章节中的现代舞,营火旁像幻影一般滞空与粘连的肉体,在我看来很有Francis Bacon作品的风格。
英国画家Francis Bacon是同名英国哲学家近亲的后代,擅长描绘尖锐、狂暴、扭曲、噩梦般的画面。
巴勒斯和Bacon在五十年代由艾伦金斯堡介绍相识,因为他觉得两人的艺术风格很相近,当时巴勒斯刚由于误杀妻子的风波出逃,而Bacon正处于一段灾难性的不健康关系中。
巴勒斯评价两人的异同点:“Bacon and I are at opposite ends of the spectrum. He likes middle-aged truck drivers and I like young boys. He sneers at immortality and I think it’s the one thing of importance. Of course we’re associated because of our morbid subject matter.”
William Burroughs and Francis Bacon in 1986饰演Allerton的演员Drew Starkey也在访谈中提到导演瓜达尼诺拍摄时参考了Bacon的画作。
Two Figures (1953)
Triptych–August (ii) (1972)另一个有趣的点是电影中使用了两首半Nirvana的歌曲,电影开头Sinéad O‘Connor翻唱版的All Apologies、李与阿勒顿相遇时的Come As You Are,以及两人在餐厅吃饭时点唱机里播放的Marigold。
这个时空交错的设置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事实上Nirvana的主唱科特柯本一直很仰慕巴勒斯,并在1993年见到了他的偶像,两人合作了一张单曲专辑The 'Priest' They Called Him,其中巴勒斯以monotone朗读,而柯本弹奏不协和的吉他噪音。
见面后巴勒斯点明了他对柯本的印象:“Kurt was very shy, very polite, and obviously enjoyed the fact that I wasn’t awestruck at meeting him.”“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at boy; he frowns for no good reason.” 专辑发行不到一年后,年仅二十七岁的柯本自杀身亡。
导演在采访中提到他在电影中特意使用Nirvana的音乐来展示柯本与巴勒斯的友情。
William Burroughs and Kurt Cobain in 1993
6 ) 哪儿哪儿都是灿烂的忧郁
改编自威廉·巴勒斯从弃稿中翻出来的同名半自传体小说。
小说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Queer这个词还处于半明半暗、自我厌弃的禁忌状态,是男同性恋者的暗指。
背负杀妻之罪的巴勒斯被迫在墨西哥城流亡,沉溺于毒品、劣酒与男色,直到遇到他生命中的在劫难逃。
一个彻头彻尾的巴勒斯故事,就连和影片不太搭调的涅槃乐队BGM和电影中升仙段落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人融合穿透是从弗朗西斯·培根的绘画中汲取的灵感,盖因为这两人都与巴勒斯私交甚笃。
这个故事与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以卢奇诺·维斯康蒂的电影有相近之处,在这些故事中,中年艺术家总是痴迷于理想化身的美少年,为自己的情欲惊恐万状、患得患失。
电影的前半部是一部魅力和犀利并存的性喜剧,双男主充满性张力,一个胶着粘稠,内心激荡,像花花公子版的中情局特工;一个美丽淡然,没有太多人格,像地表最具知识分子气质的Calvin Klein麻豆,在既污秽又宛若天堂的墨西哥城中寻欢作乐。
后半部变成了一部追寻超凡体验的奇幻公路片,对死藤水抱有执念的巴勒斯求佛得佛,睇破(或者恐惧睇破)真相的两个人从此天涯两隔。
电影的最后三分之一重回瓜导经典《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一段同志之爱,并未带来救赎,而是在现实的目光下逐渐凋零。
整部电影更像爱德华·霍普的画,哪儿哪儿都是阳光,哪儿哪儿都是阴翳,哪儿哪儿都是灿烂的忧郁。
7 ) 「007」主演的年度同性电影,被低估!
以《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闻名于世的原著作者安德烈·艾席蒙另有一本小说《爱的变奏曲》,大陆译作《春日序曲》。
这本小说分为五个篇章,第一篇《初恋》写同性,其后四篇写异性。
这篇《初恋》的故事,讲的是男孩保罗在成年后回到故乡,只想再见一见父亲的木工好友南尼。
他从小对南尼怀有同性情愫,但这次回故乡,他却发现父亲和南尼曾是一对隐秘恋人。
木屑纷飞、热汗淋漓,这一篇字字欲火焚身,贴心程度不输《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非常适合被导演卢卡·瓜达尼诺改编为电影。
而《初恋》之后的四篇异性小说,文感陡然下跌,艾席蒙写得心不在焉,显然对异性题材无甚兴趣,似乎只是出于身为作家总要挑战其它领域的原因,才创作了其它篇目。
他对自我的掩藏能力,远不如被评论界视为二流作家、一生却富有而长寿的毛姆。
英国传记作家赛琳娜·黑斯廷斯在《毛姆传》中,将毛姆的同性倾向展露无遗。
但毛姆本人不但通过婚姻早早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化,而且在创作中从不透露一星半点此情真心。
他非但一生从未写过同性小说,而且在《红毛》《面纱》《寻欢作乐》等小说中,将异性情感研究得比谁都透。
但可惜的是,人如鸿鸟,雁过留痕,从他与两位同性友人间过从甚密的交往,以及其晚年最爱在自家别墅中开裸体泳池派对等事,可以断定他有着很深的同性情结。
只是创作上的绝对自律,让他在小说中彻底抹掉了这方面的情欲真心。
毛姆和他的男人们艾席蒙的无法掩藏,毛姆的绝口不提,这两者综合而成的摇摆状态,被极为形象地呈现在了导演卢卡·瓜达尼诺最新的同性电影《酷儿》当中。
对影迷而言,《酷儿》的噱头在于“007”丹尼尔·克雷格主演破尺度同性片,硬汉特工突变酷儿爱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性癖的隐喻。
但演员其实是《酷儿》最不重要的地方,这部电影的魔力,在于瓜达尼诺对同性身份和情感的不竭探索。
2024《酷儿》导演瓜达尼诺跟艾席蒙一样,他们无法在作品中掩藏住真性情,所以《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改编堪称天雷勾地火。
而在《挑战者》这部异性电影中,赞达亚这个角色的成立依靠的是她本身的气场与魅力,她几乎是独立在瓜达尼诺渴望表达的情感之外,如同一根天外的引线。
这部电影的成立,则在迈克·费斯特、乔什·奥康纳这两位男演员青春、燥热的互动中。
比如在大学餐厅里,奥康纳用脚将费斯特的凳子勾到自己身边,又比如两人在桑拿房中表面互呛、实则调情的热气腾腾的对话。
桑拿房中的亲昵场景,对裸身的疯狂迷恋,正如同阿根廷导演马可·伯格(《金发男子》《跆拳道》)后期肉体横陈的影像表达,看似刁钻实则性感的身体镜头运动,又令人想起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的男性身体摄影。
在《同义词》《阿赫德的膝盖》两部电影中,拉皮德热衷怼着男演员的生理部位运镜,镜头深到恨不得直接刺入。
这种运镜方式,其实是同性题材惯常爱用的。
2019《同义词》
2021《阿赫德的膝盖》这部《酷儿》中,瓜达尼诺便多次对32岁的德鲁·斯塔基如此运镜,只是程度不如拉皮德那样饥渴难耐。
即使像李安导演的《断背山》这样严肃的同性电影,希斯·莱杰、杰克·吉伦哈尔在帐篷中的“一夜春宵”,镜头也有点此般风味。
这种运镜的流行,一方面是由男性的身体曲线决定,但更为重要的,则取决于同性情感的隐秘性。
与异性情感天然便具有社会性不同,同性在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渐变中,始终呈现出一种极度参差的面貌。
这种参差,注定同性将一直被最基础的身体欲望缠住,很难直接抵达身体以上的交流。
这种基础性,便决定了导演们的镜头爱在男演员们的私密曲线中运动。
瓜达尼诺在《酷儿》第三章中,便想摆脱这种基础性,试图通过一种极度抽象的表达,探索灵魂的交流。
电影《酷儿》根据美国作家威廉·巴勒斯(1914-1997,代表作《裸体午餐》)同名半自传小说改编,电影依次分为“你觉得墨西哥怎么样”、“旅行伙伴”、“丛林里的植物学家”和“两年后”这四章。
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丹尼尔·克雷格饰演的美国侨民李在墨西哥城结识了年轻的学生尤金。
两人在一通交往后,由李出钱结伴前往南美洲旅行,期间李因长期的药物上瘾而罹患重病。
当身体恢复一些后,两人在厄瓜多尔的密林中,通过食用一种叫“死藤”的植物,达到了心灵感应的境界。
这种感应,让尤金看到了身为酷儿的残酷后果。
于是,他决意从李的人生中彻底消失。
最终李怀抱着对他的思念,直至老死在孤独的床上。
首先,这部电影是典型的瓜达尼诺式的。
整体而言,它呈现出瓜达尼诺对复古影像那极为成熟、流畅的掌控力。
无论是角色、景致在影像上的做旧感,还是红、绿、蓝、白等色彩安排与层次,以及空镜所呈现的建筑格局与线条,都是瓜达尼诺身为导演在技术上的专业表现。
他在艺术及幽深情绪的捕捉上,则体现在慢镜的间杂。
比如李在酒馆看见门口的尤金一闪而过,一闪而过本是快,但瓜达尼诺偏偏用了一个瞬间的慢镜头,精准地表达了尤金在李心上那么快又那么慢的悸动时刻。
局部来讲,电影《酷儿》的前两章正如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一样,中间突然出现断身女体的画面(隐喻的是李对异性的残缺需求,这种需求是社会性需求对身体需求的被迫反刍),又犹如《阴风阵阵》乍现。
而且还能在片中看到不少其它电影的影子。
比如李和尤金的对视如同《卡罗尔》;李房间墙上的衬衫,是《断背山》结尾式的挂法;李和尤金共坐在沙发上看书,令人想到《单身男子》中最安稳的一幕。
而这些,都被统一在了瓜达尼诺导演自己的风格中。
2009《单身男子》
这种风格的成熟、独特、优美,甚至能够远远超越题材与取向本身,令人产生无差别的向往。
电影《阿诺拉》的女主角麦琪·麦迪森就曾说过,自己想出演瓜达尼诺的电影(尽管她知道,女演员在他的电影中不一定能获得艺术的偏爱)。
第三章“丛林中的植物学家”,可能是电影《酷儿》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一章不断令人想到毛姆。
影片中,李被人误解为是中情局职员,他在南美生病,和尤金在密林中遇险,都和毛姆的人生经历颇为类似。
毛姆曾做过间谍,在和年轻的亲密男性出游中国时,差点死在中国的沼泽地中。
《月亮与六便士》中,男主角查尔斯前往南太平洋的一座孤岛,在那里的村庄找寻人生意义;而在他70岁高龄写就的杰作《刀锋》当中,男主角拉里同样出走寻道,并在印度的日出中悟出了生命的一切。
这些,都同电影《酷儿》中的李试图在南美密林中找到心灵感应之法异曲同工。
李和尤金在植物学家的帮助下,服用了死藤。
于是,全片最抽象的一段戏出现了——李和尤金逐渐变得半透明,后又恢复成完整的肉体,两人拥抱在一起,彼此深入到对方的身体当中。
李的手在尤金的皮肤下游走、抚摸,尤金如是,两者便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合体。
这个场景其实并不难理解,它代表的是从《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到《酷儿》,亲密的同性从“无限接近”抵达到了“彼此透穿”,这是瓜达尼诺对同性情感的理解进阶和理想渴望。
在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艾力奥和奥利弗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如艾力奥的父亲所言,“你有过一段很美好的友谊,也许已超越了友谊”,无限接近,但最终没有抵达。
然而当艾力奥说着“艾力奥”,奥利弗说着“奥利弗”,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没有实体的彼此穿过”。
而在《酷儿》中,瓜达尼诺将这种“穿过”实体化——李的身体穿过尤金,并留在尤金的身体中,尤金同样如此。
这种穿过与性无关,而是性之上的一种心灵渴望。
爱一个人太深,不只是想进入他,而是想成为他;但在成为他的同时,知道自己也还在,且看见自己正在成为他。
而电影《酷儿》只是将这种情愫与概念,通过特效,用两具身体写实地呈现出来罢了。
所以本质上,《酷儿》并非一部抽象电影,它只是需要观众们去理解“艾力奥”和“奥利弗”不再只是两声呼唤,而是进变成为两具真实的身体。
密林中的这场心灵感应,让尤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酷儿。
这与他自己的愿景不符,所以他最终离开李。
李死在床上的最后一刻,还在幻想年轻的尤金抱着自己。
或许这就是酷儿们的世界吧,从始至终都被身体掌控。
所谓灵魂,所谓心灵,只是身体的附庸,而非身体的主宰。
作者| 冷猫;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8 ) [Film Review] Queer (2024)
Title: QueerYear: 2024Genre: Drama, RomanceCountry: USA, ItalyLanguage: English, Spanish, FrenchDirector: Luca GuadagninoScreenwriter: Justin Kuritzkesbased on the novel by William S. BurroughsMusic: Trent Reznor, Atticus RossCinematography: Sayombhu MukdeepromEditor: Marco CostaCast:Daniel CraigDrew StarkeyJason SchwartzmanLesley ManvilleHenrique ZagaDrew DroegeAndra UrsutaAriel SchulmanMichaël BorremansOmar ApolloDavid LoweryLisandro AlonsoColin BatesAndrés DupratMichael KentRonia AvaRating: 7.5/10Birthed out of William S. Burroughs’ own experience in Mexico, QUEER the novella burrows into his sexuality in an almost achingly touching extent that it wouldn’t surprise anyone that in time, it will morph into a motion picture wrought by none other than Mr. Guadagnino. Tossing off his 007 outfit after almost two decades, Craig is hot to trot hopping on a role that couldn’t be more disparate from the suave, immaculately suited spymaster and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the often disheveled William Lee, an avatar of the author himself. An American expatriate sauntering in Mexico City in the 1950s, Lee is a writer having a monkey on his back, but his jones for Eugene Allerton (Starkey), a young American G.I., the Adonis-like object of his desire, turns out to be far more potent despite himself.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an epilogue included), QUEER may error on the side of wandering unduly into Lee’s cringy, blasé conquest of an inscrutable Eugene, to attest how a man can easily be reduced to a simpering, mumbling love fool for his infatuation as long as he receives even a smattering of positive signals. Guadagnino’s unrelieved scenes of toping, smoking, mainlining also test an audience’s patience (whoever has a functioning olfactory sensorium would even want to stay near to those people?). A person’s sexual attraction is a variegated private matter, but a general sex appeal cannot be too deviated individually, one may argue. Lee’s unilateral crush is magnanimously accorded with some sort of reward as Guadagnino and Kuritzkes’ script do not shy away from explicitly intimate acts, though the age discrepancy between Lee and Eugene (at least 2 decades apart) determines that the latter’s physique in the buff is stylishly and artistically exploited to quench a more unsavory lust of lecherous middle-aged gay men whose libidos are supposedly on the wane. Not that it is wrong to adopt Lee’s perspective as the film’s line of sight, after all, it is an author’s irrefutable prerogative to stick to their own vision in a roman à clef like this. But one really hopes QUEER would’ve beefed up Eugene’s part (in the novella, he is more like a sketchy symbol than a character with enough flesh and blood), and found a key to his perpetually unforthcoming interiority. Ergo, albeit Starkey’s own striking appeal, Eugene’s evasion not only finds him a merely empty hull who has no apparent emotional fluctuations, but also conduces to a shallowness in Lee, whose intellectual facade cannot mask his own capitulation to the primal libidinal impulse out of a stupor of stultifying ennui. While the narrative kernel is a somewhat schematic imprint of the two men's differentiations on the sexuality spectrum, Guadagnino's film well comports itself meandering into a Lynchian realm with its surrealistic elements, aptly supported by Trent Reznor and Atticus Ross’s decisively disruptive sonic contrivances and anachronistic needle drops (Prince, Nirvana, Sinéad O’Connor, to name just a few), plus an uncharacteristically bedraggled Lesley Manville as a mad doctor in the South American jungle: dreamlike, astral sequences accessorized by striking miniatures and vintage hues, phantom caresses and two naked bodies melding into each other, Lee’s yearnings find the most aesthetically stunning expression and no wonder, telepathy is his holy grail to dismantle the impenetrability of a human's soul and emotions. As the cynosure of the story, Craig is terrific to behold (even in juxtaposition of a sinfully delectable Starkey) and magnificently exposes Lee’s vulnerability and debasement to a piteously affecting level, internalizing all the setbacks and frustrations with a wry smile and never veering into the lane of sinisterness. As often with Guadagnino's work, QUEER substantiates the auteur’s growing capacity in style-experimenting, queerness-exploration and mood-setting, but it seems that an undertone of distantiating Pyrrhonism has been detected in his recent output, that might keep a viewer’s empathy at bay, which, contrariwise, is not necessarily a shortcoming but a hard-won distinction, only it might sound the death knell of the acceptance from a more mainstream audience, if that is something of Guadagnino’s concerns. referential entries: Guadagnino's CHALLENGERS (2024, 7.4/10); BONES AND ALL (2022, 7.3/10); SUSPIRIA (2018, 7.5/10).
9 ) 复古又先锋之作,唯有“当今”环境无法消化
回到了曾经拿手的同性恋题材,瓜达尼诺如鱼得水,完全发挥了自己的创作特长,即对于声画的主观性营造,调动各种手段,让每一个画面都具有极强的情感渲染力,将同性恋人物的复杂心境与纠缠情爱直观地呈现出来,并作用于彼此之间的缠绵关系,《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粘稠、绵延的镜头处理,正是人物始终没有被外部世界观念斩断的情爱牵线。
这种爱情的角力正是瓜达尼诺作品中的叙事主线,而直观的复杂心绪表现则是相应的“叙事途径”,是瓜达尼诺的“戏剧性”。
在《酷儿》里,我们能看到A24对瓜达尼诺赋予的自主性,他更加大胆地实验影像技巧,也更加扩展了既有的爱情角力之主题。
比起《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他的手法途径不再集中于镜头移动,而是丰富到了音乐、剪辑、叠影,且更挑战观众传统观影习惯的处理方式。
而在主题的“角力缠绵”之上,他也从情侣之间的二人纠缠出发,外延到了人物对整个世界的对决。
这是以往作品中必然涉及的部分,即同性恋者面对世界主流观念之压制的反馈,既做出反抗,又始终弱势着,在本片中则强化成了一个主要的内容层面,展现人物对“外部世界”的纠缠复合之角力,与情侣之间的相应关系形成了同步,也让情侣之间的交互更多了一种“彼此试探”的意味。
这落实在了恋爱关系的建立与推动这一具体层面上。
男主角似乎更加坦诚,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主动地“攻击”伴侣,伴侣则在外部世界的观念中畏惧,小心翼翼地掩藏,接受男主角的“攻击”,被其引导着试图接受同性恋的自我真实人生。
但从本质上看,男主角其实反而是惧怕外部世界的存在,他彰显自我的攻击恰恰是过度敏感的应激反应,努力刻意地强化着“同性恋”的自我形象,以此压抑内心被动摇的弱小与不自信,防止自己被世人的蔑视与排斥所摧毁。
反而是似乎被他攻击“求爱”的弱势伴侣,实际上才是自信的存在,极其自然地处在各种外部环境之中,彰显着自身的身段、优雅、美貌,完全无视周围的眼光。
这带来了男主角与伴侣的情爱攻守关系,男主角在表面上是在积极主动地“攻击”,引导伴侣走上同性恋之路,并接受自己,实际上却在瓜达尼诺的镜头处理之中,凸显了他自己的“被引导”。
声画即男主角的主观内心反馈,是影片的重要手段。
它投注在伴侣的身上,伴侣则独立于这种声画主观性,是客观存在的“独立外部之人”,以主观心境的隔绝而成为了更强大、坚定的“完美同性恋之符号”,自身毫不动摇(观众无从感知),只展示外在的体态之美,以此引导着男主角的情爱激荡反应,带动声画部分的变化。
并且,男主角的“弱势”也外延到了其对外部世界的反馈状态,与伴侣共处于各种环境之中,与“淡定美丽自信”的后者始终对比着,凸显出自己在左顾右盼、拿捏体态之中的不自信,反过来被伴侣的坚定所引导,真正消化了自己的同性恋命运。
瓜拉迪诺将作品放在了墨西哥,男主角等人的异乡人身份与墨西哥的环境产生了先天的文化隔膜,作为同性恋与外部主流世界之冲突摩擦的外化象征,同时又拓展了“自身坚定、引导不自信者”这一情爱层面行为的表现方式。
在影片的第一篇章之中,男主角会引领伴侣进入各种墨西哥环境,也在这些环境中与其他同性恋进行着对暗号式的交流,像特工一样地行事,正是同性恋美国人之于主流社会墨西哥的难以融入,真实的自我只能偷摸为之,而伴侣则始终落落大方。
环境以酒吧为主,是内部约定俗成的同性恋聚集地,外界却并不知情,男主角等同性恋在其中交谈、彼此交互情爱,而外人则对此感到诧异、排斥,让男主角等人只能互相暗示、时刻留意外人反应。
男主角在酒吧中看到伴侣,也带着伴侣进入一个个酒吧,在表面上引导着伴侣进入了同性恋的世界。
后者从“意外进入,与女同伴相会”象征的“潜在命运”开始,经由他的引导,发展成了有意进入、与男性情侣相会的“主动接受命运”。
但事实上,在这样的环境中,反而是伴侣更加无视外部环境、大方而美丽,带动着男主角的情爱震荡与凌乱内心,完成了生活与性取向层面的反向引导。
在第一篇章中,男主角引导着伴侣,让其接受同性恋人生与同性情侣,这形成了二人在情爱关系之中的角力,带有攻击力对应的同性恋意志之“高下”,并被导演具体成了同性概念中的攻与受,呈现在性爱的内容之中,同时也落实在非常微观的“攻击性要素”之上。
男主角佩戴的枪、朗读报纸里的杀人事件,以及自身发出“强力引导”时象征“同性情爱中强吃弱”的动物要素---蝎子、西班牙斗牛、山羊标本,等等,暗示着他在情爱丛林中的肉食者地位,强力地试图吃掉地方,纳入自己的同性恋世界,实际上却带着之于外部环境的敏感与不自信,反而是动物世界里的弱势存在。
作为对上述内容的表现,瓜达尼诺动用了极其丰富的声画手段,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渲染力。
在序幕中,我们看到了诸多的符号式要素:条纹规整的衬衫意味着反向于性爱的“穿上衣服”,条纹更强化了其刻板、规整性,即压制自由同性情爱的刻板性取向与性爱观念,蝎子爬行在上面,手枪摆在上面,象征着“攻击性与强势肉食动物”对此的冲击,最后则落到了JEWEL的单词之上,表明这一切支撑之爱情的宝贵。
这些要素迅速地落实在了男主角的身上。
他坐在同性恋酒吧里,极其主动地引导着一名同性恋男孩,试图让他接受自己的求爱。
男主角的第一次出场,带有瓜达尼诺对影史经典的借鉴,依靠后者的呈现风格、人物形象、内在主题,加持了自己的表达。
远景中的身形、默默行走与拉长的影子,静态的镜头与消失的配乐,包括他佩戴的大檐帽,让人想到了梅尔维尔的杀手电影,带有强烈的情感克制与隐忍状态。
这带来了非常复合的表意暗示,一方面塑造了男主角的强大“攻击性”,一方面也让他成为了“独行杀手”,冰冷只是对内里情爱渴望的强行克制,独行杀手会沉迷于情爱的阴谋,最终死亡,而男主角也同样会暴露实际上的弱势一面,面对外部世界而产生心境的动摇。
在序幕中,这充分表现在了他勾引男孩的一幕。
他看上去非常强势,不停地说着关于同性恋如何被伴侣家长歧视的笑话,并主动地抚摸男孩的项链,实际上却不时留意旁边异样眼光的路人们,说话时也显得非常神经质,刻意地突出着自己的“自信”。
这导致了勾引的结果,男孩并不接受他,直接逃离,他则只能站在原地,镜头更强化了这种状态,此前始终的正面镜头突然切到了上方角度,并由树木进行了脸部遮挡,暗示着他力量的削弱,其诱发则是环境的切换,在“同性恋酒吧”到“外面”的瞬间出现。
显然,当他离开了同性恋酒吧这一相对强力的加持环境、面对更整体性的外部主流环境的时候,色厉内荏的强势就暴露了弱势的真面目。
他对男孩的强势、自信“同性恋”并鼓舞伴侣,只是外表的表演而已,强大的攻击性也是相对的,停留在两个弱势者的内部。
瓜达尼诺使用了“外貌”的概念,并由此处发展到了全片。
序幕里男孩的容貌是美丽的,却被严重的雀斑所影响,意味着其作为同性恋者的弱势,同时也暗示了男主角投注其身上的情爱的“不完美”,男主角相对强大,却也是神经质的扭曲形态。
随后,我们看到了这套手法的再次使用。
在夜晚的时刻,男主角处在了上述的“梅尔维尔式”场景之中,与异性恋者对谈,在对方多人的强势面前迅速离开,并得到了对方“我要和他保持距离,因为同性恋总是想和我上床”的贬低评价,同属于黑夜的“梅尔维尔式杀手“也就失去了攻击性加持的强势,被环境所打败了。
作为对此的”验证“,男主角走在街上,看到了伴侣,梅尔维尔式的纯静环境音瞬间被打破,他走在外部环境的墨西哥街头,伴随着nirvana的《COME AS YOU ARE》。
在全片中,摇滚乐的元素反复出现,加持着男主角与伴侣的情爱时刻,而此时的二人初次相遇,发生在男主角受挫的瞬间,也由此定义了二人爱情的走向:表面上,伴侣会带来男主角的爱情转机,但烘托男主角心境的音乐却反而是全片中最为敏感、脆弱、甚至绝望到底的一首,柯本临死前的演唱对应着男主角在外部社会之中的实质弱势,让其表面上的自信笑容变得无比刻意而伪装。
在这样的音乐中,他看到了斗鸡,以及偶然路过的伴侣,伴侣由此成为了二人同性情爱关系中的”胜利斗鸡“,在他主观性”弱势“的音乐中保持着恒定的美丽姿态,在第一视角的升格画面中走过,留下缓慢而厚重的慢镜头之心灵震荡性,引导了属于他内心的音乐。
这意味着二人关系的本质,男主角引导对方的强势会被反过来压倒,后者对他的“同性情爱、美妙幻觉”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保留,最终主导了关系的发展,让他进入绝望的“柯本”状态。
在这个阶段中,男主角穿行在数个同性恋酒吧,给出了更真实而全面的反应。
他在第一个之中与同性恋友人聊天,互相”对暗号式交流“的模式并不足以抵消此前的弱势:伴侣的秃头形成了又一个”同性恋强大之美的缺失“,而男主角刚刚落座时,下意识地收拢双腿,不让其悬在半空晃荡,也是对于”外部主流社会礼仪“的一种驯化动作。
导演使用了非常大胆的声画手法,让男主角在同性者的交流中突然”凝固“,直接变成了黑白的状态,环境音的收音机也变成了非常嘈杂的底噪声,表现出外部环境对他的巨大影响,流畅的内心抒发直接被”凝固“住了。
而当他在酒吧中遇到伴侣的时候,表面强势与内里反向的状态完全展开。
此前,他先自行进入一个同性恋酒吧,敏感而小心地暗中窥视、寻找同性对象,却没能得手,只能迅速离开而”弱势“,随后进入第二个同性恋酒吧,看到了自信美丽而坐的伴侣,却显得不够自信,因为看到伴侣身边的女伴,随即转去了另一个”更弱势存在“的同性者。
在极度表现主义化的黑白高对比度画面中,男主角带着大檐帽的巨大身影笼罩了男孩,意味着绝对强势的”同性之爱引导力“,男孩则缩成一团,答应了男主角开房的要求。
在男主角与男孩开房的段落中,瓜达尼诺首次激活了”攻受“的概念。
粉红色的光线、二人身影出现的镜中,都暗示着绝对情爱、真实心境的外露,而男主角却是”被动的受“一方,伏在男孩的身下,为其提供口交服务。
由此一来,他的弱势形象就得到了两重的确立,首先是之于”绝对强者“伴侣的”弱“,伴侣此时是带有女伴的”绝对主流社会者“,同性世界的男主角根本无法接近他,只能回避地去寻找同性世界里的相对强势感,压倒更弱势的男孩,但到了情爱爆发的真实瞬间,男主角又变成了”受“,被进一步地动摇了。
绝对外部与同性内部的两重动物森林之中,他实际上都不是食物链里的上风存在,只是靠着大檐帽与言谈进行着刻意的装扮而已。
男孩缺了一个门牙,由此打破了其美丽程度,再次说明男主角投注于此的情爱的”缺陷“---在二人离别的时候,男主角想要给钱,即居高临下的”肉体服务购买“,却终究没能给出,主导性与强势形象被打破。
伴侣再次出现,暗示性地完成了对弱势男主角的”首次引导“,也是对其本质弱势的揭露。
导演给出了两个同性恋酒吧的段落,展示二人在环境中的表里状态。
在外表的言谈中,男主角始终是强势主动的一方,似乎不顾外人眼光地对伴侣行礼。
但当段落进入具体对谈的部分,他却暴露出了最为弱小的敏感一面:二人与另一个同性友人对谈,伴侣不太顾忌地高抬腿,骚气地侧坐,说着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是同性恋者内部的自信一方,而男主角则始终留意着外人的反应,对伴侣说出“这里是同性恋酒吧”时不停偷窥旁人,此段落的第一个镜头是西班牙斗牛的杂志封面,拿着杂志而自信风骚的男胖子无疑拥有着斗牛士的姿态,而他“勾引”的男主角则是“牛”---女伴到来之后,男主角迅速放伴侣离开,去到“主流性取向”的状态。
而在男主角与伴侣独自交互的两个酒吧段落,表里的强弱势同样得到了表现。
男主角对伴侣行斗牛士之礼,暗示着对伴侣的“挑逗与强势勾引”,同为同性恋者的老人却对他不屑一顾。
随后二人开始对谈,男主角说着墨西哥的杀人事件,似乎非常“攻击性”,首次出现的叠影手法却揭示了一种“暗中潜在的内里”,即他此刻的心境反应,也可说是“灵魂精神的外显”。
手部的虚影温柔地抚摸着伴侣的脸,与他表面上的言谈举止形成了对比,让表面成为了一种“对外部规则与眼光的遵守甚至忌惮”,只能停留在谈话中,压抑了内心中直接抚摸示爱的渴望,正是梅尔维尔电影里杀手主人公的状态。
这也用在了二人约会的电影院段落之中,且带有更丰富的表意手段。
身处在黑暗的相对封闭环境中,观看着同性意味暗示的电影,是之于绝对外部环境的相对暧昧世界,但男主角依然正襟危坐,“恪守规矩”,抚摸伴侣的手只能出现在虚化的叠影之中,如同他对关系的渴求只能寄托于电影的非现实平台电影画面中,人物被引导着伸手,推开了“门”而进入,现实里的男主角则拥有了虚化的手,镜头从身后出发,推拉向了电影银幕,暗示着他对此非现实世界的“进入”,影院正是“门”。
象征性的“进门”延伸到了现实维度:二人进入了男主角的家,也由此开始了叠影中“情爱交互”的落实,却又等同于“大银幕里电影世界”,暗示着这一切之于客观现实的脱离。
男主角放下了一直佩戴的枪,无疑是同性关系的跃进与男主角的“强势攻”属性,但它接在电影院段落的后面,由此成为了男主角进入的“电影世界”,由他的强力所引导而成,却带着一种非现实性。
二人回家时走过的绝对外部世界部分,正是对此的表现。
男主角拦下出租车,却与伴侣产生了墨西哥与美国人的冲突,从语言到“该死的美国佬”,暗示着其同性恋身份之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冲突,他对司机的恶毒产生了敏感、神经质的反应,极度不自然地大笑,一旁的伴侣却不发一言,始终保持着沉静的美丽,正是二人实质上的强弱之分。
在此前的对谈中,他提到自己必须长期配枪,以及“接受我的同性恋,这是一种血脉注定的命运”,但这种强势与完全接受都只是表面,说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反复留意着旁人的眼光与反应,正是不经意间流露的不自信。
音乐的使用同样指向了这一点,在二人约会的过场段落中,温柔的音乐响起,加持了男主角的视角出发的主观性场景,是他被“客观存在而无心境表现”的伴侣所影响--而非影响伴侣的情绪---的爱情关系之中、处于弱势被引导方的表现。
此外,与肥胖友人交谈时的“斗牛士杂志”,结合二人之于外部眼光的反应,与秃头友人交谈时,镜头带到的“山羊标本”(被捕猎的弱势动物),以及他的正襟危坐、被“黑白凝固化”,都让他处在了丛林法则之中,并成为了“同性交互中的被捕猎、斗牛并杀死”、处于被引导一边的弱势动物。
他是同性恋内部的弱势者,更是外部社会中的弱势者,同性恋世界本身也就是之于整体环境的弱势存在,分别表现为两个“同性关系中强者”友人的秃头与肥胖之缺陷,不足以象征同性情爱达成状态的绝美。
随着男主角与伴侣初步建立关系、发生初次性爱的推进,瓜达尼诺开始进一步地开发本片的表意系统,将诸多层面的手法与要素拓展开来,让这个部分变成了深入男主角内心的过程,穿过其“以同性恋的信念立足于外部现实,压倒传统观念之主流世界”的强大表面,通向其极度不自信、只是强撑同性恋之自我的内心真相。
“酒”、“香烟”、“酒吧”、“肉食”、“打字机/注射器/手枪”,成为了重要的元素,与直接输出主观性内容的运镜、音乐、环境相结合,在这个部分中完全发挥出来。
酒、香烟,是人物获取快感的途径,对应着同性情爱与性交之中的体验,男主角会为伴侣倒酒、点烟,象征着他在性爱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引导初出茅庐的伴侣从懵懂进入同性恋世界,也为伴侣提供肉体与精神层面的情爱快乐。
与之相应地,男主角作为同性恋者,面对主流社会的态度,获得体面而上层的外部社会身份,从而证明同性恋者的取向与观念对于整体环境的胜利,是更宏观的“强势”,却也带着“暂时幻觉”的不可持续之虚假。
这落在了打字机、注射器盒子、手枪的要素上。
打字机是他作为作家的道具,以此将内心投注在文字的“现实”之中,是主观心境与追求的现实化达成,情爱渴望的落地,注射器则揭示了其情爱等同于毒品致幻快感的本质,手枪是社会现实面的标记,是“毒品”带来的“强势达成之幻觉”,暂时地加持了男主角的对外力量,是他应对墨西哥社会局面之动荡的强势手段,又是社会层面的“阳具”,对应着他在同性爱层面的“强攻”身份,用阳具的“手枪”给“弱受”提供高位而强势的快感,并完成自己作为同性恋者在现实社会里的强势胜利,但他在每次情爱的时刻都要“摘下手枪”,就暴露了这种“现实强势”作为“人为佩戴”的后天赋予,会在同性爱爆发的性交高潮中反而“去除”,将他还原成弱势的真是状态。
在开头的画面中,条纹衬衣是人们穿着得体、在外活动的穿着,条纹强化了象征社会礼节的规整性,同时也在视觉的眩晕感上暗示了其对同性情爱的抑制,蝎子、打字机、手枪都在衬衣上,是男主角强势身份在现实里的胜利,并通过打字机而输出在现实的“文字小说”之中,以此作为同性情爱之内心追求的达成形式,其上写着“jewel”,更是强烈的暗示,意味着他在现实中挖掘出同性情爱的宝石,即美丽无比的伴侣。
同性恋酒吧在现实社会中合法经营,形成了同性恋满足的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对接,又因其中同性恋客人的遮掩、对普通客人的隐瞒,变成了一种相对局限的“现实落地”。
男主角等人流连于同性恋酒吧之中,在这里似乎找到了同性情爱的实现途径,并由此扩展到了自身对肉食的摄入之上。
在电影中,男主角在酒吧的每一餐都是肉食,构成了他在人类社会之“丛林”中的强势地位象征,是社会与同性关系中的肉食动物,即沙漠里的蝎子、斗牛运动杀死公牛的斗牛士,也体现在台词之中---通过大量的交谈,他描述自己对同性恋的堂堂正正,以及对伴侣的强势建议,做出各种挑逗、示爱、关系推进的邀请,也会描述餐食与相关联的情爱内容,如自言一种理想中的食物,将动物的肉体切开,同时表现着其对肉食与性爱的强势,不仅喜欢重口味,更趋向于SM。
酒吧与肉食形成了男主角在现实里的强大地位,而反向的“无法融入酒吧”与“肉食受阻”就成为了动摇其强势的途径,也对应着酒、香烟、谈话的部分---在酒吧里的“自斟自饮”与“喝醉”,只能自己给予自己快感,而非理想中的强势给予伴侣,且这种自我满足不过是“醉倒”的一种负面行为,是他强行赋予自己的社会、情爱层面中的双重胜利之身,表现强势的谈话也经常无法持续下去。
而在更直接的主观呈现之中,音乐与运镜得到了充分的使用,作为背景伴奏的音乐让场景完全成为男主角的主观化世界,由音乐的风格与内容去表现他的起伏、正负面心境,而音乐的切断、进入环境音,则是对其同性情爱感受的直接打破,将他逼进了冰冷的外部现实。
运镜的流畅甚至“暧昧黏糊”的运动风格,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并由突如其来的快速不稳定移动、突兀的剪辑切换画面所打破。
在表现男主角与伴侣的初步情爱互动时,瓜达尼诺细致地操作着上述的要素与手法。
在二人发生初次性爱的前后段落中,男主角的“外强中干”已经得到了非常完整的表现。
在酒吧中,他极其主动地诱导着伴侣,但当伴侣表示自己对同性恋酒吧的属性完全不知情的时候,他却打了磕巴,反复确认,正是对伴侣懵懂的真实反应:面对这样一个“雏儿”,他本应强势引导,自信地将伴侣引入到同性恋的世界之中,拥抱自己的真实取向,结果却是打破强势形象的错愕,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如此懵懂之人。
随后,二人一起进入了外部环境之中,深蓝色的暗夜让它拥有了一种静谧的非日常感,具有同性爱实现的氛围,让二人愉快地行走在其中。
男主角表现出了对外部现实社会的“胜利”,与墨西哥本地的出租车司机对骂并取胜,伴侣只能无奈地诅咒几句民族主义脏话。
并且,极其雀跃的音乐响起,连通了男主角极度快乐的情爱满足之心。
但是,当二人即将进入男主角家、真正完成性爱的时候,瓜达尼诺马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真相表现”。
在第一个画面中,镜头先是带到了二层的明亮卧室,随后下摇到愉快的二人,前者正是他们即将进入的情爱实现场所,让他们雀跃不已,却在外部角度出发的镜头中暴露了其局限性,其明亮停留在一间房子的程度。
音乐的处理接力而来,当男主角打开房门、进入“实现环境”的时候,雀跃的音乐反而瞬间被打断了,取代以极度压抑的安静。
随后,伴侣环视着男主角的居家摆设,这是片中少有的伴侣主观镜头,即伴侣作为“绝对美丽者”(男主角同性情爱的完美寄托对象)对男主角生活的认知与掌握:他看到了打字机与吸毒针头的盒子。
这同时作用于暗喻与戏剧的层面,伴侣由此意识到了男主角的吸毒真相,埋下了不满于此、戒毒要求被拒绝之下的关系破裂,同时也是男主角视角之于全片主视点的首次游离,取代以伴侣的主观视角,与伴侣记者的社会身份(观察、拍摄、客观记录各种人事真相)相结合,作为对男主角客观真相的揭露。
此刻带着伴侣进入房间的情爱欢愉,其实只是“吸毒快感”而已,打字机写作对应的“心境实现”正是其达成幻觉的途径,在这里却只是静止放置,并未工作,男主角在全片中也始终没有任何的打字画面,象征着幻觉的无从达成。
男主角与伴侣的情爱,得到了毒品幻觉、不可持续的暗示,伴侣也因其吸毒而有所保留,让此间发生的一切都成为了短暂的圆满。
他跟随了男主角的引领而来到此房间,即将拥抱情爱,让男主角的现实身份得到了“情爱结果”的肯定,由此在两个层面中获得胜利,他在现实中实现了情爱,其成功正是现实强势的证据。
但是,镜头迅速地变成了快速而模糊的平移,连续发生两次,打破了伴侣主观视角中稳定慢速环绕的移动方式,由此打破了这种正面的暗示,以及画面中的粘稠暧昧氛围。
这恰恰来源于男主角的主动行为,给伴侣倒酒。
他想要进一步推进情爱,为伴侣提供“快感”,却反而打破了伴侣对自己的肯定,作为“情爱完美结果”的积极确切也被他自己削弱了。
这为二人随后的性爱、更未来发展的恋情关系,埋下了负面消极的伏笔,也开启了男主角在这段情爱中暴露弱势本质的过程。
事实上,早在二人第一次偶遇时,强主观性的音乐伴随着第一人称视角的画面,已经为男主角的真实心境做出了定性:看到绝对美丽的伴侣与自己对视、暧昧,音乐却依然是延续自此前酒吧受挫(伴侣与女人下棋,异性恋倾向)的《COME AS YOU ARE》,心境也仍旧是自杀前的科特柯本。
伴侣拥有绝对的美丽,不同于男主角此前交集的缺陷美者,没有雀斑、秃头、肥胖,却依然无法让他走出绝望感。
而在双方即将性爱的段落中,男主角为伴侣倒酒,打破了伴侣对自己现实强势身份的“肯定”,随后二人一起饮酒,暧昧发酵的氛围却再次被酒打破,他选了一瓶“年轻人很少能享受这种味道”的酒,暗示了自身对同性恋作为“少数者愉悦”的接受,并邀请后者加入进来,却导致了伴侣作为“非少数者”的呕吐。
伴侣勉强喝着,却在暧昧火花即将爆发的时刻呕吐起来。
男主角对伴侣反复输出着“酒”的情爱,想让二人一起获得精神快感,却起到了破坏情爱快感的反作用,其强势攻者的姿态显然是虚假的,也对应着他面对伴侣呕吐的手足无措。
在刚刚进入房间的时候,他卸下了手枪,已经暗示了其“人为赋予的强势地位”的去除。
对符号的使用扩展到了“衣服”(条纹衬衫)之上。
首先是调情的部分,男主角抚摸着伴侣的衬衫领口,想要脱下,让二人能够脱离社会主流观念准则的“规整衣服”,却停在了“夸赞质地”的尴尬掩饰之中,其状态也完全没有伴侣来得自然,伴侣的“突然呕吐”正是对男主角“输出快感”之反效果的表现,反而由伴侣自行回到了床上,推动着二人开始了性爱。
男主角强势地脱掉双方的衣服,并压在伴侣身上进行口交,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启性爱、输出快感。
但是,在此前与男妓的性爱中,他已经露出了“下跪口交”的弱势真相,在此刻的性交中则再次暴露,伴侣逐渐压到了上体位,反过来主导了与他的肛交。
在这里,眼镜的元素也得到了使用,它出现在片中大部分同性恋者的脸上,等同于条纹衣服的意味。
在性爱的过程中,男主角先摘掉眼镜,随后伴侣两次打落了男主角的眼镜,既体现出强势地位的转移,也让男主角的“后天社会形象”被去除,切换到属于人的最本质“裸体”,随后暴露的绝对真实则是性爱里的弱势---第一部分性交之后,男主角给二人点烟,却被伴侣压上来的自身弱势、第二部分性交所打断,强弱势的关系就此交换,他“给予快感”的点烟也没能成功。
男主角的强势同性爱只能在非外部现实的环境中实现,二人此时进入的房间正是此前“电影银幕中推开心灵之门”的外延。
而即使在这个环境中,男主角实质上也依然是弱势与失败的状态。
在性爱高潮的时刻,镜头带到了点燃的烟,烟是他输出快感的途径,此刻确实得到了“点燃”,却无人享用,而情爱快感的实现也被随后出现的两个窗户镜头所打破,内部的明亮只是相对于窗户隔绝之外部的有限存在而已。
这削弱了男主角主导的“同性快感”,随后他再次发言,却被打断而没能点着,再一次夯实了这种表达。
甚至情爱段落的拍摄技巧,基本依靠一两个固定机位的镜头,其克制程度不言而喻。
更丰富的镜头处理则是此前的对谈部分。
从中远景的稳定切换中突然来到二人背后的特写镜头,画面本身暗示着双方即将贴合的相对位置,也是此前电影院里“男主角虚影之手抚摸伴侣”的构图,却瞬间被再次切掉,而伴侣打开门、走向卧室的行动同样也是此前电影里的内容,“打开心灵之门”,电影院段落中主观性强烈的“前拉镜头(进入门)”变成了此刻进入卧室的伴侣,暗示着伴侣之于“打开二人心灵之门,完全接受情爱关系”的真正推动作用,而男主角则相应地归于弱势地位,其“进门”只能是电影院段落里的“抚摸之虚影”,以及强主观性的镜头前拉的象征性程度,远没有伴侣来得扎实、现实作用。
作为一部从男主角立场出发的作品,暧昧的镜头迅速被切掉,也同样意味着男主角的“心乱如麻”,并不足以引导这段情爱关系,整个部分---乃至于全片--中的时常凌乱、口不择言、尴尬难堪,便表现了他对于同性爱加入外部社会的坚信度不足。
在初次性爱段落的最后,二人享受余韵的身影从“客厅拍摄的卧室”开始,逐步退到了室外拍摄的居民楼一隅。
强调愉悦美好之主观性感受的音乐烘托着美好的氛围,男主角也终于得到了“无缺陷”的绝美情爱对象,甚至特意由“伴侣骨折的肋骨与呕吐的酒味”进行提示,肋骨在男主角的抚摸中“好多了”,酒味则被男主角告知“闻不到”,让男主角成为了“情爱缺陷的主动弥补者”,但这一切只得到了极其局限性的现实达成而已。
在二人初次性爱的段落后,瓜达尼诺紧跟上了日常性的现实部分,干脆地推翻了短暂的美好。
白天取代了深蓝色的夜晚,男主角坐在自然光线的酒吧中,为伴侣讲述着“非洲的死藤,用作奴隶制,俄罗斯人用它提取汁液,注入人体,控制人的思想”,并将手放在了伴侣的额头上。
这段对话有着非常标志性的“新浪潮”腔调,从表层文本内容而言非常突兀,甚至前后不搭、莫名其妙,其象征性的作用更强:奴隶制、俄罗斯、思想控制,是现实社会层面的政治向内容,男主角将它与二人的同性情爱结合在一起,试图以情爱的“死藤”去“控制伴侣的心念”,掌控住伴侣的额头,如同此刻他用这些话题来表现自己,侃侃而谈,展示之于伴侣的强势,即“同性恋酒吧环境中的主导性”。
由此一来,他也就完成了现实世界里的同性情爱之胜利,对应着影片设定的70年代墨西哥,处于民间运动高潮的政治动荡年代,情爱正是在这个舞台中发生、维持,面临现实社会的巨大考验。
但是,伴侣的沉默打破了他的强势,陷入敏感而脆弱的尴尬之中,随后再次做出尝试。
在这个部分中,瓜达尼诺极度细致地操作着镜头与内容的同步,完成了潜在的表意。
男主角先从菜单里的火焰冰激淋开始,它来自于现实层面,却去除了此前的政治属性,退回到了同性恋酒吧这一相对性的环境,镜头也切到了座椅为前景、遮挡人物、强调环境现实感的中远景。
随后,男主角将火焰冰激淋的原理拓展成了自己想象的菜品,将一只活猪放进烤箱,直接切开、撕下耳朵吃,这显然是更进一步的“强主观之非现实(纯粹想象)”,带着男主角对肉体的巨大欲望(食欲与情欲)与强势,甚至到了SM的扭曲程度。
此刻,镜头切到了二人的特写,意味着男主角此刻“情欲实现”的进一步非现实化,已经完全退到了自我主观妄想的层级,在伴侣的面前却依然暴露出了弱势的本质,看着伴侣的大笑,显得小心又拘束,描述美食时则是夸张过度的敏感与神经质。
瓜达尼诺极其短暂地带回了情爱完美的时刻,用暧昧的黄昏光线取代了冷白色的白天日常光,二人在酒水的快感中拥吻。
这也是该阶段中的最后一次完美时刻,迅速被负面的信号所打破:二人在夜晚的房间中继续拥吻,伴侣打断了男主角,主动表示“我想喝朗姆可乐”,随后则是“我们去酒吧”,主导了一切行为,男主角只是凑上去亲吻、为伴侣暧昧地拉裤链,却迅速失去主导权,不停地答应、“好吧”,并放任伴侣自己拉裤链,随后跟着去到酒吧。
走向酒吧的过场画面中,愉悦的背景乐再次环绕着并肩而行的二人,随后却是反向的内容:伴侣转去与女伴同坐,男主角的同性恋朋友则说着自己的恋母情结,由此成为了“美好同性恋”在“异性取向”削弱、干扰之下的扭曲结果,且他口中的另一个朋友也回了美国,意味着同性恋者在此处的融入失败,只能回到更现实、明确同性恋不可行的本土。
男主角对此保持着敏感而脆弱的状态,强笑着“幸好我有独立的收入,不用回去”,落入眼中的则是自身完美情爱对象的“破灭”:仍有异性恋倾向的伴侣,并口称“我现在有更大的鱼要捉”。
此刻的他仍然在努力,试图为自己争取到伴侣身上的完美同性爱,抵抗现实的削弱,但已经看到了伴侣身上的“不如人意”,而同性愉悦也在悄然间转向了他的自行给予,在该段中不停地给自己倒酒、饮酒,于二人交互“互相倒酒”方能达成的情爱关系而言,这无疑是消极而不可长期持续的。
瓜达尼诺连续给出了多个段落,从日常现实维度中的外在行为出发,逐步推进到男主角的主观世界,表现出其真实的消极性。
首先是绝对的外部环境,水洼、底层情景强化了其属性,男主角跳过水洼,来这里消费男妓。
这说明了他对伴侣关系的动摇,需要用别的方法来弥补情爱缺口,而男妓家中的完全黑暗、停止在其敲开房门一刻的段落,也意味着其即将走入黑暗与“情爱愉悦”的不存,招妓只能是暂时的弥补而已,无法改变他的失落与空虚。
随后,他在日常光线的酒吧中,与伴侣进行交流,个人表达、主观情感投注更强的对象,提高了段落对其人心境的表现程度。
他为伴侣倒朗姆可乐,却被“现在不想喝”地拒绝,也失去了侃侃而谈的强势姿态,最终放任伴侣离开,提出花钱雇佣伴侣的“包养”,实际上已经是现实语境之下的妥协,打破了情爱关系的完美纯洁,却依然被拒绝,只能反过来把记者工作的相机交给伴侣,在“现实社会身份”中接受伴侣的离去,暗示着现实世界里的“承认败北”。
这带来了更进一步的主观性表现。
他独坐在酒吧中,“自行赋予酒水”之下,愉悦变成了不可持续的消极“醉意”,而伴侣则与女伴言谈甚欢。
他跟随着进入了二楼的同性恋酒吧,第一个镜头是他从街道进入酒吧的远景,等同于二人一起走进他家、初次性交段落的最初画面,却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这种负面的状态随之落实,愉悦的音乐从“与现实融为一体”的背景伴奏,随着他进入二楼而突兀切换,变成了特写里的播放器声音,声量、品质都变得微小而模糊起来,与现实的环境音混在一起,有着明显的弱化与区别。
他的愉悦也即将被如此地削弱,体现在连续的第一人称视角之中:看到谈情说爱的同性伙伴,而他本人则与此隔绝开来,无法与之一起欢愉,随后则是伴侣女伴,把玩着玩具手枪,暗示着“现实社会之强势地位”的让出,连同伴侣的情爱伴侣位置也一并让出---他努力争取着伴侣,说着“俄罗斯人控制思想”的话题,想要挽回控制权,却受限于自行赋予快感的消极“醉意”,昏厥倒地。
由此出发,瓜达尼诺带来了最直接的主观段落,即昏迷中的梦境。
他以影片开头的“梅尔维尔式”画面出现,此前的绝对现实、极致无情、杀手形象,在此刻成为了内心世界的呈现,也对应了梅尔维尔式杀手的“强行压抑感情,最终暴露情感一面而败北”的真容。
他在顶光投下的阴影中“掩去表情”,带着杀手的大檐帽,似乎冰冷无情,实则“掩盖真情”。
他将匕首交给旁人去磨,意味着一种“现实中强势力量”的打造,但随后看到了空洞的六角星,对应着开头处爱抚同性情侣六角星挂坠的部分,情爱的挂坠变成了“空洞”,也就打破了强势力量支撑的情爱实现。
随后则是各个人物身穿黑白条纹衣服的出现,条纹衣服从序幕里的衬衫变成了囚服,强化了其规整性与对外穿着所象征的“外部社会、契合规则”寓意,将每个拥有情爱--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女伴同样出现在这里之人都包裹、束缚其中,而此地也正是囚禁他的监狱,剥夺了他与伴侣的完美同性之爱。
在梦境的最后,他看到了婴儿,由此构成了对自身人生的追本溯源,在出生的时刻即注定了如此的牢笼状态。
现实短暂地出现,他与伴侣做爱的床铺上空无一人,他只能睡在地板上,情爱归零,而此刻的梦境也继续深化,强势肉食动物的蝎子引出了一个女性,被“切开”、裸体地放在餐桌上,对应着此前的“猪肉美食”,此刻却成为了“蝎子”,逆转了他口中描述的强弱势地位,反而让他在梦境中被冲击:面对自己当成“美食”的弱女子,他被逼问出了“我不是同性恋,我身魂分离”的动摇,承认自己的肉体现实无法实现精神理想,但“叠影”手法表现的“灵魂游离”在此刻也落入了“不是同性恋”的自我否定语境。
这让他成为了现实丛林里的弱势“被食用”方,女性形象意味着”男同性恋”取向的根本性打破,让他在潜意识中同样拥有了对女性的异性恋渴望,正是肉体之欲--以及其对应的现实规则、主流取向---对其“绝对同性恋取向”之精神目标的削弱。
女性能实现他的肉欲,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旁人口中“恋母情结”的童年影响,辐射出了其自身无法掌控的种种客观现实,从个人童年起点到外部现实社会,让他完全独立而内化的同性心境无法保持纯粹,其带来不可持续的同性情感满足幻觉,也同样是对这种“现实创伤来源”的徒劳弥补,即女性身上插着的针管,暗示“毒品”,是日常中“自我赋予之醉意”的升级。
同性欲望来自于“恋母情结”等异性情欲的扭曲过往,让他下意识地以同性满足去弥补异性扭曲。
幻觉的最后一个镜头再次回到了梅尔维尔式的段落开头,”杀手”身着西服的脚被切换到了裸体的状态,带着巨大的伤口,正是其绝对真实内在的“弱势受创”。
当他回到现实的时候,消极的状态也就彻底外露了。
他再次与伴侣相会在酒吧,暧昧情愫的黄昏光线之中,伴侣却扔掉了香烟,强烈象征性地抗拒了“同性愉悦”,对他说出“再见”。
在酒吧中,他自行喝酒、吃药片,不同程度地自我给予消极快感,以彻底弱势的姿态恳求伴侣,与自己一起南下,却被冷酷无情地推拒。
国际象棋是很恰当的概念,伴侣与女伴在各种段落中对决,带上了象棋一贯的理性、冷静、克制,也是此刻对男主角的姿态,完全剥离了同性情爱的感性状态,而男主角只能试图摆着棋子来搭话,也必然地失败而去,因为其“梅尔维尔式杀手”只是勉强的理性克制,在此处终究变成了女伴口中“他棋子摆错了”的形象破碎。
最后,他独处于房间之中,为自己打下毒品,长镜头强化了注射毒品的全过程,以此突出其深陷同性爱抑制、只能自我赋予消极愉悦的悲剧性状态。
吸毒的一幕定义了男主角的本质,摇滚乐的背景伴奏随着吸毒的进程而逐渐流出,这正是男主角在前半部的同性情爱中获取欢愉的真相:他在追求着现实里的同性爱,试图树立自己的强势形象,战胜传统观念,引领绝美的伴侣成为自己的情爱对象,以此直观地“获得”伴侣美貌所象征的完美爱情,但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自我麻醉而已,只是在制造着成功的幻觉,欢愉的暂时性无异于毒品的快感,此前沉浸于二人情爱的摇滚乐“心灵体验”正是此时自行给予、作用一时的“毒品体验”。
在这里,他给自己点烟、喝酒,打破了此前与伴侣的彼此给予,二者是低级别的“毒品快感”,此时与吸毒一样化作自身行为,会随着段落结尾的朝阳升起而迅速结束,从静谧、内化、隐秘心灵之快感的深蓝色夜晚回到日常现实的世界,而他制造快感的房间也在剪辑中逐渐缩小,成为了整体世界的一个微小局部。
男主角通过同性情爱而获得的愉悦是不可持续的,其在现实里达成的努力、短暂的成果,都只是他强行给予自己的幻觉,伴侣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引领,由他强势主控的爱情关系也并不确凿。
对伴侣强势的他将伴侣引入同性恋世界,让伴侣接受同性取向的真实自我,扭转伴侣基于传统主流社会观念的性取向压抑,由此也成为了他对主流社会的强势压制、努力战胜。
到了上半部的尾声,这一切变成了他对自己的幻觉,吸毒时的表情并不愉悦,反而显得空虚无比,正是对其不可持续性的有力表现。
这也引出了影片的后半部:现实化的幻觉世界。
男主角吸毒之后的所有内容,都成为了一种漫长的“毒品幻觉”,在客观现实中带上了强烈的主观性意味。
摇滚乐的伴奏正是对此的加成,又与潜在保持、愈发外化显露的客观真相相结合,逐渐被后者所抵消。
男主角想要在极度日常化的现实世界里达成同性之爱,让自己保持强势地位,继续引领伴侣,扭转其思想到“接受同性爱”,并落实在“让伴侣与自己同行南美”的具体行为,捆绑着伴侣的外部活动,而旅程的目的则是控制思想的死藤,即思想层面的“强势引导伴侣”。
在后半部中,男主角逐渐进入原始丛林,得到了愈发直接的“强弱势动物”表现形式,而真相也随之揭露出来:他愈发直接地表现出对“强势追求同性爱”的渴望,也愈发暴露了一切只是幻觉、终究不可实现的真实。
随着旅行的推进,他逐渐靠近了死藤,对伴侣的情感寄托、争取途径,却从客观现实的手段逐渐变成了“强行”与神经质,也愈发与毒品的“真实面”混杂在一起,而强势的一面逐渐动摇。
环境从日常化的社会开始,逐渐变成了更加接近本质的自然,既是他主观上想要脱离当代社会的压制、进入并实现同性情爱的世界,同时也是“情爱关系中弱肉强食之丛林”的直接、真实呈现,让他与伴侣身处其中,暴露出他弱势的真相,寄托于此的“扭转伴侣,引领同性关系”也就不可实现,“自然世界”中的双重发展彼此交互作用,正是对他主观部分的有力打破。
直到最终,他直接接触到了死藤,却发现其远远不是想象中的完美,只是让自己彻底走到了毒品最终导致的破灭。
后半部的中心是旅行。
开启旅行的前半部结尾段落中,他与伴侣身处在日常光线的酒吧之中,做出了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强势表达,“我考虑买下这里,免除你的债务”,抓住了伴侣的经济困境,这正是当代社会中的惯常问题,由此潜在地“逼迫”伴侣与自己同行。
这是后半部的起点,他似乎完成了当代现实里的“强势”引导,对应着二人坐上巴士的日常化远景,但内里的不和谐已经流露出来:他暴露出了自己对伴侣的强行,表面上的和谐交流成为了假象,情爱关系由此变得不自然起来,而他也只是“自斟自饮”而已。
随后,旅程正式开始,一系列的要素、呈现载体,都逐渐地变化,向着于他弱势、不利、揭露性的方向发展,让旅行目的地的厄瓜多尔整个潜在地成为了此前“吸毒”一幕的后续”幻觉”,从幻觉的开始发展到高潮,再到快感衰落之后的负面。
而其中始终穿插的空虚、麻木、消极,则是他在吸毒时的僵硬表情,始终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自我给予、不可持续、只是幻觉”之本质。
当他们进入厄瓜多尔的时候,瓜达尼诺直接给出了客观的真相。
二人先是在夜晚的巴士中相处,微妙的打光将灯光下的其他人与蓝色夜光中的二人进行了环境的分隔,由平移镜头所强化,此时的男主角尚且能爱抚睡着的伴侣,保持强势主导的情爱和谐关系。
随后,他们行走在日常化的当代街头,也保持着最为正常的姿态。
此时,他询问当地人,购买毒品,同性情侣关系中的“幻觉”真相已然揭晓。
与之相对的则是伴侣,镜头从其斜后方取景,让观众站在了伴侣的视角与立场之中,暂时取代了通篇整体的男主角主观角度,伴侣在用相机拍摄着购买毒品的男主角,执行着记者的社会性身份,也让这一视角成为了“客观揭露真相”的存在,让男主角对情爱之主观寄托得到了客观层面的揭示与定义。
在二人情爱刚刚开始、伴侣进入男主角房间的段落中,这样的表达也有出现:伴侣的第一人称视角之中,男主角装着吸毒工具的盒子,作为作家而写作虚构作品,用文学的形式输出、宣泄幻想的打字机,其承载的真相都被“客观视角”收入眼中,暗示着伴侣在起点即对男主角与二人情爱关系的真相把握、自我保留,由此导致了男主角“强势主导情爱”自始至终的虚假,从开始就已经失去了伴侣的毫无保留,同时也意味着情爱在客观视角之下的幻觉属性。
而在后半部的开头,这一用法再次出现,且有着伴侣与观众同一视角的更“强势”感,是真实的情爱关系中强者,也由其作为记者的身份而具有了更强的客观揭露性。
当男主角问到购买毒品所在、走向目的地的时候,身后的蓝色墙壁是对前半部中“深蓝色夜晚、情爱发生环境”的延续,让彼时发生、似乎在现实中达成的同性情爱,随着色彩的”融入白天日常环境”而落到了真正的客观世界之中,成为了微小的局部,也暴露出了“毒品式幻觉”的真容。
伴侣给男主角点烟,墙上是酒瓶的特写,让“给予快感”的强势主导方换成了伴侣,也将酒与毒品升级的毒品与情爱直接相关了起来,在购买毒品的高空远景中得到了现实的呈现:伴侣给男主角扔了一瓶酒,由此形成了“快感”的传导,给予方却转换了,而男主角则表现出了神经质的咒骂,其强势表现开始露出了不和谐的刻意一面,并延续到了“肉食”的要素:男主角将肉食料理递给伴侣,继续着前半部里的“情爱中强势动物”的姿态,自己却开始吸毒,让这一切成为了“自行给予的幻觉”,伴侣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安,关系即将动摇。
同时,“梅尔维尔式侦探”的大檐帽也大量地摆在地上,同步于带着帽子走过它们的男主角,以其铺张的存在感提示了“强行抑制情感、看似强大、暴露真心后即死亡”的承载属性。
由此一来,寻找死藤的厄瓜多尔之行,整个后半部,就早早地得到了“幻觉”的定义。
瓜达尼诺让男主角进入了毒品戒断反应的负面状态,同步于二人关系中强弱势的交换、和谐的打破,以及男主角对毒品的愈发深陷、情爱挽留的愈发强行,形成了同性情爱心理层面的“幻觉消退”与随后生理上真实、必然存在的“负面反应”。
他们再次回到了巴士上,平移镜头却没有了环境的区分,让他们融入了外部的日常环境,男主角也陷入了戒断反应的寒冷与昏睡,不再有此前对伴侣的强势爱抚。
而当他们来到旅馆的时候,伴侣在特写镜头中摆好了现金、照相机,均是“经济”与“记者身份”的当代现实化标记,也再次给出了他“客观当代社会视角”出发的凝视镜头,其看到的男主角给自己点烟,试图给予快感,已然失去了旅馆房间中“与伴侣做爱,给予伴侣情爱快感”的强势能力,且在“自行吸毒快感”的道路上走到了下一步的戒断反应之中,寒冷、颤抖、不可控制。
伴侣看到了这样的男主角,想递上香烟的举动也被打断,感到非常不安,情爱关系也就不再仅仅是强弱势的交换,来到了伴侣主导之下的不可持续:伴侣是主导者,在开头即察觉男主角吸毒的真相,从而有所保留,延续到此时,看到男主角吸毒后反应,因此直接中断了自身主导的情爱快感。
通过伴侣对男主角的戒毒帮助,影片直接地给出了伴侣的“强势引导”状态,也让二人关系似乎拥有了转机,只要男主角能够保持弱势、接受伴侣主导的戒毒,就能在现实里保持这段关系。
但是,男主角确实呈现出了弱势的姿态,深陷于戒断反应,却始终没有坚定地戒毒,这也对应了他在情爱关系中的该阶段状态,继续着勉力为之的“强势主导”。
事实上,“强势主导”便是男主角的“毒品幻觉”,由此才能让他产生战胜主流社会观念、达成同性情爱者胜利的愉悦,因此他必须主导伴侣而非相反,以此“扭转伴侣”,引领其接受同性取向,以及自己的同性情爱。
但在现实之中,这就导致了伴侣从客观视角出发的“戒毒帮助”,只是让伴侣感到失望,最终落到了关系打破的结局。
死藤号称的“控制思想”、以此极致地强势引导伴侣内心,不过是毒品幻觉而已。
男主角表现出了自己对“同性情爱毒品”的沉浸,他抵消戒断反应的方式并非坚持“戒毒”,反而是与伴侣贴在一起,在特写镜头的暧昧中更深地沉浸于情爱,暗示着“以吸毒来暂时解除负面反应”。
其内心幻觉直接出现,二人在对一张空白的稿纸输出意念,稿纸在他们身前反复漂移。
这是非常“费里尼式”的一幕,带有很强的寓意:稿纸是男主角作家身份的对接,他在其上书写自己的心理,将心境的“情爱追求”落到现实里,“书写心境”的稿纸在二人之间游荡,象征着二人在思想层面的“心灵共通”,在其基础上则是控制权的争夺,表现着情爱关系达成之后的强弱势地位,也对应着后半部中对毒品死藤控制思想的寻求。
更值得注意的是,稿纸上空无一字,并未将男主角的心境与情感抒发“成文”、投入现实,象征着心灵共通的“情感内容”之虚无,而始终的漂移则弱化了男主角的强势主导地位,这已然暗示了男主角对“死藤”寄托的不可达成。
这一幕对应着其发生情境的幻觉属性,成为了对男主角贴上伴侣肉体的揭示,让男主角主导(主动靠近贴上)、暧昧和谐的情爱时刻成为了男主角自行产生于脑海、自我赋予、等同于吸毒的暂时幻觉,且其心境本身也已经倒向了“无法获得主导权、无法继续幻觉(写上字)”的消极一方,同步于现实里的情爱关系动摇、自身强势姿态弱化。
在随后的现实内容中,伴侣推动着男主角去医院看病,日常环境的远景、刻意强调的大风天气,让相拥的二人在客观世界中遭到了冲击,并落实在了医院之中:问诊的时候,男主角身后贴着“大脑外露、全身血管”的图画,暗示着他的精神与心理即将被彻底地揭开、拿出、对外呈现,再无掩盖的可能。
我们也首次听到了男主角对自身经历的自述。
在象征“客观现实中外人”的医生的主导问询之下,男主角处于被动地位,说出了自己在美国被打压、逃到南美洲的弱小经历,这才是其同性恋者在客观现实里的真相,而其“强势主导情爱”也就成为了“毒品幻觉”。
医生身后的落地窗放大了外面的客观环境,以此加持了现实世界的威压,强势地逼迫男主角说出了自己的弱势真相。
随即,医生给出了自己的要求,不由分说地只给了三毫克阿片类药物。
这对应着男主角在现实层面的出路:弱势地接受,放弃毒品与幻觉,同时也意味着对情爱关系中弱势地位的接受,接受伴侣让自己戒毒的要求,以此换取伴侣的满意,从而延续这段关系。
但是,如同自己叙述的那样,同性情爱的受挫才是男主角来到南美洲的根本缘由,因此他不能放弃对自身强势地位的“幻觉”,这关系到他对同性恋观念本身的坚定与否,必须树立自己对外、对情爱对象的强势,将伴侣从双性恋变成绝对的同性恋、所谓的“接受真实自我”,以引领绝美的“极致同性爱化身”的方式,树立起自己对外部的强势同性恋者地位,反击一切外部主流环境。
因此,在医院段落的最后,观众通过镜头站在了医生的角度上,看到的却是男主角“三毫克怎么够用”的负面真相。
而当二人再次坐上巴士的时候,环境与关系也再次发生了恶化:二人甚至没有了日常环境里的局部阳光,而是完全处在阴影里,男主角给自己点烟,挑衅地弹了一下伴侣,自行给予“快感”,其强势也已经露出了“强行输出、暴力行为”的姿态,引发了伴侣的不满。
随着环境的再一次切换,二人进入了更加原始、自然的世界,暗示着对“死藤”的接近,瓜达尼诺也短暂地给出了片刻的完美时刻,作为对“死藤”理想效果的呈现:男主角靠近了死藤,似乎也拥有了死藤在想象中的控制思想、主导伴侣依附于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带着二人一起脱离了当代社会,在原始自然世界中摆脱一切主流观念的压制,让关系变得不可撼动。
但是,死藤不过是毒品的极致,这一切同样只是幻觉,只是其快感变得更加剧烈,甚至上升到了“现实化”的程度,但终究要衰退下去,而其内部也同样蕴含着“吸毒时麻木表情”所对应的“无法排除现实影响”,对应着二人关系在具体情节中的真实面流露,潜在地动摇着表面的男主角主导与完美延续。
首先,在自然环境的远景之下,伴侣露出了绝美的裸体,强烈地象征了同性情爱的高度实现,引出了二人在海水“自然世界”中的暧昧游动。
裸体意味着绝对的真实自我,海水则是自然环境与“羊水中的重生”,似乎让双方摆脱了此前现实环境中成长、受到束缚的人生,进入自然、摆脱当代,完成拥抱自我同性之心的新生。
但是,当他们上岸之后,男主角发出“喝点什么吗”的酒水邀请,却被伴侣无情拒绝,“我要在这里拍照”,记者的现实属性再次出现了。
随后,二人在房间里发生了性爱,男主角摆在桌上的手枪是其现实层面中强势形象的解除,表现为其抚摸伴侣、却停在半空的手,反倒是由伴侣指出“我以为你要摸我”,并攥住了男主角犹豫贴上的手,两次主导了肉体结合的发展过程。
男主角说出“你以为我是酷儿吗”,与他问询伴侣“有时候你也很享受”相结合,自己对同性身份有所否定,也不确信对伴侣的主导效果,反过来需要伴侣给予自己的肯定回应。
当二人最终性交的时候,镜头从肉体贴合的特写开始,移到了外面的世界,经过当代日常的街道,定格在自然的蓝天白云,意味着二人情爱“脱离当代、进入自然”之下的暂时达成,却是由伴侣主导、男主角一度试图主导而又被动摇的结果。
这些后半部的性爱内容,正是“死藤”的巨大幻觉,让男主角产生了“情爱关系可现实达成”的假象。
性爱段落的后续一段中,瓜达尼诺给出了完全反向的负面结果,让它微妙地成为了“性爱”本身的“高潮后续”,即毒品式性交在幻觉衰退之后的负面反应,带着男主角从幻觉回到了真实世界,面临“戒断反应”。
它等同于音乐的变化,后半部中此前始终持续的摇滚乐,与画面中持续的“情爱和谐”表面相结合,男主角沉浸于此心境愉悦之中,一直来到了环境自然化的“正面极致”,然后伴随着性交之“高潮”的结束,滑落到了客观现实的阶段。
特写镜头中,伴侣吃着肉食,“情爱自然”中的强动物身份得以确立,男主角的再次抚摸则被粗暴地推开,同时也在神经质地强调自我地位的时候,吐露了关于吸毒、被歧视、负面反应的弱势真相,最直观的示弱则是对情爱关系的“我知道,这违约了,我不应该这么快地再次上手”。
这引出了二人的分离,以及男主角在这种“情爱关系打破”之真实状态下的“独自直面真相”。
男主角自己坐在了飞机之上,环境是此前巴士的本质性升级,窗外是天空的绝对自然世界,引发的却是负面真相的升级,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带着空虚弱势的表情。
他想要寻找死藤,因此愈发深入死藤植物所在、排除当代主流观念与社会的自然,却也即将面对死藤并不如预期、只会导致死亡的真实结局,当代的排斥是无可逃离的,因为它已经深切地改变、扭曲了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失去了坚定而纯粹的同性情爱之心。
在他找到人问询死藤、得到其下落的关键段落,镜头反复强调着其身处的自然植物园环境,问询对象的口中却始终是现实的内容:海洛因、死藤不会让人产生欢愉、和你想的不一样,以及出于现实角度的怀疑,“你是中情局吗”,由此影射了美国在当时对墨西哥的强权遥控、镇压革命,将本片在前半部中象征“客观现实压迫”的政治环境要素再次激活,笼罩了此刻环境的自然世界之表面。
男主角得到了死藤的下落,却被告知“拥有死藤的女人与死藤都不如你所想”,而现实里的自然环境也随即变成了凶恶的大海,其深蓝色对应着前半部里的性爱发生环境,却不再是此前停留在局限性环境(房间)的美好,真实的一面即将到来。
电影的第三篇章,男主角带着伴侣真的深入森林,寻找死藤,原始自然世界让他彻底脱离了当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压制,似乎可以如同理想预设地那样去成为“动物”,获得同性爱丛林世界中的肉食强者地位,主导、引领伴侣去接纳自己与其自身的同性恋本心,这也正是死藤制造的“心灵感应”效果,让他能够与伴侣完全相通,以此掌控伴侣的心灵,走向同性恋,也达成精神与肉体的完全相合,即肉体的性爱交织与精神的情爱相通---在第一阶段,他在叠影的形式中触摸伴侣,以此完成了影子的“灵魂、精神”与肉体的同时触碰,由自身发出动作而形成了主导性,但伴侣并无回应,叠影也意味着他的个人精神妄想,且并不真正发生在肉体层面,只是无法长久的“灵魂游离”。
因此,他才需要深入丛林,获取死藤,将之转化为现实,将同性情爱的灵魂回归到肉身的完整现实之中。
灵魂游离在叠影的呈现手法中表现出的强主观性、虚幻性,也意味着其只能达成于非现实层面的短暂与虚无,并被男主角所认知,在他此前的“我灵魂游离”表达中处在“我不是酷儿”的后面,必须通过灵肉一体来获得现实世界维度的确切胜利,但死藤最终能给出的效果,也不过只是更高程度的灵魂游离而已。
由此一来,第三篇章就成为了“死藤反应”的现实具象,男主角进入了其世界,从头到尾都处在“反应”之中,是其主观追求在现实维度里的落地,也由此呈现出了现实中的受容状态。
在这个落地于现实世界的森林之中,他的表现、遭遇、最终结果,都与纯精神构想中的美好背道而驰,死藤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心灵感应,只能制造幻觉,并同所有毒品一样地过度使用、引发消极反应、最终死亡。
整个森林篇章就是男主角的主观世界,是其在现实里的个人追求,以及追求达到极致程度之后的致命打击,随之变成了被现实挫败之后的消极主观反应:理想的破灭感,对现实的臣服。
在二人靠近“死藤”的部分中,瓜达尼诺几乎放弃了前两篇章中的音乐,让男主角不再雀跃或缠绵,始终处在惊悚的音乐与心境之中,就此直观地扭转了前两篇章里的积极状态,他越接近理想的达成目的地,反而越在其反向的真相中陷入深渊。
第三篇章的开始,这种惊悚的音乐伴随着二人深入丛林的画面,以及狰狞自然世界的远景,正是对此的表现。
而在他们找到了植物学家之后,性取向更是形成了潜在的对立关系,同步于男主角与植物学家的暗中角力,并被放置在自然的大背景环境之中,成为了“动物竞逐”的行为,以此全层面地破除了男主角在此前建立的一切。
他们共处的森林中小屋,就是原始森林与动物世界的舞台。
在其中,植物学家是女性,与男性保持着异性恋的关系,又强势地“引导”着伴侣,不仅是话语的发号施令,在动作上也经常主动拥抱,甚至强拉伴侣到自己身边。
于是,异性恋中的女强,就成为了植物学家二人组的属性,男主角二人组的同性恋、男主角主导的“强势”,则与之对立,相互试探、角力,形成了性取向、性别层面上的比拼,等同于对这个世界掌控权的争夺。
在最初相遇的时候,男主角被吓了一跳,对植物学家的镜头始终以枪口的角度出发,后者的强势地位已然明确,“枪”作为墨西哥混乱时局之当代社会中强势地位的符号寓意,也从男主角身上被剥夺了,意味着他在当代与自然中的同步弱势。
四人聚餐,“肉食”的要素再次出现,与对话的进程、构图的设计相结合,搭建出了多层的“食物链体系”:作为明面上的各自强势者,男主角与植物学家对话,打着喜欢伴侣研究的借口,试探死藤的下落,但他需要用“俄罗斯和美国的实验”作为掩护,已然暗示了其“脱离压制自己的当代时局”的不得,神经质大笑的状态也与此前勉强拉拢伴侣、展现强势的状态一致。
相对地,植物学家虽然放下了枪,却始终带着更扎实的危险感,就像是丛林中的肉食动物一样,似乎时刻要将男主角一枪击毙,翻脸不认人,有着更强的“融入自然、成为丛林强势者”的意味,压制了“无法彻底自然化、勉强支撑强势”的男主角。
这也体现在了二人的肢体动作与性别层面,植物学家会强势地拉过男主角,与他相拥、碰头,也始终掌控着自己一边的话语权,丈夫似乎只是自己的附庸,意味着女性对男性的压制,“女强”异性恋对“男主角强”同性恋的压制,甚至强势地引导了男主角对异性亲密行为的被迫接受。
男主角想要用死藤引导伴侣的同性恋,在靠近死藤时却反而被引导到了反同性恋。
并且,在“肉食吃饭”的象征性表达中,男主角始终没有吃一口,植物学家等人则始终在吃,特别是伴侣与植物学家丈夫的状态,更拓宽了“情爱食物链”的范围:镜头带到了二人的对视,伴侣对丈夫报以微笑,形成了隐秘的同性情愫,伴侣在其中占据了实质的主导性,对应着他对男主角同样的主导地位,且由此刻二人是否肉食的区别所暗示。
于是,同性恋大于异性恋,女强大于男强,而在男性同性恋的内部,伴侣则在眉目传情的“出轨”中脱离了男主角的表面掌控,成为了相对上层的强势存在,而男主角甚至在“肉食”层面上弱于植物学家的丈夫,成为了最低的弱者。
在这一段中,瓜达尼诺完全放弃了个人标志性的游移运镜,也切断了其表现的暧昧流动之情愫,完全使用固定镜头、等同景别、单人到全景切换的流程,也放弃了音乐的烘托,极度强化了此刻对男主角---全片主观性环境的主要来源---的绝对冰冷、无情感,将这个场景变成了“只有杀戮”的原始丛林,与男主角想要的“实现同性爱之丛林”背道而驰,而他在其中则是最弱的动物,唯一的情愫发生在伴侣与他人之间,割裂出了男主角主观性构成的整体场景,爱情也并未投注在他的身上,甚至是对他表面掌控的背叛。
瓜达尼诺也设计了构图。
画面中始终存在着柱子,打破了构图的和谐,让男主角此刻对局面与话语权的努力掌控被弱化了,也隔断了他与伴侣,而在另一边,植物学家与丈夫一起出现的画面中,柱子直接遮蔽了丈夫的身影,且并未完全挡在二人之间,意味着植物学家对丈夫精神心智的无阻隔、以及“遮蔽其独立存在”的更强掌控力,植物学家与男主角的高下、男主角与伴侣的高下,就此得到了暗示。
在这一段的最后,植物学家强势地拥抱了男主角,男主角只能报以尴尬而神经质的笑声,随后被伴侣重新拿起枪、威慑着离开,表里的强弱关系得到了最确切的表现。
而在段落的进行中,镜头不时带到墙上的猫头鹰,伴侣也瞥到了它,随后“勾引”丈夫。
这定义了环境的自然丛林属性,也让伴侣与猫头鹰联系在一起,在对视中形成了人与动物的心灵共通,让自己贴近了动物,随后才完成了有效的“男男心灵共通”。
他通过对视的同性爱意输出,实质上成为了“同性情爱森林”里的强势动物。
这正是男主角理想中死藤的效果,也形成了与第一阶段中类似段落的对比:男主角与同性友人在酒吧之中,身后是动物标本,男主角却无视了它,由此不具有对“动物”的共通与贴近,如同此刻环境中动物的“死状”、而非第三篇章的“活物”,象征着他只能停留于当代社会与“人类形态”,输出的同性表达也只是神经质而已,最后被“冷冻”成了黑白的纸片状。
跨度极大的对比,证明了男主角之于伴侣的又一次弱势。
在第三篇章中,瓜达尼诺同样给出了男主角拥有的心灵共通,却是以负面、弱势、与理想相悖的形式出现。
次日,男主角再次与植物学家谈论死藤,“对研究感兴趣”的伪装已经被干脆地戳穿,段落开始时被枪威逼的状态也让他处在了明确的弱势地位,反复接受着植物学家的强势爱抚,只能以神经质的强势表演回击。
当对话深入到“死藤用处”的关键时刻,瓜达尼诺给出了第一人称视角,中断了整体的男主角主观性环境,切到了植物学家的主观角度。
此前,他两次给出了伴侣的POV或类POV(越肩镜头)画面,完成了对男主角“落在他人眼中”的客观真容表现,也以此弱化了男主角对场景与画面的主观性掌控之“强势”,对应着他对同性情爱、伴侣心智与去向、自身之于社会主流观念的强势追求之动摇。
在这里,植物学家拿到了主观性视角的权限,再次弱化了男主角的力量,且在居高临下的俯拍角度中形成了之于此前POV的再升级,将其眼中几乎无法保持神经质逞强的男主角削弱到了极致。
这也契合了此刻的内容,男主角的“对研究感兴趣”借口被戳破,随后更是被告知了“死藤不会产生,你其实知道的”这一真相,同性追求与自身强势、掌控伴侣的心愿被击毁了。
此外,POV镜头从被迫承认“心灵感应”目标的男主角身上移开,在他与伴侣的身上游移,这让植物学家意识到了男主角的所图,即对其的“心灵感应”。
男主角似乎达成了它,却并非如所愿地发生在自己主导、与伴侣之间,自己的状态是尴尬而被迫的“被单方面窥探出客观真相”,更让出了第一视角的权限,成为了绝对的弱势接受方。
这也让人想到了第一阶段中的伴侣POV镜头,在男主角的打字机与毒品盒之间游移,单方面地窥探到了男主角”追求只是幻觉”的真相。
并且,第一视角的画面也与此前段落结尾的“猫头鹰凝视一切”特写产生了延续性:动物凝视一切,是场景中的最有力存在,第一人称POV视角的拥有者便是这样的“动物”,正是此刻的植物学家,并在多层面寓意中压制了弱小的男主角。
最终,植物学家对男主角的多层面压制、削弱,落在了死藤真实作用的表现之上。
瓜达尼诺给出了相当具有嘲讽性的一幕,死藤其实无处不在,构成了男主角所处的环境,他却对此一无所知,也并未从该环境中感受到任何想要的效果。
植物学家把死藤扔给了他,镜头久违地变成了升格镜头的“移动运镜”处理,却是此前暧昧情愫渲染的反向,极度迟缓、滞涩,让愕然中接过死藤的男主角流露出负面的心境,感知到了死藤不如其所想所知、无法引发其目标的真相。
随后,瓜达尼诺直观地给出了二人对死藤的吸食与效果。
他们接受了极度原始的部落宗教仪式,似乎由此在文化、社会维度上彻底脱离了当代人文社会,进入了“原始森林”,脱下了象征当代观念束缚的条纹衬衫,完全赤裸,并吸取了纯植物毒品的死藤。
但是,这并没有让他们拥有摆脱当代社会观念压制的“同性爱圆满”,一切追求的效果都以负面的方式出现:在冰冷的固定长镜头之中,二人的同性爱在情感心灵层面的共通、甚至其本身的存在,都被压抑到了极限,让他们倍感痛苦,先是被木架所隔离(共通的割裂),随后更是吐出了心脏。
这是极其大胆的一幕,二人血淋淋的心脏被并置在地上跳动,以此完成了物质形式的“共通”,却与男主角追求的心灵层面完全不相干,温暖的“心灵”爱情也被鲜血淋漓的器官“物质”所取代。
吐出心脏的一幕,是“心灵共通”的物质形式达成,对应着同性爱追求、引导彼此心灵解放与接受同性自我,其在物质现实维度之中的落地,却完全是男主角之理想的反向。
此外,瓜达尼诺也展示了更加精神层面的效果,它接近于男主角二人在吸食死藤毒品之后的幻觉,是物质层面的肉体生理反应,即现实里的精神达成形式;吸毒过量的幻觉。
二人赤裸地共舞,不停地掰过伴侣的头,以此完成“对视”的“心灵共通”。
在第一阶段的性爱中,男主角进入了“二人把玩空稿纸超能力”的幻觉,稿纸在他们之间不停移动,象征着“精神共通”,却并未写有任何文字,暗示着男主角作为作家、以写作输出自身主观心境的“失败”,此时的精神共通正是他的主观追求,空白纸张也就意味着共通内容的虚无。
而在这里,当他们共舞的时候,无疑处在了明确的“共有幻觉”里,切实地拥有了共享的内容。
在他们最终相拥的时候,手臂直接进入了彼此的身体,并撑出了明显的手臂轮廓,由此在画面中呈现出了“叠影”(灵魂游离)的效果。
这是瓜达尼诺颇见灵气的设计,在第一阶段中,男主角在叠影里爱抚伴侣的脸颊,以此表现了精神层面对情爱共通的渴求,也与物质现实明显区分开来,而在吸入死藤之后,“叠影”以现实维度的形式出现,对应着二人的确实相拥,让男主角的理想似乎不再是单纯的精神幻想,完全进入了现实,从“灵魂游离”变成了“灵肉合体”,但这一切的“实现”本身其实就是他吸入死藤之后的幻觉,也引出了随后的“幻觉消退”,即第二篇章中反复展示的负面反应阶段;二人的裸体沾满了泥巴,承受了现实中自然世界对“美好裸体性爱”的削弱,他们的状态也极度低沉,仿佛短暂性爱与毒品快感之后的贤者时间,在固定镜头的正反打中完全冷却,随后则是精神层面本身的“真相”。
伴侣说出了“我不是酷儿”,打破了男主角对他的引导、掌控努力,男主角对此则毫无波动,最终归于二人身形的逐渐淡化、消失,这正是现实维度里的又一次“叠影”,彻底颠覆了第一阶段里的“持续存在”,去到了“灵魂游离无法持续”的最终结果,且其形象自身也变成了情爱的冷却、终结,表现着人物“灵魂与内心”本身的受挫,再次印证了此前积极高潮、情爱达成的短暂。
虚影是此刻人物口中的“游魂”,发生情爱的裸体即精神追求的具象现实化,最终在此刻完全消失。
镜头反复给到了燃烧的篝火,是情爱的火焰,在此刻却无法扭转二人身影的消失,是非常明确的“幻觉消退时刻”。
随后,这一切更是完全地消失了。
赤裸的二人极度冷淡,代表当代社会束缚的衣服已经去除,也身处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却无法延续死藤的效果,迎来了理想寄托死藤不如预想之下的归于现实,毫无性爱欲望地草草入睡。
镜头在二人之间移动,从男主角移到伴侣的身上,以此强调了实质性主导者的归属:伴侣的一句“我不是酷儿”才真正打破了男主角的希望与二人的关系,而男主角在第一阶段中同样在幻觉中自白,则没有这样的一锤定音,只是暴露了他个人的内心受缚而已。
而在最后一个镜头中,二人的共眠被倒置构图,意味着关系的被颠覆,而作为主导者的伴侣则流下了眼泪,给出了最有力的“结果宣示”。
这层内容延续到了第二天的篇章结尾处。
在正反打的对比之中,伴侣与植物学家处在同一画面,而男主角则被孤立于一旁的单独画面,以此强调了前者之于植物学家的“同等主导者”属性,同时又由伴侣在构图中的相对低身位,表明了伴侣与植物学家的内部强弱,作为女性、异性恋者的植物学家压过了男性同性恋的伴侣。
这同样体现在了双方之于“死藤”与自然环境的态度之上。
植物学家建议二人留下来,因为对死藤在初次使用后即有反应,非常难得,而心灵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只能尽力无视而非抹除。
这揭示了二人在最后的走向,对死藤的敏感让他们成为了当代社会中最极致的同性恋者,能达成最强的心灵情感共通,但即使是他们,也终究无法长期停留在自然世界与死藤环绕之中,而是充分意识到死藤的幻觉属性,认知到其不可持续,由此被沉重打击,选择回到当代社会,而非一直停留在幻觉与死藤之中---这是对于“毒品”与“同性恋”的一种“理性清醒认知”,对应着他们接受的当代主流观念束缚,终究没能完全脱离而出。
由此一来,男主角与伴侣就没能战胜主流社会的传统观念,始终受缚于此,放弃了现实人生里的个人追求,接受了同性情爱的“消失”。
而他们已经是世界中最为强力的同性爱者,其失败无疑是整体同性爱的失败。
具体到男主角的身上,他作为明面上的主导者、坚定者,最终暴露出非主导、强势的弱者本质,受到了伴侣的主导,失败于“引导伴侣完全接受同性爱的自我”,反过来被伴侣引导了自身的“放弃自我”,更是消极落点的更有力表现。
在他们离开自然世界的时候,镜头先是停留在植物学家先站在高处、随后揽过丈夫的身影上,目送着他们的远离,让女性主导的异性恋成为了自然世界里可扎根的唯一存在,而同性恋者则只能远离伴侣走在前面,引领着弱势的男主角,让他一步步地回到当代社会,自然环境也转为了刺伤他的负面存在,其结果则是“同性爱”本身的消失:伴侣的身影淡化、消失在了现实氛围的环境之中,其绝美身姿象征的“完美同性爱”从男主角的现实人生里离开,而其消失方式是“叠影”的淡化,即个人妄想、“毒品幻觉”的消退。
他选择回到当代社会之中,承认同性爱在现实里的本质,只是暂时维持的完美幻觉,随后更长久的结果则是毒品过量“死亡”象征的“自身被主流社会毁灭”,因此必须放弃。
在第三篇章的结尾到第四篇章的部分,瓜达尼诺完全放开了创作的自由度,呈现风格让人想到了帕索里尼、费里尼、以及70年代大卫柯南伯格的电影,极度地抽象化、象征性。
他直接呈现着男主角的内心世界,并在风格的加持之下,强化了它的“毒品致幻”意味,光怪陆离、跳跃碎片、欠缺连贯,是吸毒之后的迷蒙梦境。
这是风格化的内心呈现,也与本片密切贴合,意味着男主角对毒品与其象征“同性爱”的无法摆脱,即使回到了当代社会,甚至自行承认幻觉危害与不可持续、能动性强烈地做出选择,也终究无法完全消除内心的自我。
他在理性上明知是“恶性幻觉”,却依然克制不住触碰它的感性冲动,对毒品的无法戒断也正是对同性爱的不能放手---植物学家对他们的判断,“吸入死藤之后,心灵之门一旦打开,就无法闭合,只能强行无视”,正是对第四篇章中男主角结局的揭示,她告知了伴侣,伴侣则作为强势者,主导了男主角的命运。
在第三篇章的结尾,高度的风格化已经出现。
男主角看到了伴侣的“淡化消失”,即内心中对“同性爱幻觉”的放弃,但随着他迅速抬头的视线,镜头快速上摇,去到了天外宇宙,白天迅速变成了黑夜。
男主角的视线让这一内容具备了主观性,表现着其内心世界在“放弃同性爱”之后的反应,其内容是对前半部中“黑夜变成白天”的快速蒙太奇的再现,黑夜原本是同性爱达成的部分,白天则是对此的“当代日常化取代”,而到了第四篇章的开头部分,快速蒙太奇的进程逆向,却无比短暂,男主角从黑夜的天上掉落下来,落在了白天的海边---“黑夜”更加短暂,当代现实的力量愈发加强,构成了男主角的投降,但黑夜并未完全消失,即男主角内心中同性爱的残留。
男主角从天上坠落到海岸,抽象地表明了一种“灵魂落到凡人世界”的“回归肉体”之意,此前的同性爱被称为“灵魂游离”,而放弃同性爱之后的此刻则是反向的“灵魂回归肉体”。
他经历了“灵魂游离”不可持续之现实、更无法达成正面“灵肉合一”之后,接受了反向现实,并回归客观世界。
物质层面确切存在的肉体只能存在于当代社会的现实之中,而脱离社会、进入自然、吸收死藤的整个第三篇章,其整体就是一次吸食毒品、获取幻觉、同性爱似乎可达成的“灵魂游离”之旅。
镜头强调了男主角站在自然界沙石之上的状态,此时的海岸处在白天日光的“日常化”(前半部里白天的街道与酒吧)与风平浪静之中,对比着第三篇章开始时的午夜海岸、惊涛骇浪,让男主角站在了第三篇章的反向起点,从自然世界的同性爱幻觉中走回到当代人文社会的客观现实,而自然世界本身也随着他对同性爱的放弃而被现实的日常化环境所同化了。
从离开森林到篇章结尾,男主角穿回了当代的衣服,不再是第三篇章的裸体,同样是对其状态的表现。
但是,男主角并未完全抹除同性爱的渴望,他只是尚未察觉到这一点,在时机来到的时候依然会不自觉地进入到幻觉之中,哪怕没有吸毒也会如此。
对同性爱之幻觉的抹除、复现,即是第四篇章的内容,给出了多次循环往复的过程,以次数加深了男主角对“同性爱毒品”的愈发深陷,与表面上的“放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观上已经想要割断它,却终究抗拒不了最本质的自我,只能沉浸在其在当代现实环境的受挫与痛苦之中,无法达成它,也无法彻底终结其失败。
第四篇章的开头,“两年后”的标题似乎意味着一切的物是人非、重头来过。
但是,男主角走出了海岸,其背后的照相机却表明了未变的东西,伴侣此前用照相机工作,记者身份是其当代社会属性,在此刻加持在了男主角的身上,而它又表现出了男主角对伴侣的旧情难忘,由此形成了完整的暗示:既难以割舍同性爱人,又不免受缚于其当代属性,结果便是与其在此时的被迫分离。
这样的男主角走入了第四篇章之中,将自己的状态进一步地展开、呈现出来。
他再次进入了当年的同性酒吧,却是白天的日常化氛围,曾经属于夜晚的同性情爱荡然无存,中景为主的固定镜头,空旷的酒吧室内环境,肥胖的“不完美同性爱”友人,其从厕所走出、整理裤链的“不美”,都是对情爱美妙氛围的打破。
男主角与友人对话,谈到了曾经朋友们的离开,以及伴侣的远赴他国,尽量地装作若无其事,却依然是当年的神经质、强撑欢笑,并没有真正割舍掉以伴侣为首的同性爱生活中的一切,只是当年的“强撑同性爱中强势者”变成了此时的“强撑放弃同性爱”,是更加消极、臣服于现实的勉强,不变的则是纠结的痛苦,无法处于同性与主流之两极中的任何一方、完全成为其方向的纯粹者。
友人揭穿了他“我不在意”的谎言,逼迫他承认这一点,镜头最终切到了室外的街头,而酒吧中的二人则成为了被其日常环境笼罩的局部存在。
前半部里的类似构图同样有所运用,表现的局部存在是情爱时刻,在这里同样被颠覆,内外都归于当代现实一方,意味着其局部作为“暂时幻觉”的消失。
但是,男主角并没有完全融入这样的日常环境,而是迅速回到了幻觉的世界。
瓜达尼诺几乎是“超量”地设计了影片的结尾,多次给出了幻觉的破除与再生,每一次的节点都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全片的完结感,似乎已经是足够有力的点题,随即却又迎来了下一段的循环,作为“状态往复、痛苦持续”的再次叠加。
首先,男主角躺在床上,房间变成了午夜中的红色,正是他与伴侣第一次性爱的“情色之红”与具体场所。
他无法控制自己回到这里,却只能孤身一人。
镜头带到了摘下的眼镜和帽子,这是当代社会“束缚”的象征,即对于裸体之绝对真实的“覆盖”,特别是眼镜,在大部分时间里被人物佩戴着,性爱时刻被“打落”,在第三篇章的幻觉中被摘下,篇章结尾则又被二人戴回。
而在这里,男主角摘下了眼镜,却依然身穿着西装,由此强化了自身之于裸体与当代穿着而同等的不纯粹,无法彻底归于现实或“主观情爱世界”。
他掏向怀中的手枪,则是又一次的“混合象征”,手枪是他面对当代现实---墨西哥政治运动环境---的强力凭依,让他能够战胜主流社会的观念,也主导伴侣的内心与二人关系(每次性爱时都会摆出手枪)。
他在结尾处再次试图掏出手枪,依然想要在当代实现自身强势的同性爱,却没能拿出来,正是一种象征:他没能让自己脱离现实与同性爱的任一方,依然想要达成二者的混合,哪怕已经明知其不可行,“强力”符号也就无从出现。
由此一来,男主角在“黑夜、红色光线、房间”的现实中迎来了强势地位与同性追求的再次失败,随之进入了更深一层的主观世界之中,这是他的“幻觉”,是现实受挫之后的一种反应,对应着第一篇章结尾处“被伴侣拒绝后吸毒”的部分。
他看到了微缩模型的房间,其内部亮灯、外部整体黑夜的状态,正是前半部里情爱局部达成的相对实现,此刻的他在绝对现实里受挫,渴望着在幻觉中达成曾经的美好,哪怕只是短暂而局限的存在,也想将此房间带回到前半部里的状态。
对模型公寓楼的窥视,在其眼中的自己走过红色更加满溢的走廊、再次进入房间,是确切无疑的表现。
然而,即使在此刻的绝对幻觉世界中,同性爱依然只能以一种无法延续到底、反复被打破的消极状态而出现,打破者正是男主角自己。
他已经承认了同性爱的不可实现与持续,由此形成了“亲手打破”的主观世界内容,但又在感性的部分中没能彻底割舍掉渴望,由此导致了“再次出现”的内容部分。
瓜达尼诺的呈现是丰富的,每一次的循环都有着独立的呈现形式。
首先,男主角看到了盘成“无限”符号样貌的蛇,蛇是自然世界的存在,让房间回到了其环境,而符号则是对称的形状,对应着此前幻觉里的“游移于二者之间的稿纸”,似乎带来了“无限”的绝对积极支撑:放弃强弱势的不平等,在平等中实现同性爱的无限可持续之达成。
但是,当镜头给到蛇的特写时,蛇流出了眼泪,这是第三篇章之中,伴侣在幻觉终结、二人冷漠入睡时、作为段落终点的动作。
因此,蛇成为了伴侣,且再次地给出了由其眼泪所主导、判定二人关系与同性态度的消极结局,平等与实现被打破了。
随后,男主角明确地看到了伴侣,孤身躺倒的状态仿佛是尸体横陈,也并非与男主角的同床,形成了对第三篇章结尾处“冷漠同床,流下眼泪”的再次升级,而其佩戴的蝎子吊坠在蠕动,更是以沙漠中强势动物的形式象征了其在“同性关系森林”中的强者地位。
男主角试图反击,宣示自己的强势主导,也由此逆转伴侣主导之下的死亡、孤身之消极,但具体行为只能是掏出手枪,将一切带回到当代现实社会(甚至是墨西哥政治的程度)的情境之中。
于是,男主角再次“回到”了方才的现实房间,再次试图掏出手枪去抵抗“孤身在床”(现实里的他自己,幻觉里的伴侣)的消极现状,也强调自己的主导地位,带来的则必然是再次的“现实中失败”而已,因为他自己的理性便早早地承认了这一切。
作为对此的表现,瓜达尼诺明显地借用了大卫柯南伯格在《裸体午餐》之中的桥段。
如同柯南伯格让男主角去射击女伴头上的苹果一样,伴侣将酒杯放在头上,让男主角掏枪射击酒杯,自己却被击中,酒杯滚到了男主角的脚边。
酒杯是片中“引导同性传情”的载体,男主角为伴侣倒酒,反向的则是他给自己倒酒,一直到第四篇章开头酒吧中的“彻底归于自斟自饮”。
而在此刻的幻觉之中,伴侣拿出了酒杯,诱导男主角的射杀,以此完成了对男主角的强力引导,而男主角的掏枪射击则只是表面上的“强势”而已,反而因其牵扯的当代属性,导致了主观世界之幻觉中的实质性弱势---他无法摆脱当代主流观念的束缚与压制,那么承载其暂时寄情的“毒品幻觉”、主观世界,也就同样不能给出完美的状态,而是随着他相比于第一篇章的更加受缚、甚至投降,更进一步地动摇,不再能保持哪怕一时的美好景象。
受困于当代主流环境、无法摆脱强势宣示、始终纠缠于同性渴求,就此混合出了男主角在此刻的掏枪与其结果:他是实质上的弱势者,无法主导象征“完美同性爱”的伴侣,反过来被其主导,诱发了“亲手击碎一切”的开枪射杀,而滚动到他脚边的空酒杯更是微妙的象征物,其滚动方向、伴侣拿到头顶的“诱导射击行为”,构成了伴侣对男主角的强力引导,也是酒杯一贯的寓意,在二人之间传递所象征的“情爱引导”,但它又是空的,由此象征了同性情爱本身的虚无化。
此前的男主角尚可在不同程度的“幻觉”---现实里的暂时实现,现实里的吸毒致幻,暂时走出现实的个人妄想---中得到同性爱的体验,或自己饮用并传导给伴侣,或至少是自斟自饮,在结尾却完全落入了伴侣的掌控之中,无奈地接到了空空如也的酒杯。
伴侣主导了同性情爱的“消除”,从酒水到引诱男主角射杀自己,这发生在男主角的主观世界之中,说明了他根深蒂固的弱势自我认知,明白自己不足以压制主流观念、在当代社会中取胜,由此意识到自己无法“主导、掌控完美同性爱”,只能反过来被“同性爱”的受挫状态---做出决定并引领二人离开森林的伴侣---所主导,弱势地接受其消极结果。
他始终在努力地争取,直到结尾也是如此,其主观能动的行为却只能带来“亲手抹杀”的结局而已。
而当他拥抱着伴侣的尸体哭泣的时候,又流露出了“投降于现实”之外的内心部分,依然不能真正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失败,依然留恋于同性之爱,因此会不停地为其破灭而悲痛,循环地深陷在这种“欲求而不得”的往复痛苦之中。
在这一段中,瓜达尼诺安排了数个节点,引导着一种似乎积极的转折,旋即又打迅速地打破了它,这种设计甚至作用于观众对这类艺术片表达方式的既有经验。
男主角看到蛇,蛇流下眼泪,这可以是影片的消极结局,因为伴侣化成了蛇,只能以动物形态“达成圆满”,但男主角抬头又看到了人类形态的伴侣,由此引出了积极的上扬,随后,伴侣是“死尸”的状态,又是一个消极结局的落点,但当男主角转头、画面剪辑之下,听到了动静,伴侣又复活、坐在了床边,然后才是这一小段的真正消极结局,男主角被伴侣引导着开枪射杀,悲痛哭泣。
这种循环往复的设计是对于“不可消除的情爱追求,不可实现的追求结果”之痛苦轮回的叠加强化,又非常精妙地契合着核心艺术片观众的观影经验与学识水平,堪称瓜达尼诺的一种个人趣味。
至于趣味中的最重要部分,无疑是对柯南伯格《裸体午餐》的借用。
看过它的观众都会记得“女主角头顶苹果,被男主角射杀”的段落,也会从柯南伯格的表达中准确掌握其主题。
反复的射杀段落,男主角反复地摆脱毒品依赖,抵抗毒品带来的欲望满足,随之走出毒品制造的幻觉(欲望的可满足),世界反复地在清醒的现实与吸毒的致幻之中轮转,甚至逐渐以“现实中人披着他人半身皮”等形式,愈发混杂起来,直到男主角似乎彻底放弃了毒品,现实环境也持续地“清醒”起来。
但到了结尾,苹果与射杀的段落再次出现,同时伴随着又一次的“问路”桥段,男主角开着车再次询问“这是哪”,苏联军官打扮、带有强烈现实政治世界意味的路人则再次回答了毒品王国所在地的地名,由此让男主角在全篇中的“戒毒旅程”失去了意义,最终还是开车回到了毒品的世界,这甚至成为了此前现实世界的延续,意味着“毒品依赖”在绝对现实里的无法摆脱,它诱发了人类本性中对欲望的极致渴求,“沉沦于欲望”本身便是现实,随之的后续现实结果则是结尾段落的冰冷雪地、苏联军人、射杀女主角所对应的“消极”---象征欲望的苹果会被射击,人的欲望必然是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人只能不停填充着它,并不停地面对无法填满的痛苦,追求的后续正是“意识到其不可填满的现实”,即“射击苹果”。
而在《酷儿》中,除了射击段落并未多次使用之外,瓜达尼诺显然是细致地重现了《裸体午餐》的结尾设计,从大的思路到小的细节---如酒杯对应苹果的寓意承载---都逐一贴合,也由此引领了观众对本片主题、“主观性世界”等呈现手法的理解。
当然,瓜达尼诺并非只是照抄《裸体午餐》,全片的表达系统显然出自其个人,哪怕是第四篇章里的“照抄”部分,也有着鲜明的独立操作部分,通过突兀的剪辑节奏、单人构图、人物姿态,渲染出了诡异到恐怖片的氛围,对应着主题层面的表达,让前半部里的“同性爱达成”之美梦变成了此刻的噩梦,其氛围的无逻辑、跳跃、突如其来的惊悚,包括刻意的顶光,正是标准的噩梦质感。
音乐同样如此,前两篇章里的轻快摇滚、温柔抒情,经过了第三篇章里“冷淡入睡”时的幽怨伤感、爱情受挫,以及裸体共舞时的皈依惊吓、打破美好,在第四篇章的开头,以轻快摇滚再次起始,暗示着男主角彻底回归现实后的表面解脱,旋即又回到了幻觉复现之后的诡异部分,最终落于结尾的伤感。
对音乐的使用,从成作品的名曲到渲染式的音调旋律,以前者的创作者与作品寓意、后者的感性作用,引导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微妙而细致地把握住作品中复杂、纠缠、不断细微变化的内心层面与曲线,显然是瓜达尼诺自己具备的一贯长项。
瓜达尼诺回到了独立的表达之中,给出了多年之后的男主角。
他垂垂老矣,自身已经彻底变成了丑陋、衰败的弱势与“不美好”同性恋者形象,重新回到已然绝对日常化的房间,后景的窗户映出了白天自然光线的日常世界,升空的飞机暗示着“离开美国同性恋者的聚集地(躲避本土社会打压而来到的墨西哥)”,但他并未坐上飞机,飞机只会载着此前大家口中的“回国朋友”而离开,由此让他成为了留在同性爱追求之世界的存在,哪怕所处世界已经彻底当代现实化。
而他也只是再次收获了痛苦而已,在客观的维度中只能孤身躺在床上,伴侣的大腿、二人的交织,只能在腿部局限的画面中出现,正是他在现实中强行为之的个人幻想,且因为当代现实彻底化之下的打压升级,幻象也变成了“无法呈现完整二人”的更加受制状态。
这让他的痛苦再次升级,与此前的第四篇章内容连接在一起,不断地重建又破灭,形成了一种同性爱之幻觉无法解除的情况下、其与现实程度同步上升的痛苦无限攀升。
这也正是此前蛇给出的“无限”符号所带有的真正含义,并非同性爱终于达成--哪怕是幻觉之中---的“无限”,反而是其挫败痛苦不断升级之螺旋的无限。
作品的四个篇章架构非常规整,实际上形成了对男主角主观世界---其“吸毒”之后的感受反应渐变过程的各阶段表现,他对同性情爱实现的追求正是一种“吸食毒品”。
在第一篇章的“情爱达成”中,他处在暂时的圆满幻觉,在第二篇章的“幻觉消失”后迎来现实里的“负面反应”阶段,即“对药品的代谢”,随后则是完整真相的第三阶段,让他与观众一起看到了“吸毒幻觉”本身的真实样貌,承认其无法改变的暂时与虚无,主观性的世界也由此变为消极的调性,对应着他对“毒品”的最终态度,最后落于结果的第四阶段,彻底认清现实后的进入现实,并给出“认清也无用、只能深受痛苦”的现实人生、命运结局。
瓜达尼诺表现了同性恋世界内部的相对强弱势,更外延到了墨西哥整体社会的外部,并由其具体情境而落实。
七十年代的墨西哥处于社会动乱、暴力革命的历史时期,由此成为了“动物世界”的具体呈现平台,而男主角在内的所有同性恋者都成为了对暗号交流、偷偷开房才能维系的弱势者,且因外族身份而直观地被“主流社会”所隔绝、冲突,只有伴侣是永远冷静、恒定的真正强势存在,看上去被带入了同性恋世界,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内心坚定、情绪平稳,保持了外在与内在共同指向的“绝美姿态”,成为同性恋世界的完美符号,引导了男主角在内的所有同性恋者,走向无掩饰与克制的极致自由情爱人生。
这也构成了同性恋世界与外部社会世界的对应,同性恋的自由正是民间运动所追求的自由,双方在大部分时间互相冲突,而如果男主角对恋爱与同性恋之心的彻底接受,能够与墨西哥运动的成功保持同步,就扭转了他之于世界的被隔绝,变成了对后者的一种融入,由此给影片带来了真正的主题寓意,即对于同性恋者“解开传统束缚”的呼吁,以及自由性取向、纯粹性情爱之未来的乐观态度。
这部电影是威廉巴勒斯的半自传体小说改编之作,巴勒斯对毒品的沉浸,在美国六十年代的消极现实之中,以毒品和滥交等暂时快感支撑着美好的幻觉,以此对抗自身的“垮掉”,以及其对文学创作的自我心境之寄托,完全契合了本片的“强主观性风格之系统,以及表意的内容所指。
它就像是当代版本的《裸体午餐》,同样是整个世界的主观化,对吸毒幻觉的现实落地,其相关性绝不仅仅是“打字机要素”的程度。
瓜达尼诺之于《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更进一步尝试,围绕着同性恋题材、纠缠的情爱关系、同性之心的引导与诱发之“角力”,构建起了全片,并用极度强调心境、情爱之质感的声画技巧呈现出来,主题的表现从“绝对封闭、聚焦二人”扩展到了更外部,涉及更具体的某一国家、民族、社会形态、特定历史时期,从而强化了压制人物、引发其“不够直面同性取向之自我人生”、需要他人引导而又抵触、持续纠缠状态的主流传统社会的存在感,让它以具体的形式与人物发生冲突性的交互。
在传统眼光与观看方式之中,它会显得非常怪异,每个段落里的剧情都显得单薄,人物只是在谈论着一些非常独立、片段,甚至强行“直抒胸臆与过往经历”的内容,由此便直接诱发了亲密等极端情绪反应,而段落串联起来就更显得突兀,整体剧情过于单薄,似乎不足以支撑人物的复杂关系与缠绵心绪,但它的叙事重点恰恰在于声画本身,其直接输出情感线条与质感的形式才是“叙事核心”,而传统意义上的剧情叙述则只提供对其情感的“定义注解”,是辅助性的存在。
它颠倒了剧情与声画在传统剧情电影里的主次地位,于瓜达尼诺自身而言的实验、拓展性也比较强,呈现效果也不算差。
并且,这种实验也体现在了对演员的使用之上,丹尼尔克雷格的表演带着有意的刻意、夸张,打底基础的强势,与愈发流露的敏感、脆弱、神经质相结合,同时又以其先天部分作为重要的加成,巨大成功的007形象无疑直接带来了英伦特工、资深情种的优雅与有力,更是情爱关系里的“主动引诱方”,也配合了克莱格本人的硬汉线条,这一切先天部分又在他的主动表演中被彻底颠覆,让人“大跌眼镜”,即人物出发的表里呈现。
它让人想到了那些最为先锋、实验的经典作品,仿佛诞生于灵感最多、表达方式最自由、最大胆、最尝试、最实验、最开拓独特表达方式的年代,既“复古”于电影风格的所处年份,又“超前”于电影表达的实验程度。
在很多人已经无法“消化”这种作品的当下,仍然愿意进行这样的创作与尝试,无疑需要瓜达尼诺的勇气,以及A24对其的支持。
在瓜达尼诺进入主流电影界的时候,他只能拍出《挑战者》这样的偏商业类型化制作,个人尝试非常淡薄,而到了A24麾下,才能触及《酷儿》这样的作品,题材更大胆,手法更开拓。
至于评分网站的低分、颁奖季度的缺席,或许是最不重要、也最可预见的当代现实结果。
10 ) 巴勒斯的《酷儿》与瓜达尼诺的《酷儿》
*全都是剧透*中英混杂是因为我两种语言都很差开头先避雷一下作家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酷儿》中文译本。
也许是时间久远的缘故,书中充斥着译者的大量延伸和自行解读,以及由于对性少数群体缺乏了解而形成的景观化、刻板印象化的描写,从我看来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巴勒斯的本意,有条件的话还是推荐阅读原著。
一直想写一下电影和原著的区别和联系。
总的来讲,电影和原著的前三分之一几乎完全吻合,从电影的第二章开始分道扬镳,最后可以说是互相背离,这其实也契合了瓜达尼诺设置的三段式叙事。
电影的前半部分几乎照搬书里的场景和对白,逐字逐句到令人怀疑编剧是不是在偷懒的地步。
不过书里对与李交谈的配角都进行了非常透彻而刻薄的描写,读得让人忍俊不禁。
描写造船的年轻人Moor:“He looked like a child, and at the same time like a prematurely aged man. His face showed the ravages of the death process, the inroads of decay in flesh cut off from the living charge of contact. He had aged without experience of life, like a piece of meat rotting on a pantry shelf.”书中的阿勒顿跟Drew Starkey在电影里的形象和表演差不多,美丽的、随性的、淡然的、没有太多人格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书的前半部分,尤其是阿勒顿刚认识李的时候,有不少阿勒顿的心理活动,也有他视角下的李的形象;不过随着故事发展,这种视角几乎消失了,一切都沿着李的双眼和思维叙述,阿勒顿彻底变成了客体。
阿勒顿最初对李的殷勤抱有戒备、困惑和好奇,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接近自己,但等他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由李一手操办的这段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稳定而程式化了。
“Allerton returned the greeting automatically before he realized that Lee had somehow established himself on a familiar basis, whereas he had previously decided to have as little to do with Lee as possible. Allerton had a talent for ignoring people, but he was not competent at dislodging someone from a position already occupied.”李虽然平时信口开河,百无禁忌,但到了要向阿勒顿出柜的时候仍然感到焦虑和坐立不安,像是一种普世的性少数困境。
“Lee felt uncomfortable in dramatic something-I-have-to-tell-you routines and he knew, from unnerving experience, the difficulties of a casual come-on: ‘I'm queer, you know, by the way.’ Sometimes they don't hear right and yell, ‘What?’ Or you toss in: ‘If you were as queer as I am.’ The other yawns and changes the subject, and you don't know whether he understood or not.”阿勒顿请Dumé带他去城里的性少数活动场所也是书里原本的情节。
阿勒顿淡淡的queer curious反而让李更抓耳挠腮了,他无法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判断阿勒顿是否是酷儿,或者他有多酷儿,他的酷儿程度是否能支撑他回应自己的感情,这一切都像一场难以破解的棋局。
书里对每个酒吧和餐厅都进行了简单的描写,电影中的布景跟我读来的感受比较相似,破旧的、布景似的、令人安心的,像一座避风港,或中转站。
电影的一个吸睛点是大尺度镜头,但事实上书中的几处床戏都讲得简短而保守,反而对李被未遂的欲望所困的描写更加丰富、具象、令人心旌摇荡,这或许也是主旨“disembodied”的一个体现。
很遗憾书中第一次床戏之后李提议替阿勒顿赎回相机这段没有出现在电影里,那部相机一直贯穿至电影结尾,也是阿勒顿态度骤然冷淡的转折标志。
李不断反思哪里出了问题,试图以阿勒顿的思维回溯整个过程,这里也是后续不再出现阿勒顿视角的转折。
从这里开始,导演和编剧开始脱离原著发展主观能动性了。
电影对书里李孤独而绝望的心情、行为和梦境幻觉进行了拆解重组,包括电影中李醉酒后对阿勒顿说“I want to talk to you, without speaking”的部分也是电影改编的一部分,应该是为了加深渴望telepathy的主旨。
电影中李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注射、喝酒和吸烟,背景响起New Order的Leave Me Alone的长镜头可以说是全片中我最喜欢的片段之一。
南美之旅部分巴勒斯和瓜达尼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巴勒斯更多倾向于描写李在旅程中的所见所感,瓜达尼诺更多的是拍摄李和阿勒顿关系内部的东西。
很喜欢李独自观察街上玩耍和河里游泳的男孩并被欲望折磨的部分,毫无遮拦的幻想、孤独的旅人和真实的、丑陋的欲望。
李幻想自己买了一艘船并和阿勒顿在海上度日,真诚的、单纯的、甜美的幻想,李这个角色在故事中很多时候都像一个漫漶的矛盾体。
“Lee could see the boat anchored at twilight. He was smoking weed with Gene, sitting beside him on a bunk in the cabin. He had an arm around Gene's shoulders. They were both wearing swimming trunks. The sea was glassy. He saw a fish rise in a swirl of water. He lay down with his head in Allerton's lap. He felt peaceful and happy. He had never felt that way in his life, except maybe as a young child. He couldn't remember.”
书中的李比电影中的形象更刻薄、油滑、强聒不舍、惹人生厌。
书中充斥着李傲慢的、不可一世的独白,政见、抱怨、歧视和讽刺,而被迫担任听众的阿勒顿通常只能默许或岔开话题。
书中李对阿勒顿赤裸的控制欲毫不遮掩也毫不引以为耻,而阿勒顿通常对此不发表任何看法,因为原著的后半部缺失对阿勒顿心理活动的描写,我并不知道他是不介意还是不在乎。
电影中减少对白可以说是美化了李这个角色,也把整段关系浪漫化了,有些镜头仍然有瓜达尼诺最出名的那部《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痕迹。
“Lee smoothed Allerton's eyebrows with his thumbs. ‘Do you mind that?’ he asked. ‘Not terribly.’ ‘But you do enjoy it sometimes? The whole deal, I mean.’ ‘Oh, yes.’” 电影里在床戏之后用了这段对话,Drew据说是即兴加上了第二遍“Oh yes”,但书中的叙述非常极简,除了对话内容和动作之外并没有太多提示语,单凭文字难以读出阿勒顿的态度究竟如何。
电影中的阳光、海岸和被风吹动的窗帘更像是一种美好的猜测。
雨林部分是改动最大的地方,由于我是看完电影才读了原著,读完感到十分震惊。
这可能是最典型的电影与文学的区别:荧幕上的故事具象、完整、戏剧化,而文字则可以悬而未决,不解释、不给出答案。
首先我完全没想到原著的Doctor Cotter是男人,电影里神神鬼鬼的巫婆形象实在太深入人心,她在电影第三章中的分量过于庞大,令人难以想象竟然是一个半原创的角色。
书中妻子的角色由电影中的丈夫担任,不干涉任何核心对话,负责端茶倒水招待客人,这样的倒置也算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对比来看非常有意思。
最震惊的一点是原著里李并没有得到Yage,也没有真正与阿勒顿心灵相通,最终两人离开并不是恐惧看清真相而逃遁,而是无功而返。
电影中喝下草药后吐出的两颗带血的跳动的心脏、埋入彼此皮肤之下的手指和再一次出现的自白“I’m not queer. I’m disembodied”,在书中寥寥带过的地方将情节推上了高潮。
这一段大概是融合了书中前文两人在电影院看Orphee时,李苦于不能触碰阿勒顿而备受折磨的描写:“An amoeboid protoplasmic projection, straining with a blind worm hunger to enter the other's body, to breathe with his lungs, see with his eyes, learn the feel of his viscera and genitals.”电影中两人体验telepathy后的第二天,Cotter对阿勒顿说:“You should’ve seen yourself last night.”“Door's already open, can’t close it now. All you can do is look away. But why would you?” 每次看到这里都被阿勒顿的神情轻轻击碎了。
如果把书和电影结合来看,“Allerton felt at times oppressed by Lee, as though Lee's presence shut off everything else. He thought he was seeing too much of Lee”,而两人经历过灵肉分离重组的一夜之后,阿勒顿对正视自己和正视两人的关系感到恐惧,他才是不敢看向镜中的那一个。
比起原著,电影更多地把聚光灯投向阿勒顿,而不是只从李的视角出发,整个故事因此显得更加平衡、更加圆融。
Drew在采访中提到:“This isn't a story of unrequited love. It's a story of unsynchronised love. I think we’ve all had experienc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hat feeling. It’s that two people have this love for one another, but for whatever reason, they exist in time and space that doesn’t allow them to fully merge.” 切入点很小,但确实是一则很令人动容的见地。
离开的时候,就像在与之前两人一起看的Orphee呼应,李听到身后的声响转过身,再回头的时候阿勒顿就消失了。
由此想到了《燃烧女子的肖像》中俄耳甫斯的故事,一个“放手”的桥段,抵达结局前的最后一处转折。
原著中最后一章直接是“两年后,回到墨西哥城”,转为李的第一人称叙述,没有过渡,也没有解释,于是电影用了一个抽象的转场来表现。
书中的李仍然不断想起阿勒顿,从过往的路人身上寻找他的影子,到处打听他的消息,最终得知他在六个月前离开了,作为向导陪一位上校前往南美洲。
这不禁令人困惑: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仿佛整个南美之行,城市与丛林,两个人的旅程,都只是李一个人的幻想,阿勒顿并没有随行。
书的结尾令我读出了一种《春光乍泄》的落寞感,“我终于来到伊瓜苏,觉得好难过,因为我始终觉得站在瀑布下面的应该是两个人。
”原著结束于李的一个梦,其中他梦见一个卖哥伦比亚彩票的人被指出这里不是哥伦比亚的时候露出了困惑受伤的表情,他想起阿勒顿听到他说他们不用同一种货币的时候也会露出这样困惑受伤的表情。
电影中则用了更多符号化的元素:霓虹旅馆、凝视自我之眼、流泪的衔尾蛇,与之前出现的意象一一呼应。
据说李朝阿勒顿开枪是巴勒斯枪杀妻子的投射,我觉得在这个故事的语境下可能象征着他希望在头脑中杀死阿勒顿,停止他对自己产生的影响,但并没有成功。
李听到身后的声响回过头,阿勒顿又消失了,就像在雨林中的最后一眼。
电影结尾处的原声带,“LOVE.”,包含了枪声和阿勒顿手中的玻璃杯滚落的声音,一边听一边回想电影中的场景,感受到一种轻轻的心碎。
弥留之际,李颤抖着躺在床上,想象男孩的腿交叠在自己腿上,就像在基多一个毒瘾发作的寒冷的夜晚,有人依偎。
深夜听着原声带梳理完原著和电影的脉络,仍然感觉被击中了。
感谢这部电影出现在我的2024年末,当之无愧的我的年度最佳。
最后夹带一点私货,无论是看电影里还是读原著,阿勒顿这个角色都看得我无性恋雷达狂响,一边读一边忍不住感叹:Of course he’s queer. He’s one of us! 重新搬出一则毫无根据的酷儿理论了:文艺作品里所有取向不明、态度暧昧、厌恶承诺和strong bonding的角色都应该是无性恋。
We’re among you. We’re everyw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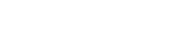
































































87分钟之前需要忍受DC直男强演基佬的生硬演技(都怪我看了太多007🚬),之后开始逐渐抽象,瓜导最好别告诉我其实一切都是所谓Yage导致的想象/幻觉😓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这一行字在此刻得到了具象化。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到影片的主题和意图,那段不对等的亲密关系也被刻画的很好,所有的邪典怪诞的内核是试图沟通的两个爱人,瓜导的镜头语言也依然很值得品味,但这一切终究还是太抽象了。本想着看大叔鲜肉谈恋爱,谁料到成了春光乍泄+夺宝奇兵+永久居留+现代舞的低配版大融合…看很多人在夸丹尼尔的表演,油腻和躁动确实是有了,不过这完全就一个多动症版布兰科啊…德鲁的颜我也实在欣赏无能,一眼幻视梅总+尼子…只能说艺术的确是有它的审美门槛和目标受众的吧,而我也确确实实地认识到了自己不属于这部片子的既定观众群,所以只能走马观花看个热闹了。
复古+超现实的影像风格依然让人着迷,场景的道具感很重,也符合全片所要表达的美学形式和主题,这并不是大家所期盼看到的浓情爱恋,德鲁饰演的角色更多的只是作为一枚代表欲望和美的符号,没有任何亮眼之处,全片整体上形式大于内容,充满了空洞和乏味,毫无思想和灵魂,让人难以下咽。
前面有种复古的味道,还挺好看的,但后面突然神乎,非常跳脱而不知所云。
中南美洲的风景美丽得像有呼吸,可惜主题过于陈旧,爱的不可能性、追寻心灵感应但反过来发现交流也没意义的寂寞。主人公们外貌还是够用的。
巴勒斯笔下的Lee其实是个很固执干瘪自欺到极致的人,queer在当时的双关意味恰好满足了lee抗拒酷儿身份却又暗自紧张兴奋的情绪。巴勒斯笔下的蜈蚣既有因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历史影响而造就的危险性,也有毒到情深爱到骨髓后最魅惑最致命的性欲和爱欲。原著写得并不好,而电影前两部分也没拍好,五十年代酷儿集群团体内老年群体与年轻人接触时的胆战心惊和欲盖弥彰其实没太拍出来;毒和酒和性的融合做得不到位。从原著角度出发电影没拍lee和尤金的感情基调是很多的,可这是惊世骇俗的以大尺度非社会既定道德感著称的作者写的原著!!拍摄尺度会不会过于小了?not queer but disembodied,超自然幻想镜头语言太美,而南美丛林回归自然后酷儿们的肉体连结融合交织,证明城市异性恋规范性社会的规训最终都会是屁
3.5 恰当的技法与致敬。瓜导始终清新,有着意大利人优良的视觉基因,却没有前辈们的胸怀气度。p.s他居然对丛林不感兴趣,也是棚拍?
依旧是瓜导擅长的同性题材,不过和cmbyn的唯美挂不同,这部是巴勒斯小说里那种垮掉的气质,更像是一个老gay的内心独白,几次超现实场景也表现出了角色的精神状态,比导演失控的阴风阵阵要好很多。另外克雷格演得没什么问题,只是他的硬汉形象太深入人心。
演技较浮夸,意象浮于表面
热评少责备观众,还义正言辞“电影不是满足观众意淫的”,导演不是把自己的意淫放在大银幕上让观众花钱看?这年头还要教观众做事?跟男同性恋有没有关系都不影响这部电影完成度还不如美术馆里的视频作品,况且怎么还怪起观众觉得这是BL,导演本来就是起手CMBYN也好意思怪观众联想,不如说导演水平比你看不起的耽美也没好到哪里去。哦对不起,耽美起码不按头让我接受创作者自以为是的艺术表达,们男导演真的会给自己贴金。
看完的感觉就像是,满怀期待地打开了一盒榴莲千层,吃到最后发现原材料其实不是榴莲,而是💩
@FaF
LFF24 相比之下第三段还不错;两个人完全不来电,癫痫般的床戏,癫痫般的演技,癫痫般的配乐,我受够了;omar apollos dick scenes were 100% unnecessary i felt bad for him
does this gay experience deserve an epic bio-pic treatment? not really.
像夏加尔的画,a more accessible 阿彼察邦 Trickling tears glistening in the dark, moisture seeping through the stuffy air, I was moved to tears by the pure beauty of it all. Holding back the urges of caressing his face, to communicate without speaking. How delicate that everything is beautifully connected
评分6.2低得太过分了 这可能是瓜导目前作品探讨酷儿身份认同和困境之巅 需要一定的观影门槛 包括但不限于垮掉派文学改编、对巴勒斯生平的了解、片中多段超现实隐喻 如果抱着观看一个无伤大雅的爱情故事的心态看多半要失望了 尾声那段房间梦境太林奇了 服装设计是罗意威创意总监难怪这么时尚 disembodied是不是可以翻译成不以心为形役
@Regal Atlantic Station. 3. 瓜达尼诺还是更适合做MV导演,甚至比欧迪亚更适合。
很喜歡瓜導的美術風格,劇情真的有點冗長且乏味,影片從頭到尾貫穿的悲劇性讓人難受。。。
6/10,瓜达尼诺大姐,你不是阿彼察邦,也不是大卫林奇,把一部名字叫《queer》的电影拍成这样真的很搞笑,真的不要装了美眉
孤独是可耻的,无法对抗孤独更是可怜的,而把摆脱孤独寄托在别人身上,结果将注定是可悲的,早点认清现实让自己不需要任何人才是上策。其实是对男同志一堂很好的教育课,可惜的是剧本有些问题,主题被稀释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