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剧情介绍
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父亲伟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变。表面上平静的家庭被阴霾笼罩。妈妈慕伶扛起家,却得不到父子的体谅。儿子一鸣收到美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不敢告诉爸妈。他知道母亲不易,却不愿表现过多关心。父亲伟明则在迷雾之中暗自做出一个改变家庭命运的选择。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皮囊第三季猎冰拥有神之舌的男子:鬼灯死亡之路篇拐个洋妞做媳妇玩偶盒惊魂致命抉择玛丽·雪莱的怪物伊甸别和陌生人跳舞好警察,坏警察无处藏身人生大事竞争的守护者萤火虫之恋命回迁转帝锦我的公园好友黑鸦1够胆你就杀了我特斯拉笔记做头盛夏的方程式Voice最后的子弹花园农家做自己万岁恋爱刺客恐怖循环潘尼沃斯第一季旱码头
《小伟》长篇影评
1 ) 「死亡不在场」的死亡电影
去看了《小伟》,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但是因为足够真诚温柔克制收敛,所以还是打动了我。
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准确来说应该是一部关于“死亡不在场”的死亡电影,导演拒绝展示出疾病和死亡的冷酷惨烈,几乎是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展开对生活的追踪思考。
整部电影划分为三段,对应着母子父三人的叙述视角,结构上有点首尾呼应之感,结尾即开端。
通过幻想与现实、梦境与存在、过去与未来、死亡与新生的对立融合,将生活中茫茫无边的焦虑、痛苦、反抗与逃离像雾气一样拢在整部片子之上,使得最后的表达充满了一种只能顾及当下的不彻底和暧昧的美感。
这种当下性没有任何承诺,无法具有超越的意义,所以看起来琐碎与平庸,不过这就是生活呀,这就是通过对死亡的叛逃描述一种生活的存在性,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常态就是接受,不是英雄式的剧烈反抗,也不是软弱的屈从与跪下,而是接受,然后活下去,这也是这部影片风格个人化的原因,导演拒绝用一种更有力量的方式影响大众,他没有选择一种讨巧的策略,他不鼓舞人心,他不呼唤正确,他拒绝了一种媚俗的升华,于是看完之后会找到一点平静和稳妥之感,也挺好的。
2 )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广州
前面都蛮好,结尾部分却故弄玄虚,突然就莫迪亚诺起来,犯的依然是国产新导演的通病,其实完全可以让老豆用几句台词交代一下:为何打算回乡祭祖,及最后的时间想和家人一起度过云云。
在结局部分的半小时篇幅里用一次返乡的温馨旅程来作结束,哀而不伤,再接到结尾处母子二人在房间里整理父亲遗物,会更有味道一些,大可不必剑走偏锋,又玩梦境、回忆、现实混杂的那套近年来被反复重建强调的国产新锐模式,踏踏实实的继续用现实主义风格叙事还能留下些许余韵,结尾本来处理得不错,甚至一度让我想到了《牯岭街》的结尾,然而,接下来一个莫名其妙的运动镜头pov带着观众忽然穿过屋子走到过曝平台,又以曝白老豆曾经坐的藤椅来结束,一下子就落了俗套。
另外影片中有些细节也没能交代清楚,比如从梯子上摔下去的保安究竟怎样了?
会对主角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后面用一句台词就含糊过去,那这条线索就等于多余了,完全可以剪掉。
另外一鸣和女同学的关系也没展开些,两人的关系究竟亲疏如何?
看得一头雾水,让人总觉得一鸣的人际圈少了点什么;老豆伟明的回忆和个人经历剪得太碎了,我们只是模糊的了解到老豆原本是乡下的海岛青年,年轻时只身来到省城,一路打拼多年才换来了现在的位置,而且他和故乡家人的关系似乎也并不融洽,这之间经历过什么?
若能交代更清楚一些就好了,其实通过寥寥几句台词就可以做到,一如《恋恋风尘》中阿远打工的店铺老板偶然向阿远提及自己年轻时的往事,很自然的就把两代人的生活经历联系到了一起;母亲慕伶的个人线也很模糊,我们甚至并不知道她是做什么职业的,或是有没有工作?
为何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来陪伴家人?
如果有工作的话,那么她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同事和上司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同事们隐约知道她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之后会有怎样的反应?
可惜这些都没能展现出来,而她那个老同学阿宝似乎有些潮汕口音,是否也有暗示母亲也并非广州本地人的意味在里面?
后面母亲和阿宝喝茶的情节有些多余,和前面医院中营造的情绪也接不上,或者在这之间再加些情节铺垫一下,不过感觉也不是太好,有点画蛇添足,破坏了余韵。
或者换个角度考虑的话,如果前1/3部分在引出“父亲得了癌症”这一全片大事件之前,先像三段锦短片那样依次讲完三个人的故事,介绍角色,并在故事中一一引出其他人物,最后在全片1/2篇幅时将几条主要人物的故事线因伟明的病情汇聚在一起,进入主线大事件章节,在结构上会不会比现在这样线索琐碎、风格不一的剪辑要清晰一些,更便于观众理解呢?
当然以上也只是个人看法罢了。
至于技术上的缺陷:声音空间做得很好,不过偶尔也有画外不相干的尖锐杂音进来,后期声音处理上平衡一下估计会好些,在公共场所拍摄的外景总有路人停下脚步满脸疑惑的直盯摄影机镜头凝望不已,这时镜头稍微跟摇主角过去或调一下焦点就可以避免,却总是停滞了半拍,开场第一个镜头一路推到屋内染发的近景,这时焦点应该及时跟到老豆脸上,焦点却依然停在前景,人物区的后景一片散焦,之后又生硬的直接切到另一个角度清晰的近景,其实完全可以在调焦中用一个横移改变角度进入到故事中;整部影片中摄影机虽然动了起来,手持跟拍却晃得厉害,一路颠簸跟随人物穿梭于狭窄阴郁的楼层和陋巷间,给人一种焦躁浮动的不安定感,并反复强调加深了这种不安感,在压抑紧绷的剧情的双重冲击之下反而冲淡了原本逐步铺垫营造出的悲凉气氛。
影片在视觉上将广州的地貌特征表现得比较丰富,那上上下下的坡路,狭窄逼仄的老旧居民楼(这里我有一点疑惑:广州的中产家庭也会住在这种社区吗?
),杂乱的菜市场,骑楼下的大排档,巨大的榕树,植被茂密的山丘,密集的居住区,狭窄而盘绕的过街天桥,以及从广州站驶出的穿过城市居民区的绿皮车,都是我所熟悉的那个羊城的日常景物,甚至比之云中兄的电影中所表现的那个广州更多了些地气和烟火气,而全片贯穿始终的白话对白更是给故事本身平添了几分亲切感,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发生在广州的、关于一个广东家庭的、讲述普通广东人生活的故事,唯一美中不足的所有的镜头几乎都是在晴天拍摄的,没能完全呈现出那个雨水霏霏、绿意盎然、潮热蒸腾,时刻令人汗出如浆的广府印象……最后,这部电影只能在大荧幕上才能专心看完,并且,看一遍也就够了……
3 ) 命脉相连!这样的处女作着实令人惊艳
看死君: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没几天,但已经很少有谁提起那份获奖名单了,更多的是被文章马伊琍离婚、海清的“女演员宣言”等获奖影片之外的新闻所淹没;以及这两天被更为广泛讨论的“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又不得不让人想到这几年同样力捧青年导演的金马奖的举步维艰。
近十年来,中国电影似乎从没有像今年一样被集体唱衰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好电影诞生。
当真正的好电影出现时,我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更何况,在这青年导演队伍日益壮大的当下,每年从FIRST等影展向电影市场输送的年轻血液中,也都不乏年度黑马之作。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便是荣获了本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的作品,黄梓导演的《慕伶,一鸣,伟明》。
作为今年影展的四部惊人首作之一,本片在众多参赛片中显得有些特别,它看似只是一部司空见惯的家庭电影,却在其中埋藏着太多的“宝藏”,拥有非常大的解读空间。
命脉相连的一家三口的日常琐事,面对沉甸甸的生死命题的半梦半醒,以及逃离现实和回归自我的相互拉扯。
关于家庭,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关于告别,影片《慕伶,一鸣,伟明》就像是一支悲喜交织的奏鸣曲,暗涌出独特的生命体验。
正如片名所呈现的那样,影片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一家三口各自不同的人生,并最终拧成一个绳结。
看似是彼此分割的不同视角,追根溯源之下,却都殊途同归。
那条缠绕在母亲、儿子与父亲之间的隐形纽带,赋予了这个生命共同体既温柔又悲伤的因子。
或许,这也是很多家庭的共同宿命。
影片第一章节以母亲幕伶的视角展开。
跟随着手持镜头,慕伶只身去学校寻找儿子,貌合神离的母子关系仅寥寥片语便凸显出来。
而在得知丈夫已身患肝癌晚期时,她的内心更是承受着如排山倒海般的痛苦。
作为家庭主妇,她不得不维持平静的假象,而不让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真相。
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一鸣,把学校当作一个巨大的失乐园。
与同学偷偷躲在厕所吸烟,上课期间爬墙逃学,还有对母亲的疏远隔阂。
身处青春期的他,总是冒险又不甘。
他一边对出国留学充满着向往,一边却不忍心抛下病重的父亲。
复杂的家庭情感时不时地将他拉扯进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乌托邦梦境。
似乎唯有在那里,他才没有这样的烦恼。
第三章节中,父亲伟明的视角更耐人寻味。
虽然是触及死亡这样一个让人避而远之的话题,但这个故事中,导演以超现实角度将死亡化为一种绵软的生命形式。
梦境与现实彼此交错,灵魂和肉身相互叠加。
伟明的意识脱离于肉体,回到了故土,见到了已故的老母亲。
而幕伶、一鸣和伟明在最后的无人村落和回家的火车上,达成了情感上的共鸣。
之前所有的埋怨、不解与厌烦,都随着那一趟回乡之旅悄然化解。
专访《幕伶,一鸣,伟明》导演黄梓采访 | 看死君看死君:导演好,这部电影的片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吗?
黄梓:对,这个片名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了,甚至可以说是先有这个片名,才会有接下来的故事创作。
电影分了三个人名、三个段落,每个段落都以其中一个人作为主观视角展开故事,片名就是一家三口,里面三个人的名字慕伶、一鸣、伟明,分别对应的就是妈妈、儿子、爸爸。
看死君:我发现电影的英文名叫《All About ING》,关于ING,除了对应三位主角名字的拼音后缀,还有什么用意?
黄梓:是的,ING其实就是取谐音,就是ING,同时ING在英文里面有现在进行时的意思,我想表达一种当下的感觉。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没有离开现在当下的感觉。
当你回忆过往的时候,其实历历在目的感觉也是一种当下的感觉。
看死君:这三个人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黄梓:其实是取决于“伟明”这个名字,因为我爸爸的名字里面就有“伟”这个字,而我爸爸姐妹的名字里都有“明”这个字,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字组合成了“伟明”,其实就是我当下的一个偏好。
至于“一鸣”这个名字,我一直都挺喜欢的,我喜欢“一”这个字。
而“慕伶”是因为我也很喜欢“慕”这个字。
看死君:作为长片处女作,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黄梓:其实影片的故事多多少少有我个人的印迹,是根据我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去编写的一个故事。
虽然很多剧情其实是编的,但是里面的人物原形其实就是我和我家人。
看死君:所以,您自身的经历投射在影片中的占比还挺重的。
黄梓:是的,我爸爸确实生病了,我也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其实我爸爸生病是在前几年,那时候我刚刚留学回来,待在家里耗了一两年没啥事干,忽然间我爸就被查出病情。
我当时的心里感受就是特别想离开,因为太压抑了,每天发生的种种,让我不知道爸爸的病情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所以我就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
包括我高中时期的状态,我跟父母的关系,我当时也是非常渴望逃离,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城市,去到很远的地方。
看死君:所以一鸣这个角色,也是您个人的缩影。
黄梓:是,其实我就是把生命中两个比较困惑的阶段,交叉融合到了一起,变成了现在电影里面一鸣准备要出国,但同时他又遇到了爸爸生病的情况,面临着亲情的羁绊。
他到底是选择出国,还是留在家里。
黄梓导演看死君:影片开头通过电视屏幕出“慕伶,一鸣,伟明”这个片名的方式很巧妙,可以谈谈这个构想吗?
黄梓:其实我想做成一家人在一个休闲的下午,母亲给父亲染头发,儿子本来看着电视,看着看着睡着了,躺在沙发上;他们没有哪个人是在认真看电视。
出现的一些镜头其实并没有很清晰地带出这三个人的样子,包括母亲给父亲染头发,我都没有给他们一个正脸。
而他们的真正容貌展现其实是在电视屏幕里面,他们开着摩托车,但整体还是模糊的。
看死君:影片中有三个章节,前面两章都是按慕伶和一鸣的视角来叙事;但第三章却没有完全按伟明视角,为什么?
黄梓:我觉得他们整个家庭关系的走向,虽然三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状态,但他们需要面对的都是爸爸生病的事情,而他们可能有各自面对的一个方式,他们也没有去跟另外两方一起建立起一个怎么样的沟通,达成一个和解。
从一开始他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还是偏独立的,或者说他们的关系本来便有一点疏离。
所以到了爸爸段落,虽然一开始也是他独自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慢慢地到后面,尤其是他们离开了广州,到了爸爸以前出生、成长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是有在情感上面找到一些联结点,所以那个视角并没有特别地只是专注于其中一个人。
看死君:为何会在第三章节加入梦境与现实相结合的场景?
黄梓:这个处理方式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戏剧冲突特别强的东西,我不想只通过他们面对客观困境的方式去表现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不想简单地以事件或者剧情来塑造他们的关系以及角色。
我想在最后这部分,通过建构空间的关系,加入一些虚无的情感的连接。
父子之间的情感最终在岛上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他们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有效对话。
他们分别进入无人村,见到了以前的老房子,但是他们看到的房子是不一样的。
爸爸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对回忆的一个重现。
弥留之际,他开始有一些意识的投射,让他看到了一些与现实中不一样的东西,包括老房子里面还住着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哥哥。
那是他的一种意念的传递。
儿子一开始进入无人村其实是最写实的,然后我用了一个平行剪辑的手法。
其实那个老房子跟无人村里的其他房子一样,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了,会让我们意识到爸爸看到的其实是他的某种想象。
但是当儿子追寻着缝纫机的声音进入到一个老房子之后,里面又有一个中年女人,她在用缝纫机做衣服。
她的穿着打扮是一个当地农村妇女的样子,还跟他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方言。
但是,那些对话其实是他带着爸爸的意识,在跟母亲进行对话;也就重现了他爸爸和他奶奶当年的对话。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时空融合到了一起,由于儿子在当下也遇到选择出国还是留下的问题。
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有点像爸爸当年跟奶奶的一个关系。
看死君:影片的剪辑非常出彩,尤其是超现实部分,能否谈谈剪辑方面的构想?
黄梓:确实我们这部分花了很多时间,想着怎么把它剪好,担心在虚实处理的环节上很容易让人觉得有割裂感或者是有点太刻意。
现在影片中的最终呈现是我跟剪辑师都觉得比较满意的结果了。
因为我们又去补拍了很多,这其中有很多层次的叠加,原有的素材确实没办法支撑起我们想要的那种状态。
看死君:影片结尾处,幕伶和一鸣在收拾伟明的遗物,然后手持的镜头晃动着离开,这是以父亲伟明的视角吗?
黄梓:我自己也是这么理解,但是可能有些人有别的解读,我当时创作的想法就是想要有一个父亲的视角去做一次告别。
可以理解成父亲以一个灵魂的形式存在,他的意识还存在于这屋子里面,但是母子并不知道。
她们把父亲的衣服收拾好然后丢掉,是一个要继续生活的态度,父亲看到这一切后,就慢慢地离开了这个家,作为一种告别的方式。
看死君:再说一下最后这个镜头吧,从渐渐过爆到变成一个全白的画面,为何这么处理?
黄梓:这场戏其实是在现场临时想到的。
他是一个主观的视角,他看到的世界就会有一个转换,因为他可能要离开,离开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可能去到另外一个维度的感觉。
所以我想用曝光的手法,类似父亲的视角去表达不一样的细节。
作者| 想成为猫;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采访| 看死君;转载请注明出处
4 ) 虚掩的门帘
在《小伟》的结尾,镜头起身,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影片开头同样恍惚又充满回忆的天台坐凳上,仿佛一个行累但可以心歇的父亲。
无论这样的首尾衔接是好是坏,《小伟》都抓住机会完成了某件可能对导演黄梓来说重要的事:为悼亡父亲的电影主题探清叙事轨迹。
除祛瞟一眼简介即知的内容外,《小伟》的三段式结构,理所应当的来源于其原名《慕伶,一鸣,伟明》的自分结构,父亲伟明已过世,母亲慕伶仍健在,一鸣自己应该还有着尚未可确定无疑的未来,而过去的终将会过去,未来的还在远方,无论是对刚刚成年的儿子,亦或饱经世事的母亲来说都是一样,这表达了一个绝对真实的人生意象-生活在继续。
人生应如此的视感,从线性叙事的顺序出发,应该按照过去→现在→将来般可经验在父亲、母亲、儿子的顺序下来讲述,才有那种人生的感觉,但在《小伟》中,实际却是按照母亲、儿子、父亲的顺序讲述,这一方面预示着电影叙事的风格化,另一方面这种不寻常则构成了耐人回味的叙事脉络,其回味来源于适应-无论是朋友、同学的暂别还是亲人的永别,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用一段时间去习惯。
在这之后,生活应该怎样继续才会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在《小伟》充满自顾自存在感的镜头语言之中,情节里始终有一个因为癌症而注定要逝去的父亲,可以形成最终的封闭,而成为难以规避的故事事实。
祛戏剧的泛焦处理,或可以归结到黄梓编剧经历的稚嫩不足,或也可能因为有些经历的情感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而更像是一种祛时空的补偿性措施。
而从第三段父亲{伟明}的无逻辑回溯与现时交叉的所谓“梦”的开始,那些扩展的额外在地形式,也渐渐因为形式上与名义上的接收者-儿子与母亲,和真正的接受者-观众 不断错失而趋“散”,虽然时空会因为场景总是框定在广东的小家、老家、学校、医院等因循旧景的叙事空间而凸显出实在,从而不至于过度缺乏存在感,但故事本身因为父亲的渐行渐远,是在逐渐丧失存在感,它并不适应也并不应该被那种积累情绪、累积存在感作为驱动力的镜头捕捉和呈现,创造共情首先需要能移情的想象共同基础。
简言之,我们作为观者和慕伶、一鸣作为母亲与儿子共同知道只有父亲会逝去的事实而已。
而这样“散”的失衡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即叙事无法被父亲逝去的事实封闭,可但是,艺术正是因为有限的形式才能成为“艺术”,就像电影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一样,叙事时间终将结束于一点,而形成一个先于《小伟》结尾的封闭,所以在结尾,不被提及却已经确定逝去的父亲就和开篇提到的那个仿佛还健在的父亲形成因果,另一段叙事轨迹也就显现了,进而反过来对“祛戏剧”进行修正,而使{伟明}的第三段呈现出一种在整体中,又无法融入整体叙事的感觉。
回看《小伟》中{一鸣}部分漫不经心的“阿基里斯与龟”小故事,阿基里斯在理智的推导之下当然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极限永远存在于他们俩之间,但从经验角度来讲,恐怕没人会否认阿基里斯几乎瞬间就可以追上甚至超过乌龟,所以这段在笛卡尔完备性唯心论下的时间,就必然不可能是一段真实绵延的时间,而只是一段被截取的晶体时间(博格森语)。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段基本能当作对{伟明}段落的绝佳转喻,也是坐落在整个故事时间中,{一鸣}对{伟明}不必言明的情感,终将因为人不得不活在当下的生活终将继续,而回流到{慕伶}。
所以,视开头和结尾显然已经显形的叙事者为“历史的父亲-现在的母亲-未来的儿子”的三位一体的话,那么在其善始善终的循环之中,就必然因为存在先于本质,而有着儿子也已可以歇心释怀的答案。
诚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父母是挡在你和死神之间的一席门帘”。
细细想来,黄梓在拍摄这部悼念父亲并珍惜母亲的电影之前,可能就已经和生活达成了和解并可以继续前行,而那席门帘,也终究只是虚掩着罢了。
5 ) 《小伟》声音创作谈:家庭往事与广州记忆
1月22日,《小伟》已于全国上映。
作为一部处女作,影片展现出的精巧技法和细腻情感无不令我们我们动容。
影片讲述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爸爸患癌而改变的故事。
妈妈的艰辛与隐忍,儿子的迷茫与抉择,爸爸对故土和亲人的惦念,这种传统中国家庭的含蓄与细腻浓缩在这部影片中。
《小伟》由黄梓导演与父母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来,黄梓拍这部电影是在寻找一种和爸爸对话的方式,也是在顺着家庭情感纽带审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
同时,黄梓导演也是在拍广州。
他出生成长在广州,广州的声音成为了他对生活理解的一部分。
在《小伟》的声音创作中,为了营造更为真实、丰富的广州城市氛围,莫非影画声音团队收集、创作了大量广州的声音元素。
影片中广州街道的声音,高架桥的声音,居民区和学校的声音,这些有着浓厚粤地氛围的声音共同营造出丰富的声音空间,仿佛让人置身广州一般。
这些丰富的环境音给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影片幕后声音制作的更多细节,莫非影画采访了导演黄梓和声音指导李丹枫,请他们聊一聊声音创作中的想法和感受。
小伟· 声音创作谈莫非影画:《小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原型是导演在广州的家庭故事,片中广州的环境氛围捕捉地特别精准。
首先想问导演,关于广州,您记忆里独特的声音有哪些?
有哪些声音最终运用在了影片中?
黄梓:我觉得广州比较特别的一个声音是高架桥上发出来的。
广州有很多高架桥,整个城市有一种层层叠叠的感觉,可能有两三层的那种高架桥,它们会缠绕在一起。
每每有车经过那些高架桥时,就会有一些特别的声音。
因为高架桥并不是完全平整的,有一些拼接的位置,同时也有些凹凸不平的位置。
这个声音是我觉得挺有城市特色的。
还有就是不那么特殊,但是对我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城市马路的声音。
我们广州是有那种防盗网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和我妈经常在防盗网上放上小桌子和小板凳,让我坐在防盗网里面写字,我能够更清晰地听到窗外马路上的声音,所以我对城市的声音和马路的声音都是比较敏感的。
影片第一个镜头,虽然是一个居民楼公共天台的环境,但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带到城市的声音,把一些城市的声音加进去。
有邻里的声音,比如做饭声,小朋友弹钢琴的一些声音,还有马路上公交车靠站、刹车、开门、重新出发的一些声音,我们都在有选择性地放进去。
然后就是城市里面一些人的声音,虽然没有听得那么清楚,但是偶尔会听到一两句粤语。
有一场学校课间的戏,我是单独又让录音师去补录了一场。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学校放寒假,学校里面是没有人的。
后来我们做声音后期的时候,我让录音师去到学校把课间的声音录了一遍。
后来我们贴到了片子里面来用,我个人还是觉得特别亲切的。
因为课间的时候,有些学生讲粤语,有些学生讲普通话,其实这个是特别广州的。
而且大部分学生是在讲粤语,就像是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大家的状态。
莫非影画:请问丹枫老师,在声音创作中,您怎样用声音进一步增强这种地域感呢?
广州的声音元素在声音设计中有哪些体现吗?
李丹枫:影片整体是一个城市的氛围,广东话的氛围。
当然是分阶段的,有一鸣家的环境氛围,学校的氛围,医院的氛围和街上的一些环境氛围。
我们希望能让大家感觉到这真的是在广州发生的一个故事,所以也补录了这些环境音,为了能够让广州的氛围更明确。
广州有城铁或者列车会从像高架桥一样的地方经过。
在妈妈和儿子一边走路一边说话,走过高架桥下时,他们两个稍微有一些争执。
我们觉得妈妈跟儿子之间的情绪跟铁道上列车驶过的气氛挺契合的,所以就在这里用上了列车的声音。
黄梓:我觉得我们让这个空间的层次更加丰富的话,也不用执着于一定要百分百还原这个空间里面本来应该有的那些声音。
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高架天桥,走过的应该是一些汽车,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用它原来的那种声音,而是替换成列车经过的那种声音,好像从他们头上经过一样。
列车的声音虽然那并不是这个空间真正的声音,但是我觉得特别能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空间。
莫非影画:就像导演所说,影片很注重人物心理空间的营造,有很多主观化的处理,比如妈妈在医院走廊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可以分享一下这里的声音设计上的想法吗?
黄梓:医院那里是一个长镜头,其实也分为了现实和超现实。
现实的部分就是有亲戚来探访,当亲戚走掉之后,剩下爸爸,整个房间的氛围又不一样了。
当外面走廊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镜头跟随着护士来到走廊。
虽然空间没有怎么变化,还是在医院,但是整个故事推进包括整个空间氛围的营造都是有转变的。
再到了电梯间,亲戚走了,儿子问了妈妈一个问题,妈妈扔下一句话就往房间走去。
这时又是另外一种她特别内在的声音,虽然还是同一条走廊,但是好像进入了她的心理空间一样。
把医院里面所有声音放大,同时把那种杂乱的声音拿掉之后,会营造出一种声音,我不知道能不能用空灵去形容。
这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听到的一种声音,可能有时候在我们的梦里面,或者说在我们意识模糊的时候能够听到,这是一种人物心理空间的特别的处理。
当妈妈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从视觉上面来说,或者说从情节上面来说,其实已经跨越了一段时间了,故事已经来到了爸爸准备要出院的那一天。
这时候护士打破了所有的这种心理空间的构建,把她拉回到了现实生活里面。
所以在走廊里面的那种声音的处理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贴合人物状态的,包括完成了一个时空的转换。
李丹枫:对,医院这里的长镜头在整个设计上面是分阶段的,我们希望每个声音都能够明确,这也是黄梓跟我当时聊得最清楚的一点。
他希望妈妈每经过一个房间,每经过一个人,或是每经过护士站等一个个点的时候,都能有声音发出来,这种阶段性的设计其实也能带着妈妈的心理一层一层地递进。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设计,设想每个房间里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有的房间里面会有冲马桶的声音,有的房间里面会有护士摇床的声音,有的房间可能是护士走出来的声音。
因为楼道的另一侧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在楼道另一侧也加入了一个人推着医护车从旁边驶过的那种感觉。
所有的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进入到妈妈的心理空间。
莫非影画:就像原片名《慕伶,一鸣,伟明》那样,影片分为了从妈妈、儿子和爸爸的视角出发的三个段落。
在第三段有很强的超现实感,声音也跟前两部分的感受有较大不同。
这里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呢?
三个段落的声音设计有尝试做区分吗?
李丹枫:三个段落从剪辑风格和结构上的区别就挺大的,那整个的声音设计上也是有很大区别,因为我们想体现三个人不同的心境和感受。
妈妈那个段落更多的是一种焦虑和焦急,所以会有我刚刚提到的医院的声音,列车划过的声音,有一点紧张感。
包括她在家的时候,经常会有广播声,这也是广东话的元素。
我们专门收集了很多广东话的新闻节目,在家里一直播放。
这里其实也是想把家庭放在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里面。
总体来讲这些声音都是相对嘈杂,或者说比较让人心情烦躁的元素,这个主要是妈妈慕伶的段落。
一鸣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空间。
我们有时候会强化他的呼吸感,有时候会去做比较意象化或者说主观化的处理,进入到他的内心情境,比如他在寻找那只鞋时就做了这种处理。
伟明的段落最明显的就是超现实。
伟明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伟明在老屋见到了他的妈妈和哥哥,整个空间都是很超现实的。
伟明在船厂不停地寻找时,整个空间是很梦幻的。
声音里有一些金属的元素,风沙静静的,但是你能听得很清楚,还有小孩在船上跑来跑去,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超现实的处理。
整个段落都非常静,我们想营造出一个孤岛的感觉,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是缝纫机。
一鸣隔着一层门听到缝纫机的声音,进门后见到了妈妈,所有的这些也都是一个特别主观化的处理,那其实是伟明的一个记忆。
黄梓:对,这里也是希望通过声音来叙事。
缝纫机的声音对于那个空间来说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是一个已经荒废了很久的老房子。
但是当一鸣在这样一个屋子里面忽然听到缝纫机的声音,他尝试找到这种声音,推开房门,见到了一个他想象不到的场景。
在一个缝纫机房里面,一个妇人在用缝纫机编织衣服。
当那个妇人回头的时候,他发现是他母亲。
母亲的穿着打扮跟岛上的村民是一样的,母亲跟他说着他听不懂的话,但是他好像又似懂非懂。
母亲跟他讲的那些话,像是一鸣裹挟着爸爸伟明的一个回忆,重新经历了一次爸爸年轻的时候想要离开小岛,去广州之前跟他母亲之间的一个对话。
莫非影画:还有哪些您认为声音设计上的亮点想要分享给大家吗?
李丹枫: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伟明的篇章,在最后的阶段,我们在火车之前能够听到刚才说的缝纫机的声音,然后缝纫机的声音慢慢地变成了火车的声音,这时我们看到一家三口正在火车上。
火车是离别或者离去的一个意象化的概念。
在火车里,爸爸不太情愿地吃药时,我们有一个火车从山洞驶过和错车的那种处理。
这些都是有现实基础的意象化处理,这些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在开篇的段落,我们做了很多点声源的设计。
比如说有小孩在练钢琴,有人在做饭,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听收音机看电视,也有很多广东话的氛围。
所有这些声音慢慢地聚焦到风铃声,聚焦到一个家庭,但其实在镜头里你看不到风铃。
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在船厂段落的风声上找到一些灵感,好像是一种过去的事情被风吹散了。
所以在故事的开篇,我们通过风铃声带来一个家庭的印迹,营造一种温馨的感觉。
因为一开始是妈妈在给爸爸染头发,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家庭场景。
这里也是把风铃做了一个意象化的处理。
在最后的结尾,电视上是爸爸和一鸣在讲话,房间里面妈妈和一鸣也在说话,就好像一个时空交错的感受。
然后镜头慢慢地游走到了外面,这时候环境音才加入。
因为之前一鸣的情绪是在对爸爸的思念里,在家庭中。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当镜头慢慢移出去,外面的环境音慢慢地也来了。
这里其实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处理。
黄梓:对,最后一个镜头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处理。
这里拍的是客厅,同时又拍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的母子有一个日常的对话,同时客厅电视机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里是有爸爸的,是爸爸拿着手机去拍儿子,有这么一个像家庭录像的片段。
在叙事时间线上面,那场戏爸爸已经离开人世了。
但是我特别希望虽然爸爸已经不在家了,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还在,他的影像还在这个家里面。
所以我借用了电视这个媒介,让爸爸出现在了家里面。
之后这个镜头就变成了爸爸的主观镜头,所谓的灵魂视角。
他徐徐地走出房子,走到了公共的大阳台。
当他走出屋子的时候,屋子里妈妈跟儿子的声音慢慢微弱,直到他走到阳台,彻底听不到妈妈和儿子的声音。
这时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同时声音上带了一点城市的声音,马路的声音,也带了一点点小区空间的环境音。
并不嘈杂,而是一种很纯净的声音,一种贴近生活的声音。
就这样完成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也预示着爸爸正式跟妈妈和儿子告别。
采访:沈桥编辑:岳景萱
口碑热评电影《小伟》正在上映,没看的朋友请抓紧去影院感受吧!
6 ) 让喧哗通往低语
《小伟》有意地模糊虚实界限,却不是通过暴露画框的设计完成,相反地,它改造画框内的可用元素(包括声音),让观众在解谜游戏的参与中与创作者一同完成对影像感的构建。
有一组合段实有此乐趣——由一鸣和朋友逃课开始,到他回家路上责问丽娜是否因她告状致使朋友被惩罚结束;朋友陈晋南的回力鞋和马刺球衣成为被移置的元素,当一鸣在教室回过神来时,我们看到他穿着一件马刺logo的文化衫,而除此和结尾最后一幕之外的其他时刻他始终穿着印有"BERKELEY"的衣服,如果BERKELEY代指他对加大、美国的向往,在这一幕里马刺logo则是他怀念以至将自己代入离去朋友的象征,且导演还要借老师和同学强调他只有一脚着鞋;还有回家路上那只挂在书包上的回力鞋,回到房间也要把它摆在书桌上,在拍到房间里的一鸣和远端的母亲这一画面中,鞋子处在画面中心,且受到画面中唯一光源——台灯的照射,递进强调的过程亦象征生成的过程。
那么突如其来的呕吐和白日梦中动作的回流作为过程外的、例外而荒诞的瞬间,正是对这种后悔、难舍和「为什么自己也参与了却无须担责」的不解下所生成的错位感最具概括意味的人物反应,与象征符号的渐强形成张力。
另一段超现实情节也有类似的移置操作,出现在伟明的梦境中,哥哥带伟明去看祖坟时,镜头先是对着伟明,而后随伟明视线向前望去,变成了「此前给他们一家三口搭顺风车的司机」牵着「虚实间的伟明在泡沫厂遇到的小孩」在前方领路,镜头再往回摇,哥哥在中间,伟明依旧在后。
这是一组对位关系——在伟明的梦境中,日间遇到的司机和小孩被当作哥哥和他的儿时虚像。
还有伟国说这是爸妈的墓,然后伟明将梭子叉在父母墓前札起的渔网上,这个梭子是前面幻景中母亲给的,这些象征构成了伟明潜意识中对少年时家庭光景的怀念,堪比《野草莓》结尾中同样行将就木的老者看见年轻的父母和自己在湖边钓鱼时面露微笑的情境。
影像感不只是靠前述般符号的移置替换完成,还需要什么?
游戏性也不能显而易见地冲击或者替代影片的表意,如何掌控它?
对景别的选择就成为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关键。
回力鞋处在明亮的中近景的画面中心是一处范例;再往前倒,近景中一鸣和朋友在走廊聊天,一鸣被告知「保安据说仍在昏迷」,而后他转过身去,切到中景时浅焦镜头对焦在一鸣的背,随其视线缓慢聚焦到远景,远端的朋友被带走,带出的信息是他受到处罚,也就确定前者的「据说」为事实,同时一鸣与惩罚事件保持着一段距离……在这一段简练准确的镜头组合后,随即切到下一场景——被选作海报的深焦大全景墨绿雨林里,角色作为一个点移步入画,当我们在后面知其为超现实画面时,巨大落差的切换才不至突兀,反倒从远处看时人的朦胧感是契合该语境的。
结合影片的其他桥段,例如中近景时幕伶两次面对镜面抹泪,以及一次是扶着伟明进家门,另外两次的镜头运动是由幕伶要阻止一鸣问出真相、伟明吐血这样的被动情节中从镜面中快摇到现实;再例如两次隔壁家老奶奶的出走,第一次镜头从墙壁的特写到片警把老奶奶带回家到缓慢摇至站在楼下远看这一幕的幕伶,第二次镜头静置在一鸣取下并浏览录取信、喜形于色地跑上楼梯后十几秒,我们见证了老奶奶再次出走,两幕都不算长,但景别和情节都似自然流淌变幻而过般不泛涟漪;再如那段颇有一番设计的医院长镜头……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出一些景别的运用规律了——近景展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以及在它之下单个人物的情绪、心理。
中近景和中景在这个基础上纳入了城市空间,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人们的连接和情绪与空间存在的微妙关联,抑或它是怎么制造人之隔阂的,而不解释为什么;另一方面也在画框内留出空白给人物的外显表达,而非如近景聚焦其更细微的心理和情绪。
全景、大全景则不再以人为主体,物理空间占据了巨大的比例,可却并没有被压缩成平面景观,它似乎蕴含某种同样巨大的自然,将影片发生的一切吸纳其中,突然想到《春江水暖》,我会认为这也是它想做可显然完成度不及《小伟》的。
更系统性的镜头语言十分难得,毕竟凭自己的喜好滥用某一类语法造成空洞风格化问题的处女作不少,《小伟》不在此序列内。
但系统的、工整的同样可能发展为风格的、空洞的,为此作者给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决方案:以丰富明显的声音设计替代配乐,在医院长镜头一场戏中镜头运动由隔壁病房紧急求助的声音开始,随护士推车声和脚步声快速跟进,在幕伶折返时虽然画面仅容纳了她的脸,但背景里不同病房传出的抽水声、机器声、讨论声穿梭而过,就像战争片里在营造士兵穿梭过战场的感觉时那种处理方法,而回到病房伟明即将出院,也就是说它在同一个镜头内部就完成了时空转换,她竟是穿过了一个时空战场——显然,日常且丰富的声音加入填充了时空感,使得同一镜头内部的情景转换变得平顺甚至不易察觉。
通过有声源声音扩展画面外空间是较为常见的手法,可不必自始至终地使用也能保持生活感之连续,也可连接时空重新定义眼前的景观,却是《小伟》载着伟明回家的街道充满喧哗,一鸣回忆里的密林被赋予了神秘低语,氤氲缭绕的废旧泡沫厂传来熟悉而遥远的敲打声——日常的、离散的喧哗最终通往在永恒时间中低语的自然,体现出「阿基里斯与龟」式的连续性,永远存在的极限也就不再值得计量,追寻生活真实的答案需要的仅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答案。
回到影片整体上,纵观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虚实交错的叙事方式,相比暴露画框或者更高层级的叙事者,如《阳灿》中在老莫一场戏中姜文的画外音,或是《痛苦与荣耀》结尾阿莫多瓦在画框外的现身,其个人回忆部分以及它带来的叙事不可靠性自然是更隐秘的,故事也就不再依附于叙事者的回忆,而具备了某种原发动力,一方面它将导向更温声细语的影像气质,可另一方面,导演的自传回忆冲动又如何与故事的自发冲动调和?
不,这个问题在他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时已然模糊了。
当虚实交错的梦境替代和修补现实关系时,我们就很难分清这两种冲动到底是哪一种获得了发展,哪一种被抑制。
我可以理解回忆被选择以这种叙事方式转化为影像,可当做出这样的选择时,作品的充沛情感及美学价值就被置于首要位置了,而与自我、与回忆对话之意义则要次之。
7 ) 会有个人,陪在你身边
日后想起这部电影,我可能会先想起它的海报,那是一个镜头中的场景,山谷里密布的槌果滕占据整个画面,肆意而隐秘。
一个男孩在画面的左下角,小小的身影独自走入这无人之境,寻找另一只丢失的鞋。
鞋也许不是一定要找到的,但他需要一个理由,走进这原本不在他人生规划之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对于成人,是无法直面的荒芜庞杂,对于少年,却是一处巨大而陌生的迷宫。
海报上,两个水墨手写体大字:小伟。
片中无一主角名叫“小伟”,片尾写着:“献给我总写错他名字的父亲,小韦”。
导演将“韦”写成“伟”,误加的单人旁,也许是对父亲未完成的陪伴。
这一个人,是曾经的他,也是影片中的一鸣。
这部电影就像是导演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写着理解,写着遗憾,写着爱。
三线叙述,细节饱满,节奏从容。
慕伶身上能够让人共情的地方很多,在丈夫面前她是坚强的(修改病历、选红色的脸盆接吐出的血),在孩子面前她是真实的("是不是你也希望我像隔壁的奶奶一样再也不回来了?
"以及重压下食的那口烟),当她的丈夫和孩子在酒店那晚给她留下一片黑暗的时候,她又平静地站进了星空下的另一片黑暗里。
她的这一段人生,光明是丈夫和孩子带给她的,如果有一天同时没有了他们,她也会试着去面对。
一鸣,一个经常沉默的高中生,在面对自己的朋友的时候才变得开朗,在父亲笑的时候才会跟着一起笑,他对着他喜欢的女生喊:“反正每个人说的和心里想得也不一样,为什么要说呢?
”他回避内心的真实感受,只在他一个人的时候,会走到那片幽闭的山谷里,会一个人穿过马路跑到女孩的身边,会在街区的高低巷子独自飞奔。
他既要独自面对无法自洽的内心,还要面对生死离别的境况。
突如其来的成长始于对着父亲读他的录取信,因为病重的父亲,他动摇了自己的梦想。
从浙江回来之后,一句淡淡的“我打算参加高考”,是他面对母亲的坚定,这让他能在抉择中的不断反刍他疼痛的成长。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慢热的人,不需要有人告诉他怎么做,他们只需凭借自己的决定,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就能消化一路走来的困惑。
这个家庭,在经历了父亲的病逝之后,这间曾堆满杂物的房间,焕然一新,透过窗帘的橙色阳光,那件父亲从未穿过却印在一鸣心里的黄色恤衫,都暖在母亲的心里。
如果没有伟明那段如梦似幻的返乡之旅,可能这部电影就停留在对真实世界的美好剪辑里了。
伟明是个体面的男人,从他一丝不苟的西装和进口于慕尼黑的药,就知道他从没有放弃生之希望。
但在烧干了锅的那一天,他开始拒绝吃药,他只想用最后的时间,回到他的来处。
在回忆的世界里,他见到了母亲、哥哥、还有那个孩子(也许是童年时的自己),那是他抱有亏欠的家人,母亲给他端来一碗粥,哥哥在桌边微笑地注视着他,带他走上山头,找那一方渔网构成的安息之地。
可能伟明的父亲,就死于捕鱼,死在伟明戛然而止的童年。
伟明在少年时就逃离了那个没有父亲的家,来到遥远的广州,可能再也没有回去过。
而一鸣,在知道他的父亲身患绝症的时候,在那晚酒店的楼道里,在伟明说出留学的钱都给你留着的时候,一鸣却选择留下,留在他不知如何自处的青春期,留在母亲盼顾归家的眼神里。
伟明因为破碎而逃离,一鸣因为破碎而柔韧。
父子之间,完成了一个心愿的闭环。
影片中有三处场景的处理,我很喜欢: 出院以后,一家人坐车在广州的巷道里穿行,伟明主导发言,旁人尴尬附和。
车窗上一直有树的的倒影,将车里人的表情隐蔽于阴影之上,车忽到终点,树影簌地消失,一车人木然的表情瞬间赤裸在镜头前。
一鸣拿到录取通知书,飞快跑向家里,他的背后,是慢慢踱步上楼的邻家阿婆。
她再次离家出走,而没有人发现她。
这是真正的孤独,在电影里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上演着不忍细想的现实故事。
一鸣来到父亲的祖屋,听到踩缝纫机的声音,暖黄的光晕中,他也看到他的妈妈,告诉他自己去热一碗粥。
区别在于,给伟明端来一碗粥的母亲走了,而一鸣的母亲,还能看着他们父子在列车上玩闹。
伟明看见的是母亲的过去,一鸣看见的是母亲的未来,他要身处在这样的未来里。
整部电影的光影会根据情节而发生变化,逆光的希望、自然光的陈述、场景光的内心独白,都非常自然,让人看到导演对每一个场景的共情。
生活本来就有坎坷,但内心里,永远会有一盏灯,为照亮你的容颜而存在。
8 ) 《小伟》的声音设计
看完《小伟》后,觉得影片的声音做的非常有意思,于是找了下此片声音设计李丹枫的专访,找到了关于本片具体的声音设计的一些细节。
录音师李丹枫是录音届著名的录音指导,2018年,凭借其参与的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获得第55届金马奖最佳音效;同年,凭借影片《暴裂无声》获得第13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新锐录音师。
与贾樟柯、关锦鹏、刁亦男、毕赣等多位著名导演合作过:
下文是转载的关于本片录音设计李丹枫的访谈,在“深焦DeepFocus”等微信公众号上都有发表,现转载如下(也作为我自己的学习笔记):1月22日,《小伟》已于全国上映。
作为一部处女作,影片展现出的精巧技法和细腻情感无不令我们我们动容。
影片讲述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爸爸患癌而改变的故事。
妈妈的艰辛与隐忍,儿子的迷茫与抉择,爸爸对故土和亲人的惦念,这种传统中国家庭的含蓄与细腻浓缩在这部影片中。
《小伟》由黄梓导演与父母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来,黄梓拍这部电影是在寻找一种和爸爸对话的方式,也是在顺着家庭情感纽带审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
同时,黄梓导演也是在拍广州。
他出生成长在广州,广州的声音成为了他对生活理解的一部分。
在《小伟》的声音创作中,为了营造更为真实、丰富的广州城市氛围,莫非影画声音团队收集、创作了大量广州的声音元素。
影片中广州街道的声音,高架桥的声音,居民区和学校的声音,这些有着浓厚粤地氛围的声音共同营造出丰富的声音空间,仿佛让人置身广州一般。
这些丰富的环境音给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影片幕后声音制作的更多细节,莫非影画采访了导演黄梓和声音指导李丹枫,请他们聊一聊声音创作中的想法和感受。
关于影片幕后声音制作的更多细节,莫非影画采访了导演黄梓和声音指导李丹枫,请他们聊一聊声音创作中的想法和感受。
小伟·声音创作谈莫非影画:《小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原型是导演在广州的家庭故事,片中广州的环境氛围捕捉地特别精准。
首先想问导演,关于广州,您记忆里独特的声音有哪些?
有哪些声音最终运用在了影片中?
黄梓:我觉得广州比较特别的一个声音是高架桥上发出来的。
广州有很多高架桥,整个城市有一种层层叠叠的感觉,可能有两三层的那种高架桥,它们会缠绕在一起。
每每有车经过那些高架桥时,就会有一些特别的声音。
因为高架桥并不是完全平整的,有一些拼接的位置,同时也有些凹凸不平的位置。
这个声音是我觉得挺有城市特色的。
还有就是不那么特殊,但是对我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城市马路的声音。
我们广州是有那种防盗网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和我妈经常在防盗网上放上小桌子和小板凳,让我坐在防盗网里面写字,我能够更清晰地听到窗外马路上的声音,所以我对城市的声音和马路的声音都是比较敏感的。
影片第一个镜头,虽然是一个居民楼公共天台的环境,但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带到城市的声音,把一些城市的声音加进去。
有邻里的声音,比如做饭声,小朋友弹钢琴的一些声音,还有马路上公交车靠站、刹车、开门、重新出发的一些声音,我们都在有选择性地放进去。
然后就是城市里面一些人的声音,虽然没有听得那么清楚,但是偶尔会听到一两句粤语。
有一场学校课间的戏,我是单独又让录音师去补录了一场。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学校放寒假,学校里面是没有人的。
后来我们做声音后期的时候,我让录音师去到学校把课间的声音录了一遍。
后来我们贴到了片子里面来用,我个人还是觉得特别亲切的。
因为课间的时候,有些学生讲粤语,有些学生讲普通话,其实这个是特别广州的。
而且大部分学生是在讲粤语,就像是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大家的状态。
莫非影画:请问丹枫老师,在声音创作中,您怎样用声音进一步增强这种地域感呢?
广州的声音元素在声音设计中有哪些体现吗?
李丹枫:影片整体是一个城市的氛围,广东话的氛围。
当然是分阶段的,有一鸣家的环境氛围,学校的氛围,医院的氛围和街上的一些环境氛围。
我们希望能让大家感觉到这真的是在广州发生的一个故事,所以也补录了这些环境音,为了能够让广州的氛围更明确。
广州有城铁或者列车会从像高架桥一样的地方经过。
在妈妈和儿子一边走路一边说话,走过高架桥下时,他们两个稍微有一些争执。
我们觉得妈妈跟儿子之间的情绪跟铁道上列车驶过的气氛挺契合的,所以就在这里用上了列车的声音。
黄梓:我觉得我们让这个空间的层次更加丰富的话,也不用执着于一定要百分百还原这个空间里面本来应该有的那些声音。
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高架天桥,走过的应该是一些汽车,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用它原来的那种声音,而是替换成列车经过的那种声音,好像从他们头上经过一样。
列车的声音虽然那并不是这个空间真正的声音,但是我觉得特别能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空间。
莫非影画:就像导演所说,影片很注重人物心理空间的营造,有很多主观化的处理,比如妈妈在医院走廊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可以分享一下这里的声音设计上的想法吗?
黄梓:医院那里是一个长镜头,其实也分为了现实和超现实。
现实的部分就是有亲戚来探访,当亲戚走掉之后,剩下爸爸,整个房间的氛围又不一样了。
当外面走廊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镜头跟随着护士来到走廊。
虽然空间没有怎么变化,还是在医院,但是整个故事推进包括整个空间氛围的营造都是有转变的。
再到了电梯间,亲戚走了,儿子问了妈妈一个问题,妈妈扔下一句话就往房间走去。
这时又是另外一种她特别内在的声音,虽然还是同一条走廊,但是好像进入了她的心理空间一样。
把医院里面所有声音放大,同时把那种杂乱的声音拿掉之后,会营造出一种声音,我不知道能不能用空灵去形容。
这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听到的一种声音,可能有时候在我们的梦里面,或者说在我们意识模糊的时候能够听到,这是一种人物心理空间的特别的处理。
当妈妈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从视觉上面来说,或者说从情节上面来说,其实已经跨越了一段时间了,故事已经来到了爸爸准备要出院的那一天。
这时候护士打破了所有的这种心理空间的构建,把她拉回到了现实生活里面。
所以在走廊里面的那种声音的处理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贴合人物状态的,包括完成了一个时空的转换。
李丹枫:对,医院这里的长镜头在整个设计上面是分阶段的,我们希望每个声音都能够明确,这也是黄梓跟我当时聊得最清楚的一点。
他希望妈妈每经过一个房间,每经过一个人,或是每经过护士站等一个个点的时候,都能有声音发出来,这种阶段性的设计其实也能带着妈妈的心理一层一层地递进。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设计,设想每个房间里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有的房间里面会有冲马桶的声音,有的房间里面会有护士摇床的声音,有的房间可能是护士走出来的声音。
因为楼道的另一侧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在楼道另一侧也加入了一个人推着医护车从旁边驶过的那种感觉。
所有的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进入到妈妈的心理空间。
莫非影画:就像原片名《慕伶,一鸣,伟明》那样,影片分为了从妈妈、儿子和爸爸的视角出发的三个段落。
在第三段有很强的超现实感,声音也跟前两部分的感受有较大不同。
这里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呢?
三个段落的声音设计有尝试做区分吗?
李丹枫:三个段落从剪辑风格和结构上的区别就挺大的,那整个的声音设计上也是有很大区别,因为我们想体现三个人不同的心境和感受。
妈妈那个段落更多的是一种焦虑和焦急,所以会有我刚刚提到的医院的声音,列车划过的声音,有一点紧张感。
包括她在家的时候,经常会有广播声,这也是广东话的元素。
我们专门收集了很多广东话的新闻节目,在家里一直播放。
这里其实也是想把家庭放在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里面。
总体来讲这些声音都是相对嘈杂,或者说比较让人心情烦躁的元素,这个主要是妈妈慕伶的段落。
一鸣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空间。
我们有时候会强化他的呼吸感,有时候会去做比较意象化或者说主观化的处理,进入到他的内心情境,比如他在寻找那只鞋时就做了这种处理。
伟明的段落最明显的就是超现实。
伟明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伟明在老屋见到了他的妈妈和哥哥,整个空间都是很超现实的。
伟明在船厂不停地寻找时,整个空间是很梦幻的。
声音里有一些金属的元素,风沙静静的,但是你能听得很清楚,还有小孩在船上跑来跑去,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超现实的处理。
整个段落都非常静,我们想营造出一个孤岛的感觉,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是缝纫机。
一鸣隔着一层门听到缝纫机的声音,进门后见到了妈妈,所有的这些也都是一个特别主观化的处理,那其实是伟明的一个记忆。
黄梓:对,这里也是希望通过声音来叙事。
缝纫机的声音对于那个空间来说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是一个已经荒废了很久的老房子。
但是当一鸣在这样一个屋子里面忽然听到缝纫机的声音,他尝试找到这种声音,推开房门,见到了一个他想象不到的场景。
在一个缝纫机房里面,一个妇人在用缝纫机编织衣服。
当那个妇人回头的时候,他发现是他母亲。
母亲的穿着打扮跟岛上的村民是一样的,母亲跟他说着他听不懂的话,但是他好像又似懂非懂。
母亲跟他讲的那些话,像是一鸣裹挟着爸爸伟明的一个回忆,重新经历了一次爸爸年轻的时候想要离开小岛,去广州之前跟他母亲之间的一个对话。
莫非影画:还有哪些您认为声音设计上的亮点想要分享给大家吗?
李丹枫: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伟明的篇章,在最后的阶段,我们在火车之前能够听到刚才说的缝纫机的声音,然后缝纫机的声音慢慢地变成了火车的声音,这时我们看到一家三口正在火车上。
火车是离别或者离去的一个意象化的概念。
在火车里,爸爸不太情愿地吃药时,我们有一个火车从山洞驶过和错车的那种处理。
这些都是有现实基础的意象化处理,这些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在开篇的段落,我们做了很多点声源的设计。
比如说有小孩在练钢琴,有人在做饭,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听收音机看电视,也有很多广东话的氛围。
所有这些声音慢慢地聚焦到风铃声,聚焦到一个家庭,但其实在镜头里你看不到风铃。
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在船厂段落的风声上找到一些灵感,好像是一种过去的事情被风吹散了。
所以在故事的开篇,我们通过风铃声带来一个家庭的印迹,营造一种温馨的感觉。
因为一开始是妈妈在给爸爸染头发,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家庭场景。
这里也是把风铃做了一个意象化的处理。
在最后的结尾,电视上是爸爸和一鸣在讲话,房间里面妈妈和一鸣也在说话,就好像一个时空交错的感受。
然后镜头慢慢地游走到了外面,这时候环境音才加入。
因为之前一鸣的情绪是在对爸爸的思念里,在家庭中。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当镜头慢慢移出去,外面的环境音慢慢地也来了。
这里其实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处理。
黄梓:对,最后一个镜头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处理。
这里拍的是客厅,同时又拍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的母子有一个日常的对话,同时客厅电视机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里是有爸爸的,是爸爸拿着手机去拍儿子,有这么一个像家庭录像的片段。
在叙事时间线上面,那场戏爸爸已经离开人世了。
但是我特别希望虽然爸爸已经不在家了,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还在,他的影像还在这个家里面。
所以我借用了电视这个媒介,让爸爸出现在了家里面。
之后这个镜头就变成了爸爸的主观镜头,所谓的灵魂视角。
他徐徐地走出房子,走到了公共的大阳台。
当他走出屋子的时候,屋子里妈妈跟儿子的声音慢慢微弱,直到他走到阳台,彻底听不到妈妈和儿子的声音。
这时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同时声音上带了一点城市的声音,马路的声音,也带了一点点小区空间的环境音。
并不嘈杂,而是一种很纯净的声音,一种贴近生活的声音。
就这样完成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也预示着爸爸正式跟妈妈和儿子告别。
采访:沈桥 编辑:岳景萱附上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JHrI1Ruh5YPMtK3rCFoyw
9 ) 窩還是知道真正的廣州人是神馬德性的 這部座標系變換後的《廬山戀》騙不了窩英冥的雙眼
呵呵,起初窩還沒有仔細看,只是斷定粵語廣州佬裝逼成已經死亡的香港,正如21世紀的上海翻身農奴裝逼成已經消失的19世紀的帝國主義自由城市上海,不禁慨嘆,時間的偉大和裝逼的複雜。
後來窩仔細看了一下,發現這裡面的三個主演都是從香港進口的。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10 ) 不好意思问出口的问题
预期太高了,导演处女作的值得鼓励,但也具备各种处女作的问题,映后访谈导演说这是一个根据个人经历改编的电影,没有勇气将它拍成纪录片,我能理解这充满着主观的感受,但把事情讲清楚是另一个问题。
儿子线叛逆少年们翻墙,导致保安重伤昏迷,接着这件事儿又怎么样了呢?
这又与父亲癌症有什么关系呢?
直到最后我都没明白,儿子最后为何要放弃出国。
他家里到底有没有经济问题,父亲还说过国家政策好,有医保,留学的钱并没有花掉。
这是一个多么毛骨悚然的故事,母亲的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啊。
儿子叛逆期闹脾气,丈夫得知自己癌症闹脾气,都是冲向母亲的。
最后丈夫病逝,儿子放弃留学机会,这是为什么呀?
电影最后用一个超现实的情节,儿子与父亲重合,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这个情节又是如何导致的放弃留学的决定的。
导演说这是一个与自己父亲对话的电影,那么最需要沟通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跟母亲谈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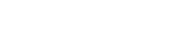

























































真情实感 难共
好看。特别温柔,开头和结尾像是《沙罗双树》,医院的长镜头拍得好。
看完也很想点根烟。ps才发现广州的景挺适合拍电影的hhh
和解是永恒的和谐,现实中的时空与时间交割……
非常棒的处女作,更喜欢“慕伶,一鸣,伟明”“All About ING”片名,概括影片3人3段,又可以说是关注当下,有现场感。生活化的戏码很容易进入。我就想问问导演当初他爸确诊是不是只做了影像和血检,不然不太可能确诊和办出院同时发生,我是听说肝癌可以不用取病理就确诊,其他癌一般先影像初步判断告知家属,然后取病理确诊考虑转肿瘤科还是回家姑息治疗,中间会有时差。不知道当初医院有没有建议导演爸爸转肿瘤科,电影感觉是直接从内科病房出的院?正常情况肿瘤科医生肯定要来会诊的,电影没有拍。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医院给开口服化疗药,以我的经验无论肝癌还是其他癌肝转移,化疗都是没什么作用的,即便姑息治疗也不该花这个钱。
3+ 慕伶4、一鸣4+。伟明段非常减分,在试图通过影像宽慰人物、触碰情绪之前必须要明确苦痛是切实存在的。“幽冥”的本质应当是忠实纪录生命在特定境况下的颤音,而非把人物放置在设计意图明显到可以一眼望穿的虚境(对比《前进青春》的超现实段落)。
IGC导演映后专场# 虽是以导演个人经历为蓝本,但依然照见了绝症/重疾对很多家庭的侵袭撕裂。镜头在一片混沌中晃进251房,又在白茫茫里淡出这个曾经的三人之家,三段式,三视角,再借用氤氲的魔幻现实穿插人在死亡与恐惧面前的游离,克制之下,更为动人。最佳三段:医院走廊长镜头(慕伶)、小区走廊尽头抽烟(慕伶一鸣)、凝视海风中的黑夜(三人)。另外,有几个配角貌似是配音的(医院食堂)一星鼓励广州本土导演!加油!!!
生活在广州的宁波人头一次在熟悉的粤语里听到乡音倍感亲切,导演对毕赣应该极为欣赏,所以寄托哀思介于写实与不断用媒介放飞自我暗示之间,导致后半段拖沓,也可能是删减的缘故。这个导演擅用媒介,可以说是我在广东见到唯一可以称是电影导演的人啦,可见我见了多少伪导演。可以期待他的技术,但或多或少我又感觉他的表达略简单,总有超脱不过港片的气韵,里面母亲面对两个垮掉的男人,真是伟大呀
一直有种父母是鲍起静(或者叶德娴)和张颂文的错觉。没有智能手机和高楼大厦,喜欢这种不那么现代化的现代生活流电影。不同于其它绝症题材影片,几乎没有正面刻画抗癌的过程,更没有刻意煽情卖惨,反而会给人更多触动。第二幕一鸣的部分拍得可真是太好了,当然最后一个灵魂视角的长镜头也堪称神来之笔。
故作深沉,实则内核空洞。想讲个故事,又想用超现实和空镜头炫一把技;想玩意识流,又发现故事不知如何讲起。所以前半段通俗叙事,后半段学样作态。太生涩了。
网络电影吗?
最后一个镜头,看着母子在角落说着话,电视里放着以前的录像,摄影机忽然站了起来去到熟悉的阳台,忽然的人称转变措不及防的戳中内心
有点儿四个春天+过春天的感觉。|太想吐槽moma百老汇了:昨晚订了票后发现写的是国语版?给微信公众号、微博留言和私信均未果,今早硬着头皮打了官网、app/小程序可以查到的几个电话,要么是录音声让订票打另一个,然而打过去是同一个录音声说号码不存在(不是真正的号码为空号),要么是微信小程序的外包说不清楚排片儿的事儿,要么是号码易主说打错了……堂堂一个电影中心没有任何有效的联系!只好抱着就算别处都国配moma也应该粤语的信念去了,现场工作人员说没人接电话了(所以设置了死循环的录音?),然后打开app/小程序看排片儿到底怎么写的,魔幻的时刻到了——粤语!(绝对是上午现改的!)工作人员同情(神经病)的眼神儿让我庆幸戴着口罩……
偽紀錄片的形式講述癌症的故事,演員就算嘴瓢也沒有被剪掉。可惜故事結構太散了,有很多文學性典故的引用,但具體想表達什麼,最後導演並沒有拆解。時間線混亂,爸爸和兒子的故事幾度讓我分不清是回憶還是虛妄,彷彿只有媽媽是活在現實生活中的人。btw,高翰文真的是就算髮際線後移、有肚腩都有魅力的演員。
在清明节祭祖之后返程的高铁上 无所事事的打开 iPad,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好的这部电影。一开始以为是少年的青春成长电影、但没想到写的是父亲患癌后的家庭故事,让人惊喜的是故事背景发生在广州 就非常贴合实际的用了全粤语对话,在普通话和京腔畅行的今天已然非常难得。电影中的儿子一鸣其实是一个和我很像的人,温柔细腻但又冲动叛逆。父亲罹患肝癌,母亲和家人极力隐瞒,最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父亲反而变得坦然,全片最文艺的一段就是一家三口回到父亲老家舟山祭祖,寻找亲情和生命的关系。电影又名《慕伶,一鸣,伟明》,是一家三口的名字,电影也以此分成三个段落、通过三人的主观角度来呈现家庭变化,之所以叫《小伟》是因为导演的爸爸名字里有「小韦」,虽然不同字但是同声,这是他能缅怀父亲的最深沉方式。作为处女作,已经很不错。
相比家庭情感的东西,导演对城市空间的刻画更能打动我,这也是为什么最后超现实的部分看得我有些不耐烦。
好碎好平…
导演拥有极为细致缜密的理性思维,在景别构图的平衡、剪辑的精确度、视点的转换节点和运动镜头的速率停顿上都下了大功夫。但此类以极端情境反逼人物状态的电影,文本的咬合一定要足够紧,才能制造出具有强烈代入感的戏剧漩涡。遗憾本片依然存在不少泄气的段落,在情感层层推升的过程中制造出不少阻力,所以直到结尾我们也没能真正看到脱离出事件之外的人物,不论是慕伶、伟明还是一鸣,都差了一口气。Ps:旅馆大风停电那场戏蛮惊艳的。
喜欢,导演处女作表现太好了,感觉比很多导演还要成熟。台词写得自然真实,镜头调度也很优秀,第一章医院的长镜头拍得真好。比起最后一段似梦非梦的场景,我更偏爱前两段,对广州人来说真的太熟悉太亲切了。导演说不喜欢架空城市的剧情设计,确实做到了。结尾那一段真实录像眼泪横飞。
感觉缺失了好多的情感。全程很平庸,除了列车卧铺车厢里的人情味,其他的都很平淡。像坐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