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剧情介绍
《气球》故事发生在藏地,讲述灵魂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主人公达杰一家因一只普通的避孕套卷入了一系列尴尬而又难以抉择的事件当中,他们原本宁静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破,生老病死如日月流转,当灵魂遭遇现实的挑战,该如何抉择?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艾米利亚的孩子酋长的男人被勇者队伍开除的驯兽师,邂逅最强种猫耳少女天才麻将少女假如幸福来临城市游戏剪裁魔法师2生死竞赛2老师错了脱狱之王第一季湄公河戊子风雪同仁堂今天开始当杀手大西南剿匪记黏人俱乐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拳脚之路好男儿之情感护理嫁给我契约夜行夜珍惜爆裂少女分贝人生虎胆侠情时尚王国黑三角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醉侠苏乞儿战友耀眼的你少校
《气球》长篇影评
1 ) 藏族群体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冲突下的现实困境
从《塔洛》开始,万玛才旦钟情于把玩各类符号和隐喻,这也许是他最近几部作品受到越来越多影评人青睐,以及在各大国际影展上屡屡现身的原因。
上一部《撞死了一只羊》还得到王家卫的垂青,由其亲自担任监制,打造出强烈的迷幻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藏语影片的表现力。
这部新片《气球》早已在去年威尼斯上首映,我有幸在电影节上观看了世界首映,等了一年终于在国内上映。
两次的观感相差不大,他对文学作品的影像化改编最出众,但是过多的符号和隐喻依然掩饰不了其匠气,尽管这次已收敛不少。
这部《气球》有别于《撞死了一只羊》的“王家卫”风格,万玛才旦又返回以往熟悉的现实主义质感,用温情幽默的口吻讲述80年代计划生育时期在藏民区的残酷故事。
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妻子一直使用安全套作为避孕措施,但当丈夫的父亲去世后,妻子竟发现自己再次怀孕。
丈夫认定是父亲死去的灵魂转世降临在胎儿上,要求妻子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妻子却极不情愿。
这个故事改编自导演本人的小说,他对小说情节进行影像化的过程中,处心积虑地糅合各种符号,作为隐喻的基础。
这些符号往往巧妙地成对出现,形成强烈碰撞的趣味效果,隐喻着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男性与女性、生与死之间的对立关系。
如果公羊配种、草原上骑摩托车、试管婴儿的新闻显得太过直白肤浅的话,那么作为核心意象的“气球”则具有无比精准的象征性。
“气球”既是孩子们的玩具,同时也是大人的避孕工具,更是整个故事里女主角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导演巧妙地将女主角置身于各类冲突之中,揭露出在传统文化、宗教观念、男权压迫下,女人的性意识和生育权遭到无情剥夺,而代表女性意识觉醒的两位女性角色成为难得的一抹亮色。
不过,导演为女主角设计两难处境时考虑得并不周全,她坚持要堕胎的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但细想之下却是站不住脚。
万玛才旦无法像伊朗导演法哈蒂那样,令核心人物处于道德两难的焦灼处境,宗教和世俗的对立面在此看来并不强烈,这无形中便削弱了后半段情节的戏剧张力。
这次看的时候,我有一点新发现。
之前感觉重点都放在了女主角身上,讲述她如何主动争取权利而对抗传统专制和宗教压迫,但这次发现这并非完全是女性视角下的反抗意识叙事。
作品更像在呈现整个藏族群体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冲突下的现实处境。
不仅女人深受压迫,男人也深陷困境:男教师无法与心上人相爱,老一辈男人跟不上时代,无法接受新事物,面对开放观念显得蛮不讲理,而男主角更因生殖崇拜的男权思想和教义规条而失去了妻子。
最无辜的要数儿子,年轻一代似乎无法走出父辈的阴影,沦为继续打压女性的帮凶(父亲与儿子在医院劝导母亲的一幕令人震惊!
)这种恶性循环的父权社会结构和意识似乎暗中契合着传统藏族文化的轮回观念,生死轮回在此显现出无法摆脱的宿命意味。
然而,导演又在结尾留给观众一点希望,红气球飘扬在空中的镜头接上一张张静默的人脸剪辑,散发出一种意想不到的诗意。
那不仅是象征着新生命的红气球,还可能是导演对藏人未来的乐观期望。
2 ) 飘荡的气球
气球是经常被导演符号化的一种表达,时而演绎自由,时而诠释欢乐,而电影《气球》也在经历了各种电影节与话题关注后,如期而至。
影片依旧带有万玛才旦独特的导演色彩,在藏区的语言环境之中,关注最普通的人的故事,将那些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故事,一点点地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呈现出来。
《气球》本身的故事并不复杂,影片将故事的核心,集中在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人物的命运选择上,以女主人公卓嘎的意外怀孕作为主要冲突点,讲述了青海藏区牧民达杰一家的故事。
文化与信仰的不同给藏地人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在《气球》中,这层面纱却渐渐被导演掀开,向我们娓娓道来藏区人物的真实生活。
人们即使羞于谈性,但仍旧有渴望,就像卓嘎一直将丈夫比作种羊,说他晚上在床上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而在谈到这些时,她的脸上也总是带着羞涩,因为我们知道,在她想用尽可能满足丈夫的同时,她也是在满足自己;卓嘎的妹妹,一名正值芳龄的女孩,因为一段失败的爱情过往,竟不惜剃发为尼,从此阪依佛门,不再为爱欲牵动,但即使这样的她在面对前任的再次出现后,我们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放下这段感情,她一切的举动都在诉说着她对感情的焦灼。
而这就是影片的精彩所在,藏区有着极其浓厚的藏地文化和宗教信仰,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的人们,自然在性话题方面有些蹑手蹑脚,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思想漂泊的漩涡。
所以在观影过程中,人时常会有些沉浸后的恍惚,不过导演所选择的拍摄手法却为故事的讲述增色不少,所以最终我也一点一点地被故事所说服,对故事中的人物也多了些感同身受。
说到《气球》的拍摄手法,不得不提下导演这次所采用的大量长镜头跟拍。
在长镜头的展现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凸显地如此生动:你会看到人高马大的达杰在追逐羊群时是那样勇猛与热烈,他带有野性的荷尔蒙呼之欲出;你也会看到在送葬爷爷时,各大僧人围聚在狭小的房间中,暖黄色的蜡烛摇曳在他们脸上,家人们在一旁都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多了几分克制,他们在用一种隐忍的方式去送别亲人;你同样可以看到卓嘎将妹妹前任送来的图书扔进火里,妹妹可以不顾一切的将手伸进火内,不畏炙热只为拿回那仅有的依恋。
而这些在长时间跟拍镜头的展现下,你很难去定义演员的表演,而是能热切的感受到他们对角色形象塑造上的敬业与人“人”合一。
除此之外,整个影片为了能与主题相映衬,在画面色彩上也偏冷色调。
清冷的画面,多了些沉淀与冷静,也与藏区经典色系形成对比,多了些暗潮汹涌。
而在这种色彩选择的衬托下,影片中的几段超现实片段才能更加突出,影片结尾那一直在空中飘摇的红气球才会看上去如此浓艳。
而这红气球不光代表着被吹大的避孕套或是卓嘎因怀孕而挺起的肚子,也代表着一个个生活在藏区的藏地人民们,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摇曳着,不断成长却又不断自我否定,寻觅生活真正的意义所在。
藏地人民的生活,与轮回转世的命运紧密相连,因着独特的宗教信仰,而拥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孩童背上长痣,被长辈说是奶奶转世留给他的记号;老人死去后,家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安葬,而是向上师请教老人转世的去处;甚至丈夫强迫妻子生下孩子,就是奢望能为死去的亲人前世接环……万玛才旦用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了一个藏地女人乃至藏地人民的命运,这个看上去是讲述藏区家庭和生育、生命和信仰的故事,是万玛才旦一直探讨的传统和现代两种观念碰撞的主题,以及这些生活在特有文化背景里的藏族人民,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到生活的答案。
片中所述的困境虽然被放在了特殊的背景里,但这份迷茫与自我怀疑是所有人都可能遭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这份信仰并不一定是带有宗教意味的,但它都有很大的概率会和你的现实人生相撞,令人不得不面对如何抉择的难题。
所以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部类型电影,它更像是一部普世电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影,照应到内心的种种困惑。
看着影片结尾那飘摇在空中的红气球,像是人们想要得到答案。
我们终究还是会发觉,文化的差异带不走人们情感的共通,信仰的不同抹不灭人们内心共同的欲火。
人生或长或短,起起伏伏,不妨坦荡些,不妨勇敢些。
3 ) 那个把手伸进火里取书的女人
读过《乌金的牙齿》,基本不记得有妹妹这个人物。
但看完《气球》,片中出家为尼的妹妹于我个人而言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她更未知更独立,怀揣着隐秘而强大的情感。
虽然她一出场就很不具体,镜头跟着她的脸晃动,大半张脸都被压低的深红僧帽遮挡,基本只能隐约看到下颌的线条,很难找到她的眼睛。
她心不在焉地看黑板报和粉笔画,转头的频率揭示了她的紧张,和其中微妙的期待。
虽然她被昔日的恋人德本加认出叫住时仍旧木着脸低着头,视线还是会静静地向上移动,小心翼翼地一看,说到他戴起了眼镜的变化,做出心如止水充耳不闻的姿态还是会被叫住,还是会在抚摸德本加送的名为气球的书时露出微微笑意。
外甥汪洋不是说好自己回家吗?
她为什么要去接他?
难道不是抱着和德本加见面的期待?
为什么会被黑板报吸引?
是不是看到了德本加的粉笔字迹?
她真的不知道德本加是外甥的老师吗?
我很怀疑。
因为当姐姐把那本《气球》投入火中,叫她忘了过去和德本加时,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找东西去抢救,但来不及,火那么旺,都没顾上烫不烫手,本能地伸手去取。
火那么旺,没有任何呼叫,她那么稳健而果决地把书取了出来,把火扑灭。
用烧伤的手抚摩着破损的封面。
那么有力且动人。
姐姐是想借助火来控制妹妹的情感?
但能驱使阿尼火中取书的情感也许比火要热烈的多。
德本加也那样慌张过。
他来找阿尼,被姐姐阻拦,说要给他一件东西。
他站在一堆牛粪前,在那一大堆燃料前,就是点不亮那一根烟。
他拒绝收下那本书,因为这是送给阿尼的礼物。
姐姐强硬地说,要么你拿走要么我烧掉。
他失望地接过书翻着,烟那么不易被点着,书却被烧得那么轻易,他翻书时甚至还散落下几片灰。
他那么不知所措,只能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
他想点燃的明明是那么易燃的东西啊,只是一根烟,只是一个坦白化解的机会。
但他就是点不亮。
阿尼和德本加的过去令人好奇,但因为姐姐自作主张的善意谎言和决绝的阻止,化解他们误会的机会因此错失。
那本书没有被读过就被几乎烧毁,我们没有窥探它的机会,只见过其中一个黑色的背影,而《气球》小说原文中并未嵌套气球这本书。
女人之间的相互为难是你来我往的。
因为命运的困境笼罩着她们每个人。
明明都是受害者,在姐姐为怀孕为难纠结之时,妹妹说的却是,上师怎么会错呢?
她和俩父子一样规劝姐姐把孩子生下来。
阿尼一身深红,瑀瑀独行,和最后的气球也很像,特别是飞走的那一只。
4 ) 一位女性如何失去自己的生育选择权
这个电影值得一个8分,但我还要因为个人情感多加一星。
整个电影反复征用的意象都指向一个东西——性。
比如小孩子用避孕套吹出的气球;比如接送种羊来配种;比如女主的三次去医院,一个要避孕套,一次查出了怀孕,一次去打胎;比如当尼姑的妹妹对性的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有关性的电影,它呈现出了在彼时彼地的文化下,人们对于性讳莫如深的真实状态。
但它不仅仅关于性,它更是关于性别——一位女性如何在周围男性有意无意的推动与胁迫下,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育选择权。
两个小儿子拿走了自己的避孕套+ 丈夫不顾无套的状况→女主怀孕公公去世+活佛说灵魂转世到自己家里→丈夫逼女主留下孩子大儿子和丈夫冲到医院阻止打胎→女主心灰意冷打胎失败周围的每一个男性都有意无意地在为这件事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连妹妹这位女性也劝她不要打胎,这是因为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立场。
只有医院的女医生告诉她“你都生了三个孩子了,我们女人来这个世界又不是为了来生孩子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生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是很痛苦,风险很大的一件事,况且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
当女主思来想去,艰难地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决定还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家庭考虑,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再生一个就会更穷困)而丈夫的反应是“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你这个妖女,没良心”、“你自私”,并且扇了女主一巴掌,女主掩面啜泣。
(虽然第二天他道歉了,但这样的伤害真的无法原谅,况且道歉以后他依然冲到医院去阻止打胎)最后,女主对出家的妹妹说,我现在觉得出家也挺好的,我也许以后也会出家。
我一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灭绝师太会要周芷若“断情绝爱”,因为在这种男权文化下,女性很容易被逼着成为生育机器,失去自主权,总有人想替她做选择,当她“不听话”的时候软硬兼施逼她听话。
想到自己的外婆生了九个儿女我就觉得特别心疼,也就是说她在近十年里一直在怀孕生产,而最后一个孩子一定是个男孩。
看到女主被丈夫扇了一巴掌,我在电影院里握紧了拳头。
5 ) 信仰歧视的风险在这里存在吗?
刚刚有个学妹跟我讨论这个片子,提到她男朋友我学长的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记录一下。
我学长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研究民俗学的。
他说非常不喜欢万玛才旦这样的导演,因为他在故事里加入了个人偏见,容易引起“信仰歧视”的风险,而信仰是不应该被歧视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在讨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女性主义进入这个文本的路径。
信仰歧视的风险对万玛才旦存在吗?
这似乎是在批评他提供的典型的精英叙事已经完全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去反思和批判貌呈“落后、愚昧”的藏地信仰了。
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并不是。
当然万玛才旦确实是足够聪明,规避这种嫌疑,他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给片子一个开放式结局,医生代表的现代社会生活观念和医学理念与丈夫坚持的轮回信仰,虽然发生冲突,但是没有哪一方“赢”。
当讨论走到这一步,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实不可避免的浮现了出来——当两种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唯一的承担者是处于叙事中心的女性卓嘎。
这引向那个问题:女性的被压迫和被置于客体,不仅发生在性的关系里,家庭结构内部,还发生在信仰冲突里面。
一种更隐蔽的压抑与被压抑:在一个社区经历观念更迭的过程中,最先被剥削也被剥削得最狠的,是女性。
医生和丈夫所代表的两种信仰大可以针锋相对,但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场域正好就在卓嘎的子宫里,而且不在这里不得以展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难说万玛才旦“歧视”了哪一方。
而且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一条妹妹和男教师的线。
理解妹妹的行动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顺“信仰歧视”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单薄,我现在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切入这个形象能为“信仰歧视”的这个观点提供论述或反证。
诸位友邻可有想法?
6 ) 女性的困境与觉醒,《气球》中丧失的生育选择权
2024年是中国女性电影元年,从《热辣滚烫》到《出走的决心》,从《从今以后》到《好东西》,女性电影如突然觉醒了似的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获取大量好评。
在这样的基调下,反观2019年的《气球》,虽然不是以女性为主题,但依然从某种意义上诠释着女性的困境与觉醒。
不少人说,《气球》是万玛才旦最好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
我不置可否,毕竟《气球》是我看的第一部万玛才旦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藏语电影。
对于中国的方言电影,看得最多的当然非粤语电影莫属,四川话、武汉话、陕西话、上海话,以及贵州话也常常出现在电影中。
但基本上以上方言,听上去跟标准的国语电影没有什么障碍。
倒是藏语,着实是不得不靠字幕的翻译,像是看外国电影一般。
然而,虽然语言上并不相通,但《气球》却切切实实是一部颇具中国本地电影内核的优秀作品。
《气球》的故事来自导演万玛才旦的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的一篇。
是的,这位已故的导演还是一位小说家。
他的许多电影作品的剧本都来自于他自己的小说创作,比如《塔洛》,比如《静静的嘛呢石》,比如《撞死了一只羊》。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其中却涵盖了诸多人与人间的关系和冲突。
小到夫妻间的、父子间的、姐妹间的,大到信仰与现实、现代与传统,乃至希望与生命的传承延续,都一一能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体现。
作为一部以西藏牧民为社会背景的影片,《气球》呈现出的不只是一幅幅美丽的藏地风光,更展现出了一个与现代都市生活截然不同的风貌。
在这个相对传统保守的群体中,对宗教的信仰,对父权的推崇,都仿佛把我们拉回了几十年前的社会一般。
而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影片表达出的对家庭中女性的困境与觉醒的阐述,更尤为突出。
影片中两位主要的女性角色无疑是卓嘎和卓玛两姐妹。
姐姐卓嘎是育有三个孩子更操持家中一切家务的母亲,妹妹卓玛是因一段孽缘而出家但依旧心存一丝红尘挂念心的尼姑。
两相比较之下,个人更喜欢索朗旺姆所饰演的姐姐卓嘎的角色。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卓嘎是立体的,她有着传统女性相夫教子的一面,也有作为长姐当机立断为妹妹斩断前缘的一面。
在人物发展上,卓嘎更有自我觉醒,冲破世俗和传统的勇气,并赋予了父权社会下女性抗争得以绵延的希望。
生育是影片最重要的主题,虽然似乎从一开始影片就将生育阻断,无论是两个被吹成气球的避孕套,还是随处可见的计划生育的标语;但电影又似乎从一开始就被生育充斥,无论是借来的种羊那沉甸甸的雄性器官,还是关灯之后男人无法抑制的欲望冲动。
《气球》并不将这一主题隐晦表达,占据海报显眼位置的红气球与姐姐卓嘎的腹部刻意重叠,鲜红的色彩夺人眼球,凸显着在母体中被孕育的生命。
女性是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姐姐卓嘎的形象带着羞涩和顺从。
保守的思想让她羞于和男医生讲诉自己的妇科需求,顺从的驱使又让她甘愿结扎能厚脸向女医生讨要计生用品。
她知道丈夫欲望强烈,更不惜冒着再度怀孕的风险来满足丈夫。
如果说这样的顺从,感受到的更多是卓嘎的贤淑,那这场生与不生的选择风波,则将冲突激化成为女性抗争的矛盾。
生活的捉襟见肘让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在面临再度怀孕的时候,陷入了困境;上师口中腹中胎儿是上代转世的箴言让丈夫与大儿子都坚定不移地选择将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
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可以让他们抛却一切现实生活于不顾,高高在上的男权思想更不允许卓嘎拒绝生育。
在这一刻,女性似乎成为了生育的工具,也是其最主要的功能。
正如羊圈里那只总怀不上后代的母羊一样,丧失了生育功能的雌性动物的下场只能是送进屠宰场。
在《气球》中,卓嘎是勇敢的,她敢于挑战深入人心的宗教,她敢于不顾家人的反对独自进行流产手术,在她质疑上师的判断之时,她已是带着觉醒的特质的。
虽然遗憾的是,她冲破藩篱的壮举最终还是被暴力冲进手术室的丈夫给阻止,但她的逃离却象征出了莫大的希望。
我们不知道卓嘎到底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此行是否真会毫不回头,虽然这场逃离略显突兀,但这逃离的勇气却与《出走的决心》中李红的奔赴远方,都彰显着被困境束缚的女性抗争后的觉醒。
手持拍摄下的观感充满着不安定,时时被障碍物刻意割裂的镜头代表着每个人的各怀心事,两个女人远走的开放性结局,无不体现出了导演的独特用心。
7 ) 备受瞩目,一票难求!它终于公映了
首发于公众号“影探”公号ID:ttyingtan作者:黄四郎转载请注明出处
>>>>藏地新浪潮《气球》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又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
本片曾在去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在国内各大影展上,更是拿奖拿到手软。
万玛才旦曾经,他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
2002年,他拍出了小成本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成为了藏语影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此,以藏族人的身份,探究藏族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关系,成为了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静静的嘛呢石》如今,他也是一个领域的开辟者。
在戏剧性的故事,与深刻的主题外,万玛才旦还给作品包裹上了一套“超现实”外衣。
2016年的《塔洛》,被万玛才旦赋予了黑白影像的厚重感。
2019年的《撞死了一只羊》,更是在监制王家卫的点拨下,呈现出强烈的迷幻质感。
左图:《塔洛》右图:《撞死了一只羊》强烈的个人风格,也被业内美誉为“藏地新浪潮”。
这位文质彬彬的四字叔叔,总能用诗意的镜头,去描写接地气的故事。
>>>>气球与羊威尼斯电影节上,《气球》曾被电影史学家让·米歇尔·付东盛赞为“本届最美的电影”。
《气球》的美,不仅体现在美轮美奂的藏地风情上。
它更是电影创作中,写意与写实的平衡之美。
写意是感性的,写实却是理性的,能将两者兼容在同一部电影中,并不容易。
本片却完美的做到了。
手拿“气球”的孩子在羊群中奔跑先说写意。
顾名思义,“气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在大人眼中,它象征着安全套,象征着女性的子宫。
在孩子心里,它又是童趣的代名词,是至纯之物。
透明的气球,总能亮到反光。
而不同人看到它,映出的,又是不同的模样。
本片结尾,大红气球飘在了空中,所到之处,迎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都与“气球”或多或少发生了故事,但心中所想,却并不相同。
这种基于同一意象引发的多义性,浪漫至极,余味悠长。
片中的另一个意象,则是羊。
与前作《撞死了一只羊》相同,片中的羊,正代表着人。
片中,女医生曾用种羊比喻达杰,暗指其精力充沛,性欲旺盛。
达杰捉羊而母羊正是对女主卓嘎的指代。
配种前,达杰曾将一只母羊单独拎出来,放在一边待宰。
用他的话说,这是只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羊,留着已无用处。
在将女性视作是生育工具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说辞,无疑代表着对女性的暗贬。
再说写实。
万玛才旦的妙笔在于,即便是超现实的镜头语言,也一定会包裹着接地气的社会表达。
《气球》海报上,就已经提出了本片的核心矛盾:“信仰与现实将如何抉择?
”
在藏族文化中,轮回转世是最核心的信仰。
本片最大的冲突,正是因家人笃定即将出生的儿子是爷爷的转世而起。
家里的大儿子江洋,天生就有一颗大黑痣,与早年逝世的奶奶一模一样。
无论爷爷还是江洋,都对转世之说笃信不疑。
但不久后,两个小儿子却做了一个梦。
他们将哥哥身上的黑痣抠下,顽皮的向前跑,哥哥江洋则在后面追,拼命想要拿回黑痣。
两个小儿子这梦看似费解,但若细心解读,不难发现:小儿子尚且年幼,三观仍未建立,尚未对信仰产生意识。
在如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对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
所以,他们才会抠下那颗痣,想把它丢弃在别的地方,消除灵魂转世的说法。
而哥哥江洋,则代表着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少年。
在影片最后,也正是他的劝阻,暂时遏制了母亲想要堕胎的想法。
所以在梦中,他才会一直追,想要那回那颗表面属于自己,实则属于传统的黑痣。
大儿子 江洋自幼生长在传统藏区,长大后又在北京读书的万玛才旦,正是在用这具有魔幻色彩的梦,表达着自己对于信仰的困惑。
科技愈加发达,祖国愈加昌盛,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闯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可面对着与传统相悖的现代理论,他们也陷入了迷茫的抉择。
是拥抱现代,还是皈依传统?
这两种不同的思潮,无疑撕裂了如今的藏区社会。
爷爷质疑电视节目中的现代科技>>>>女性视角如果说,上述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只是这类电影的常规操作的话。
那么万玛之所以是万玛,则在于他的升华。
《气球》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
女主卓嘎面对生育绑架,不惜以一己之力反抗传统,只为那一丝觉醒的萌芽。
卓嘎与丈夫有着巨大分歧卓嘎面临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据调查分析,传统游牧民族,曾长时间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
从六胎到十几胎不等,女性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毕竟在藏族文化中,怀孕是上天的恩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阻隔的。
正因如此,安全套等计生用品在藏地的推广中,曾经遭受过重重阻力。
女医生劝说卓嘎这是一个发生在藏区的故事,却绝不仅仅是一个藏区的故事。
《气球》打破了少数民族身份的桎梏,探究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女性长久以来都被生育绑架着。
卓嘎质疑信仰本片发生的年代,导演并未明确说明。
海外放映时,为了方便外国观众理解,万玛特别注明本片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可是,片中电视所播出的试管婴儿新闻,发生在1978年。
而结尾卖羊时候用到的人民币,则是1999年才正式发行的第五代货币。
在四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bug,而是有意做出的朦胧性。
发生在哪个年代,无所谓。
因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无论何时都没有被解决。
文/黄四郎
8 ) 内地院线的奢侈|气球的背后:人性与慈悲,大于古老的歌谣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观影点映,映后与万玛、陈丹青、谢飞老师做交流与讨论,有所收获。
陈丹青说:“我也喜欢万玛的其他作品啊,包括弄死那只羊。
”老师也真是可爱。
说回电影。
电影从家庭、宗教、自由、生活几个维度讨论藏地人民的生活,设计可谓是精良的。
例如,一白球一红气球,一姐一妹,一羊一人,阻隔的视听体验。
这些虽不是内核,只是小的元素,但值得说一下。
影片海报中,红气球即是气球本身,也是怀孕的肚子,即是希望也是灭亡。
正如影片最后一个气球被扎破,一个气球放飞,完美扣住了影片的叙事主题。
白气球是避孕套,影片的第一个长镜头就是“避孕套”视点,白与红的对比不只是冷暖色调的延展,更是避孕与子宫、受孕生命的象征。
关于羊,整个片子都在讨论种羊,也在讨论“结扎人”,羊是放情的、野蛮的、需要优质品种,交配繁衍为生命任务的,而人是克制的,受伦理与信仰限制的。
影片开场的几组对话,在画面中的视听上,万玛始终拿电线杆和栏杆等东西阻隔两人,人被阻隔,也是命运的不相关,俗话说,悲欢不相通。
这只是视听和符号的表意。
绝不止这些。
影片的宣传语是信仰与生活,但影片的落脚点不在此。
正如陈丹青老师今天的发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文化下,不完全是一个宗教信仰下,而是在同一个人性下生活。
”作为藏地导演,这部电影确实有所反叛,甚至anti-religion。
女主角甚至说出了“他们(转世)也有可能出错的”这样的禁忌言语,我称之为“有因的反叛”,具体如何延展,却是不可讨论的,也难以和解的命题。
人性,是最终的命题,也是唯一值得在意的,影片只是以点带面,传统功夫以点到为止。
说这部电影是慈悲的,因为万玛在阻隔、交融、与对比中时刻注意爱与人性的温度。
妹妹的绝对禁欲与姐姐的幸·性福生活成绝对对比,方知宝贵。
而姐姐在最后却说“我还不如做尼姑,没有牵挂。
”是的,影片希望达成和解,却无法真正展现和解,导演万玛在现场说:“所以只能依靠梦境。
”比如海边捉痔,哥哥的“奶奶转世痔”被弟弟拿下来看,希望这转世只是身上一片贴图,而不压于人身。
再比如,在超现实的场面中,青海湖边的孩童在奔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
脱离了梦境,女主人公在现实中却只能寻羊问路,寻鱼问水,一片倒影反射回来,却是自己苍白的脸。
《气球》先在中国调色,而后拿到泰国调色,把绿油与金黄的草丛和土地,全部改成了冷色调为主的基调,这是一小插曲。
如果没有万玛在藏地的生命经验,实在难拍出这样的东西,难怪陈丹青与谢飞老师都说,在其中看到了爱,这是万玛之前的作品也共有的关怀。
当影迷朋友问到导演:是否符号化的表达大过内容,万玛说,这部片子里根本没有刻意的符号,因为信仰、生育、放羊,这只是最真实的生活,是每一个藏地人。
这话最为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慈悲。
听起来矫情的话,在真实的《气球》里,在生活里,也变得沉重了些许。
文:Travis 允许商用转载
9 ) ……
在#IFFAM 4th展映单元看了气球🎈整体上,影片在主题和剧情上都更接地气,更能让大众看明白。
这部影片应该会有更多的受众,估计会是大家更喜欢的电影。
镜头语言和剧情都是刚刚好的干脆和点到为止,甚至内化有一丝丝商业片和喜剧片的影子,会使更多人喜欢吧。
纯粹个人感受而言,和以前的影片相比,看完有一些失落。
看完一身轻松,不会再让你思考更多、更深、更模糊的东西。
即便有一些日常生活中吊诡的真实呈现,有关藏族女性,有关社会中的宗教,呈现就完成了全部的思考,甚至提供了一种困境式的解答。
或许这是功力上达到了一种大道至简的境界,但纯粹个人感受上,还是觉得少了一些更个人和更独特的部分。
或许,一切都在变化……
10 ) 《气球》:符号密码与生命轮回
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
——波伏娃“可见之人,可见之物只有作为意义的符号出现,才能成为电影艺术的因素”。
影片中编织着符号与意象的密码,共同构建一张密而精巧的符号之网,展示了女性的苏醒之路。
卓嘎与母羊:从压抑到觉醒电影多次暗示,卓嘎和母羊存在某种关联。
母羊与卓嘎最主要的连接是“生育”功能。
卓嘎在家中育有三子,并怀有第四胎,可称之为“生育机器”。
母羊的的生殖功能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
电影中,母羊两年未下崽,已经被视为“无用”,只能将其卖掉保证收益。
而卖母羊的收入则是为了供孩子江洋上中学,从生到死,母羊一直处于一种被支配和被牺牲的状态。
卓嘎生养小孩、照顾老人、管理羊群和处理家务琐事,都成为女人生活的日常和日积月累的重担。
当然,电影中其实并未苦大仇深的刻画女性被压迫的状态,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展示。
梦见母羊产小鹿的胎梦,也预示着卓嘎的孕育。
为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卓嘎主动避孕,要避孕套甚至结扎,来对抗最原始的男性生殖力量。
而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现代化的医疗科技有关,结扎、避孕套等计生用品和医疗手段,也是帮助卓嘎更好保护自我的一种方式。
在藏族地区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下,生育是一种至高的使命,因此,卓嘎避孕、流产也是对传统和宗教的反抗。
卓嘎的努力就是对男性生殖力量和权力施加的接纳,承受与消解。
卓嘎去卫生所验孕时,镜头反复展现一只被拴着的母羊,母羊用尽全力挣不脱也逃不掉,卓嘎的验孕结果正如母羊一样,因为一次意外怀孕而被套牢,就像无情命运绳索的扼制。
卓嘎已经面临生育的痛苦,而第四胎更要面临政策的巨额罚款,宗教、政策、还有父权力量的重重压迫,卓玛面临重要的选择。
在此,女医生则是扮演着一种现代医疗科技和思想传播的使者,女医生与卓嘎交流让她难以启齿的性生活,是对女性欲望的一种疏口;给卓嘎避孕套,缓解生育压力;在卓嘎意外怀孕后劝解建议流产,为自己考虑。
从始自终,她站在卓嘎的角度上,努力让她从一种传统的为家庭牺牲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促醒了卓嘎的女性意识。
佛教的思想渗透藏民生活每一个空隙。
藏民的每一处思想和每一个行动,都受佛教的引导和启悟,佛教的一切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
作为一名藏区的女性,不仅要和处于权力优势的男性相抗衡,还敢于质疑传统宗教信仰的代表,最权威和无上的引导者——上师,这是苏醒时卓嘎面对困境作出的大胆抗争。
卓玛与火:难以熄灭的执念卓玛出场是穿着尼姑衣服的,是一种淡然的心态。
但包裹在其内心,却是一股“火”。
“火”是卓玛对爱情的意象,她的感情就像火一样热烈、真挚。
卓玛在经历一段伤心的情感经历后断然出家,多年后却意外的遇到了之前的爱人,爱人送了一本写有两人曾经过往的书,点燃了她心中的火,火光涌动就像起伏的情感与生命。
卓玛毫不犹疑的探手伸进火中取书,就像义无反顾的飞蛾扑火,从那股一闪而过的对待爱情的欲望,可以窥见卓玛强烈压抑但渴望的内心。
金巴与公羊:触底反思电影多次明说暗道金巴正如种羊一样,公羊是金巴的象征。
种羊的使命是让众多母羊繁殖后代,种羊强大的生殖力量也正如金巴旺盛的性欲相一致。
在面对众多母羊时,种羊享有主动选择权。
生殖力量也会改变整个羊群的品种。
作为男性权力强势地位,金巴是一直处于选择和主导状态的。
主动选择性交,操控和引导家庭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如传统信仰下对宗教坚定的信仰和男性天然的权力地位,金巴十分孝顺,阳刚,为家庭着想,默认女人的牺牲地位,甚至在女人反抗质疑他时动手打人。
展示生殖力、干体力活、打架、甚至怒打妻子等行为都是男性力量的一种展现。
而打人是矛盾的顶峰,此后金巴似乎开始有所反思。
妻子离家、母羊卖掉后,金巴在文成公主的雕像下若有所思。
文成公主是女性为家国牺牲的典型意象,金巴似乎受到妻子心中的那种自我意识觉醒的冲击,这在电影结尾成为一种未知的悬念。
孩子与痣:宗教的枷锁江洋是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中间的角色。
电影中的两段梦境都和江洋有关。
江洋从出生背上带痣,从小就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
对于这种身份,江洋是有一定压力的。
电影中有一段梦境,两个弟弟光着身子取下江洋身上的痣在沙漠中快乐的奔跑,影像色调呈暖调,江洋仿佛卸下了重担,与弟弟们轻松愉悦的嬉闹。
爷爷去世后,影像呈现河中江洋追寻爷爷的倒影,爷爷与江洋感情深厚。
但同时爷爷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固守者,认为摩托没有马好,认为试管婴儿等现代科技发明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去世的老人也象征着传统的式微。
如此,江洋在对卸掉宗教枷锁的企盼和对传统的不舍留恋中徘徊,正如每个在时代巨变的夹击下迷惘的孩子一样。
在时代的变化下,每个人正如洪流中的蝼蚁一样,面对自我选择和对他人的选择。
影片中两位女性,都受现实和宗教的苦恼。
姐姐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但却面对生活和宗教的两难;卓玛本来心中对爱情充满向往,但被渐渐熄灭;金巴逐渐丢弃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开始反思;孩子江洋在迷惘和徘徊中前进。
正如电影名字“气球”一样,片头白气球与片尾红气球相互呼应,印证了“轮回”主题。
象征生命的气球看起来那么红,那么大,那么重,后来它慢慢飞走了,在众多的目光下越飞越高,越来越轻盈,目光所追寻的,是红气球看似自由却不知所归的命运。
参考文献: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影视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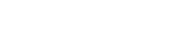























































首先色调就让人受不了,你家草原这个色儿啊……堆砌元素,而不是在认真讲故事。20210218
其实原以为梦到母羊怀孕会有更大胆的指向,但现在的呈现已经非常精彩了,探讨女性在父权社会与宗教信仰的双重压力下面对的困境,画面实在精致,副线留白处理也很喜欢
【D】甚至没有「撞羊」好,更为清晰的影像反倒没能足够贴近人物,印象中很难看到从故事的第一秒就开始点题的电影,符号化是把双刃剑。
太无聊了,是不是藏族题材的评分都会偏高啊
导演作品里最喜欢这一部!印象最深的是几段如梦如幻的幻想性场景,配合着音乐,给人迷离舒缓之感。让我联想到塔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潜行者》。达杰与种羊都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卓嘎像那只不生崽准备被卖掉的母羊;爷爷对应着马,它们已经慢慢远离了藏民的生活……更不用说白气球与红气球了。这种对应让影片的表达很清晰,容易引发思索。不足之处就是过于直接、明确,少了点蕴藉的韵味。之前的《塔洛》基本是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本片中两者不再截然对立,但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当代生活,需要对传统进行改造、祛魅,才能完成现代化。这自然就会打破传统(特别是宗教)的精神内核。丰盈的生活状态,鲜活的人物,又蕴含着文化之殇与传统之痛,手持摄影的影像风格也被近乎完美地呈现。其作品的完整性、丰富性,远超一般国内艺术电影。
相比前作《撞死了一只羊》显得更加通俗,但也失去了不少灵气。这个故事过于依赖剧本的闭合度,对女性权益的探讨也是在节奏之内,像是计算后的平稳棋局,并没有奇峰险招的快感。当然这些都是苛求,它的出现本身已经是一种意义,使得所谓藏地新浪潮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去奇观化”。
完全在激怒女性观众的角度,将女性物化过度。刚看完平遥电影节首映。感到非常失望。终于学会了固定长镜头,什么信仰与现实的挣扎。什么狗屁轮回,手持晃动镜头,放飞的避孕套就是男导演的一场春梦。很多男性观众起立鼓掌,感到有悲凉又恶心。如果影片本身的存在是为了激怒女性,导演的确做到了。如果要带着批判,或者平常心,应该是希望有更多女性站出来。抵制这种导演吧。还不如一场屎尿屁。平遥第一场,垮掉。
尼姑的线讲一点藏一点;宗教文化冲突不可说;育儿问题待解决;隐喻符号不便说明白;女性部分大多时间语焉不详;气球也是模模糊糊,说是主题撑不起来,说是线索一直没出现,说是符号不搭噶……说到底还是塞的太多了,也不讲究主从关系,除了开头结尾,根本看不出导演想干嘛。更可怕的是,可以看出强烈的设计感,大到每场戏的走向,小到单个镜头寻求的呈现效果,你看着他花时间一步一步搭建,最后他说搭完了,你发现这个东西啥也不是。2.5
前半段刻意的诙谐,后半段几锤子就粗暴的把事情结束,这不是一个好的叙事者。所用摄影机在弱光下成像太差,整体摄影也显得做作。当你获得一个好idea时,要珍惜,多打磨,尽可能去呈现它,而不是在作品里凸显导演的存在感。
看完一个多小时了也实在想不到有啥好说的,夸一下胶片成色吧,挺漂亮的。
我真的非常不喜欢《气球》,是那种非常僵化的电影。每一幕,每一个设计,人物每一个动作,都是僵化的,完全无法流动,甚至试图在控制观众的情绪,导致这部电影非常之空洞。那些隐喻也都因为意图过于明显,无法让人深入思考,而是转为明喻,让人出戏。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的存在,也没有氛围的存在,只留下一堆无聊的符号。也许只有最后一个段落,才短暂地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电影的时空。
灵魂与现实的冲突!当代文明与信仰的冲突!有了一定佛教基础后会更理解电影要表达的东西!本届平遥影展个人观影最佳
手持镜头请永远退出我的影单
这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去支持的电影。但相比导演之前的作品,这部太过于依赖象征和隐喻了。以前看万玛导演的电影,觉得真正是一个藏族导演在讲自己的故事,但现在感觉他在自我民族化的过程里,导演的视角却变得他者化了。并不是他者化的眼光就完全不好,但在方便于他者理解的同时,却没有达成真正的交流和追问,反而让苦痛被简化了。非常喜欢生育对女性束缚的描述。即使在弱者中,她还是弱者中的弱者。我体会到了理性难以解释的、能够共情到的苦痛。也非常喜欢电影所表现的挣扎,却并没有非要拿出控诉的姿态。想到了那句:如果弱者用强者的方式反抗,不过成为了强者的共谋而已。
走出《撞死了一只羊》的尴尬模仿,万玛才旦重新回归自我并再创新高,前半段你又能看到《塔洛》身上诙谐的影子,后半段的拔高也流畅而自然。女主的设置非常巧妙,从依附到犹豫,从觉醒到行动,她走出了家门,走进了自己。更可贵的是,万玛才旦还隐藏了一条线,让人更觉得了不起:这个觉醒后努力摆脱他人操弄自己命运的女主,却时时刻刻想要左右妹妹的命运,这种讽刺也是导演之前没有的高度,生涯最佳无疑!#PYIFF2019#
挺失望的,故事没讲好。最有力的冲突应该是“能不能怀孕”,而不是怀孕后“该不该生”。前者的是家庭负担(罚钱和多口人吃饭)和人的自然本性(性欲)之间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社会特色(计划生育)。一旦转置到后者,变成了家庭负担与转世投胎之间的矛盾。而尼姑和爷爷的角色明显是后加的,仅仅为了突出宗教(而非信仰)的束缚。最后宗教变成了刻意呈现的景观。法哈蒂电影里的两难冲突之所以让人共情和感动,是因为信仰加赋在人身上的是邪恶诱惑下向善的意志,而《气球》里的信仰更多是一种教条,仅仅为了不带来灾祸。这有本质差别。
意料之中,未有惊喜。细节安排过于刻意,不该是万玛才旦的水平。如果藏语电影继续成为银幕猎奇角色出现,那离它彻底失去国内普通观众也将不远。一个个别再讨排片了,上海的排片已经对得起这部片子,尤其在有《除暴》这类大片的情况下。
公公剥削儿媳,丈夫剥削妻子,儿子剥削母亲,而后他们心满意足地离开,留下一只耗尽生育力的待宰的羊。
《气球》里有很多对于女性的关怀,导演将两类藏族女人放在了姐妹两人身上,殊途但是同归。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在藏区依然到处都是关于优生优育的字报,让我感觉有点抽离现实,在电影里加上这些应该是想要凸显出女性的困境。关于黑夜的摄影让我感受到了《小亚细亚往事》中的那种深邃的包裹感,火光和稀薄的空气让这种黑更轻盈。长子在爷爷去世那一晚做的梦拍得特别棒,光影和调度的美感与死亡和轮回的表意结合得特别好。《气球》并没有像我们看的大多数关于藏区的电影那样刻意加深神秘感,这种去神秘化的展现才是我们缺少的,更接近现实的电影。
在全是样板戏的年代,这样的作品好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