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我的车》剧情介绍
中年舞台剧演员家福撞破了身为编剧的妻子音的一次出轨,然而,他安静地关门悄然离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一如往常与妻子融洽且恩爱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妻子去世,家福都没能对妻子坦诚,这变成他的心结。随后,尚未从悲伤中走出来的家福开始准备《万尼亚舅舅》的话剧演出,准备把自己沉 浸在工作里。不同国籍的演员们在家福的指导下,以各自的母语反复研读剧本,还加入了手语的表达,感人深切。剧场为家福雇佣了一位女性司机渡利,每天接送家福前往排练场地。渡利性格沉默,但车技高超。在相处中,家福开始逐渐和渡利交流自己的内心世界,渡利心中也有一段不愿面对的秘密往事,两人的创伤在最后的返乡之旅中坦然拨开,彼此的相拥与宽慰使尘封的往事得以重新审视,一丝慰藉与释怀在心中升腾。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86-不存在的战区-Part.2沙海怪兽民间怪谈:水猴子王者无敌苏乞儿南方车站的聚会情刺出生的秘密8位机圣诞长安秘闻录煎饼侠韩玉娘布娃娃死亡片场奥利最开心的一天我的媳夫尖刀战士全能侦探社第二季双城之战:天堑官方幕后纪录片爷爷的暑假乔布斯:最后一件事情死亡空间:坍塌敌人之路五十活死人旅行社的故事猴子刑警与检察官,有时是法官。火红的青春哑孩儿牙狼:月虹的旅人传闻中的七公主
《驾驶我的车》长篇影评
1 ) Drive My Car,你能開好自己的車嗎?
Drive My Car,你能開好自己的車嗎?
廖偉棠金球獎出爐,濱口龍介的Drive My Car(台譯:《在車上》)果然奪得最佳外語片,同時它也在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獎成為大贏家,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編劇。
去年它的成績也昭然,康城影展最佳劇本等三個獎,亞太電影大獎最佳影片最佳編劇,以及許多獨立影展的獎項。
看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幾乎是囊中之物了。
Drive My Car的編劇尤其見功力,也許你會覺得,有村上春樹的原著在,改編劇本有什麼難的?
但村上原著一來是短篇,二來他一貫雲淡風輕地把戲劇性藏得很深,這都是電影長篇不可能遵從的。
於是濱口龍介(也是編劇之一)必須在原文本上開創更多重世界,同時又不失去原文本的主旨與韻味。
原著裡的故事並不複雜:一個失去妻子的男人,和妻子的舊情人相遇,並向自己的女司機傾訴。
但這三者之間的「緣分」,足以讓濱口龍介窺見人世間無所不在的傷痕,然後他嘗試紀錄和修補。
濱口首先找到的,是和Drive My Car處於同一本村上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裡的短篇<木野>,裡面木野目睹妻子出軌的情景——還有經過漫長的逃避之後才被承認的傷:「對,我受傷了,而且非常深。
木野對自己這樣說。
然後流淚。
在那黑暗的安靜房間裡。
在那之間,雨仍不間斷地,冷冷地濡濕著世界。
」。
這兩點都嫁接到Drive My Car裡的家福身上,精確到妻子出軌時的體位。
接著,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在原著裡只是一筆帶過的兩段台詞的引述,作為家福演員生涯的佐證或者男人生涯的反諷,但被濱口龍介大做文章,衍生成始終伴隨整個故事的「平行文本」。
《凡尼亞舅舅》內裡的種種矛盾與昇華,直接對應了家福經歷的矛盾與昇華,兩者拉出飽滿的張力,在聾啞演員用手語和靜默演出的時候達到高潮。
而這部戲要在廣島國際戲劇節排練和演出,順理成章地讓廣島:這個飽含「傷痛與治癒」象徵的地點,成為小說裡缺少的舞台,讓幾個角色在此相遇,重啟各自的生命,實在精妙。
然後,濱口從村上春樹另一篇短篇<雪哈拉莎德>挪用來第三層文本:家福妻子「音」在每次高潮時向他和情人講述的劇本/夢境,包括「我的前世是八目鰻」這神來之筆。
濱口似乎覺得<木野>裡經歷魔幻的男人的自我覺悟不夠有說服力,因此補充了妻子角度的這一伏線。
最後濱口還加上了女主角、司機渡里美咲的少年往事,和音的情人高槻的後續故事,前者主要是她與母親的痛苦,甚至還有母親的分裂人格;後者的突發犯罪與覺悟,為他開口規勸家福補充了心理動因。
這兩者的展開充滿現代戲劇的套路,和作為近代戲劇的《凡尼亞舅舅》恰成對比。
這時候你才發現,不但渡里是家福的司機,高槻、音、甚至凡尼亞舅舅的外甥女索尼婭,都是家福的「司機」,因為家福並不懂如何「駕駛」自己的心。
「『不過無論是彼此應該多麼了解的對象、多麼相愛的對象,要完全窺見別人的內心,終究是不可能的事。
去追求這種事,唯有自己難過而已。
不過那如果是自己的內心的話,只要努力,應該就能確實窺見努力多少的份。
因此,結果我們不能不做的,大概是和自己的心巧妙地誠實相處吧。
如果希望眞正看清別人,只能深深地筆直凝視自己的內心。
我這樣想。
』這些話似乎是從高槻這個人內心的某個很深的特別場所,浮上來的。
」這是村上春樹原著裡的話,幾乎一字不差地在電影裡讓高槻這個貌似輕浮的小白臉,對貌似成熟穩重的家福說出來,未免有點諷刺。
然後家福恍然大悟,須知這也是音想要對他說的——回到故事的開始,家福面對不了幼女的夭折,麻木地活著,然後他面對不了妻子的出軌,繼續假裝沒事發生,最後間接導致了悲劇,其間的警號,恰是音所講的「闖空門」故事。
夢境一般的故事裡,音是一個偷進暗戀對象的家的中學女生,她一再地留下「物證」希望被發現,但即使到最後她留下的是一具被她殺死的屍體,對方還是無動於衷;她只好對著新增的監控攝像頭大喊「是我殺的!
是我殺的!
是我殺的!
」故事的後半部分,是高槻轉述的,因為作為丈夫的家福拒絕了音最後的溝通。
諷刺的是,高槻也通過這樣向家福坦白了自己的殺人。
而家福卻永遠沒有機會向音坦白。
高槻被捕,渡利接力來救渡家福和自己,她的姓氏和職業(司機)已經暗示了她的擺渡人身份。
面對內心深淵和接受女性的救贖,這是村上春樹一以貫之的主題,從《發條鳥年代記》到《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等小說莫不如是,濱口龍介忠實地加深了它的細節和輪廓而已。
渡利首先被救渡,來自於家福善意安排她觀看了《凡尼亞舅舅》的彩排,又執意讓她和韓國演員夫婦成為朋友,啞演員飾演的索尼婭角色更啟示了渡利。
既然家福/凡尼亞舅舅無力開好這趟命運快車,那就由渡利/索尼婭我來吧,我幾乎能聽到她的內心獨白。
所以渡利與家福是互相救贖的,正是成為他人的拯救者,我們自己才能擺脫受害人與施害人這痛苦的雙重身份。
家福在最後痛苦抉擇中(他要不要再度飾演凡尼亞舅舅)時本能地讓渡利帶他去她的北海道家鄉,其實就是潛意識承擔了救渡者的職責。
音去世之後依然參與著家福的心靈之旅,電影的最大創舉就是讓她生前替家福讀劇的錄音《凡尼亞舅舅》一再在車上重播,啟示了對契訶夫一竅不通的渡利,也啟示了自以為很懂契訶夫的家福,他終於發現自己一直念叨著的「我一直在扮演自己不是的人」不只是句台詞,而是警鐘。
他和音未能在現世演下去的戲,在車子這個最狹小的舞台上繼續對答,直至覺悟。
因此,最終的救贖者,是已死的音,是契訶夫。
電影的最後鏡頭,家福不再出現,時間線和我們的現實相交,他的車被渡利開到了韓國,左舵的SAAB車離開右舵的日本終於走上了合拍的路,渡利還載上了一條跟她在韓國人夫婦家中所見相似的犬。
接下來的故事,該是戴上了口罩的渡利、和我們如何面對新世界的考驗了。
(原刊2月)
2 ) 所谓文艺
关于人性题材的影视剧永远会被视为高尚的文艺作品。
何况本剧还有村上春树的加持,用契诃夫装饰。
在虚伪的时代,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去附庸风雅。
每个人都不想被视作俗物,因此面对所谓的文艺作品时,都是不假思索地迅速站队,不管看懂了没有,不管内容是否有价值,不管演绎的是否有美感。
家福发现妻子出轨后,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依然同妻子维系旧有的温情。
妻子暴病而死后,家福去广岛排演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
同他妻有染的青年也在应募的演员中。
广岛的举办方为家福派了一名女司机。
情感故事就是从家福同那个青年,和那个司机之间展开。
司机驾车,家福和青年坐在后排谈话,谈的主题仍然是家福死去的妻。
最后似乎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家福的不坦诚才造成了妻子的死。
那个青年也红润着眼眶,一个偷奸的人,竟然堂而皇之地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随后的日子里,司机也讲述了她悲惨的过往。
她的母亲死于一次塌方事故。
当时,她明知她的母亲仍在废墟中挣扎,却没有向施救人员告知。
司机自称是她害死了母亲,有一点点忏悔,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独白。
这种冰冷的独白仍得到家福的温暖一拥。
影片最后,司机开着家福的车,载着一只秋田犬,从超市归来。
衣服不似先前灰暗,脸上也洋溢起了笑容。
我不太清楚,导演和编剧到底是想传递一些什么东西,只能凭着感觉来讲,他们似乎都背负了太多的情感压抑,像一个罪犯在寻找越狱的出口。
最后,不惜用一种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欺欺人的方式重新开始了苟活。
影片中有一段很令人深思的话:“如果您真的想观察一个人,那么您唯一的选择就是正视并深入地看待自己。
”我觉得影片中的角色,甚至是导演和编剧都没有用实际行动来正视并深入地看待自己。
他们试图去在深爱和不忠,偷奸和单纯,阴鸷和良善中间寻求艺术的桥梁,却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东西搅在了一起,然而,他们又对自己的匠心独具不足信心,又用伟大的契诃夫来进行了包装。
影片给评一颗星,完全是献给那辆经典的萨博900。
3 ) 像漣漪擴散過後的池面:用眼淚作為信物
孤獨是甚麼呢,車窗外的黃燈滑過司機和乘客的臉,在寂靜和老舊的車廂裏,播放着熟悉的舞台劇台詞。
孤獨是心事的圍欄,有人想闖進去,有人防衛着。
大前提是有愛,沒有愛就沒有孤獨。
然而愛是甚麼呢,不是單是有喜歡的成份,還有佔有、尊嚴、欲望和自卑。
害怕受傷,偏偏受傷;有些創傷,無法治療,不如交給靜默,讓時間在疤痕上流淌,即使那將會是川流不息的不死之河。
沉默、擱置才可以讓人生活下去。
導演濱口龍介大膽地改動村上春樹的短篇原著《Drive my car》,並加入了《雪哈拉莎德》的八目鰻情節,用四大角色家福悠介(西島秀俊飾)、渡里美咲(三浦透子)、高槻耕史(岡田將生飾)、家福音(霧島麗香飾)交織創傷,構建孤獨。
以戲中戲(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談話、說故事(家福音的劇本)之方法,把一部以「沉默」和「流白」為關鍵詞的短篇小說,改篇成一趟長達三小時療傷旅程的電影。
電影中最大的改動來自家福音的情人高槻耕史。
他由一名英俊簡單的父親,變成一位玩世不恭、宛如空殼的年輕演員。
在小說中家福為了揭開妻子偷情的秘密,不禁主動親近妻子最後一個情人高槻,並與高槻成為朋友。
在聊天間,發現高槻的創傷並不比家福,高槻簡單英俊迷人,卻是一名年輕父親。
在揭開真相的過程間,家福發現高槻所知的其實比自己更小。
然而簡單天真的高槻也能給音一點家福不能給她的安慰——這是自己做不到的。
電影中,只想像平凡人得到幸福和輕易感恩的高槻被改篇成玩世不恭、不知自己做甚麼的年輕人,強調心中之空,他根本不能演好凡尼亞這角色。
但同樣地,這種「空」卻給家福音難以名狀的悲苦,高槻知道音所編寫的故事的結局。
高槻比他知道更多。
電影與原著一樣,最終家福始終無法解開妻子不忠的秘密,即使司機美咲安慰他,說音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平凡人,但這種安慰其實也像八目鰻般吞食家福的肉。
這種痛苦的結,無論用甚麼方法都不能解開。
高槻心靈之的「薄」與家福心事之「厚」形成鮮明對照,但是對照看似是兩極,其實都是一樣的,無人能解開家福音的心,兩人都無法為家福音的愛和性作合理、真實的詮釋。
二個男人有不同程度的愛,但終點竟彷彿是相同的:霧中花,當然在霧中枯。
作為演員的家福用演員的身分、熟稔的對白作為創傷的防空洞。
只要唸起台詞,他就可以忘記自己。
在電影中他和妻子一邊做愛一邊編故事,也是一種逃逸,掩飾死去女兒後,婚姻的紅燈。
文字成為了麻醉藥,但僅是轉移視線,「真實」永遠不可以逃離現場。
眾人的人生塗上黑色的基調,每個人的創傷構築了絕對的孤獨。
村上式孤獨,無論何人用甚麼方法都不能闖進的孤島,進攻防備、性與愛,通通無效,城市裏的人,只可以用謊言和性編製一種藥,暫時忘記,僅此而已。
美咲和家福可以對住冰雪破屋,大喊我要活下去,但與此同時,破屋不會消失。
或許美咲說的精神分裂的母親也可以是一個故事,是用作治療家福創傷的藥:用別人的創傷治療自己的創傷,不只是你一人不幸,別人的創傷故事,不正是喵準孤獨的槍?
《凡尼亞舅舅》的對白穿插,導演把契訶夫的世界重重地帶進廣島。
契訶夫洞察世情,是俄國最頂尖的短篇小說家,令本應很輕的小說,變得非常重。
最後索尼亞說:「有什麼辦法呢,總得活下去!
凡尼亞舅舅,我們要活下去,我們要度過一連串漫長的夜晚;我們要耐心地承受命運給予我們的考驗;無論是現在還是在老了以後,我們都要不知疲倦地為他人工作;而當我們的日子到了盡頭,我們便平靜地死去,我們會在另一個世界說,我們悲傷過,我們哭泣過,我們曾經很痛苦,這樣,上帝便會憐憫我們。
舅舅,親愛的舅舅,我們將會看到光明而美麗的生活,我們會很高興,我們會懷著柔情與微笑回顧今天的不幸,我們要休息……我們要休息!
我們將會聽到天使的聲音,我們將會看到鑲嵌著寶石的天空,我們會看到,所有這些人間的罪惡,所有我們的痛苦,都會淹沒在充滿全世界的慈愛之中,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安寧、溫柔,變得像輕吻一樣的甜蜜。
」熟知契訶夫的讀者都明白,契訶夫終身探索的是死亡、荒謬和孤獨。
電影中這段用作麻醉自己的對白改用手語演譯,刻意放大誇張的肢體語言和表情。
既是真心的安慰,也是無力的安慰。
除了這些空洞的話外,我們其實還可以抱持甚麼呢?
有生之年,我們根本無法戰勝悲傷,只有在彼岸才可以休息。
死後才可以解開人生的悲痛,光明的對白僅是糖衣,勇敢活下去,消除臉上的疤痕以後,微笑以對,不代表創傷就消失掉。
只有活到盡頭才可以休息,你必須走可去,咬緊牙關,不然悲痛不足以叫人憐憫。
這段「天使之音」說盡人生磨難。
村上式寂寞一旦遇上契訶夫之洞見,沉重如無盡黑夜。
唯一是,當美咲駕着別人的車、帶着別人的狗、走進別人的國家,當所有人的創傷都堆疊起來的時候,終於可以啓動宛如機械操作的微笑了。
原來只是一個洋葱,花光力氣和壓力剖開了傷,以為它的中心總有一個真相、解釋、出口,怎料甚麼都沒有。
人生,僅僅就是那剖開的動作,眼淚是信物,漣漪擴張後的平靜,是你僅可堅守的表情。
作者:呂永佳(香港詩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員)個人視頻https://youtu.be/NBJ4IBRwF_k
4 ) 《驾驶我的车》:自欺的文本、祛魅的文本
(原文发布于公众号“半斤八两抡电影”,作者展世邦)《驾驶我的车》,是滨口龙介带给观众的文本游戏。
经由电影内外、舞台上下、角色关系、人物立场组成的交错小径,我们甘愿流连在作者构筑的精巧的叙事迷宫之中,沉溺进电影——也只有电影——能够带来的迷人错觉。
电影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同名短篇小说《DRIVE MY CAR》,并且加入了另一篇小说中角色所叙述的部分故事;电影之中,主角家福在舞台上主演过《等待戈多》和《万尼亚舅舅》两部经典戏剧;舞台之外,家福沉浸在《万尼亚舅舅》的剧本里,会在开车时播放录制了对白的录音带;亲密关系之中,家福是音所创作的“故事”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亲密关系之外,曾经被家福中断了的音所创作的“故事”竟被另一个男人续完;筹备舞台剧过程中,家福的临时司机渡利成为这部戏剧排演时的观众,并和家福共同面对各自人生中的幽暗过往,最终重新完成了《万尼亚舅舅》的公演。
这部电影涉及了如此多的文本,文本中的角色处境与电影故事里的角色处境互为对照,令人眼花缭乱。
同一文本在故事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
文本被拆解后,又重新缝合进了新的叙事里,构成更为迷人的故事结构。
在电影文本中,有一条刺眼的缝隙,让人难以自抑地窥探——作为开场标识的片头字幕为什么要在影片开始40分钟后才出现?
以字幕“两年后”作为时间上的分野,家福似乎只是打了个盹儿,从方向盘上醒来,他开着他的红色SAAB 900T 重新启程。
墨菲斯——吗啡家福在车里睡着之前的剪辑顺序依次为:舞台公演多语种版的《万尼亚舅舅》、家福在后台压抑地抽泣、家福驾驶着他的车行驶在夜路上、听着音(亡妻)为他录制的《万尼亚舅舅》的对白磁带、出现字幕“两年后”、未知视点——音独自在桌前录制《万尼亚舅舅》对白时的背影、音不带情感地诵读对白的嘴型特写、黑场。
再次渐显的画面,是家福趴在方向盘上醒来,他将驾驶着他的车长途奔波到另一个地方筹备他的舞台剧——《万尼亚舅舅》。
从舞台到舞台,家福始终没走出《万尼亚舅舅》,他把自己封印进一百年前的经典戏剧文本。
在音的声音里,家福主动沉沦,亡妻的声音附着在亡者的文本中,令他不能自拔。
广岛戏剧祭上即将公演的《万尼亚舅舅》,家福的身份是被邀请来的“导演”,握有选择演员、分配角色、诠释文本、调度场面等所有权力,他是他自己的Morpheus(墨菲斯),与死魂灵们共舞了两年多,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对这一文本的话语权,他心甘情愿甚至是自觉地继续活在这一戏剧文本的morphine(吗啡)中,作为一个活死人。
强行违背高槻的意愿、专断地安排他出演万尼亚,是家福来到广岛之后做出的第一个叙事意义上的行为。
高槻报名的角色是《万尼亚舅舅》里的医生,阿斯特罗夫,一个引诱了教授夫人并且夺走了她的心的男人;高槻被家福强行安排的角色是万尼亚,恋慕着教授续弦的年轻妻子、嫉恨着教授——他死去妹妹的丈夫、甘愿自我牺牲并被教授剥削着生命和金钱。
这样一个自我抑制的、扭曲的受害者,之前一直由家福自己饰演。
透过广岛的剧院负责人的态度可知,家福先生是万尼亚这一角色的唯一理想演员、无可取代。
在高槻出事后,这位剧院负责人几乎是胁迫着家福“顶替”出演万尼亚。
家福,一个自我放逐在《万尼亚舅舅》文本里的活死人,借导演的权力向高槻复仇,他曾目击自己的妻子——音——《万尼亚舅舅》对白的声音磁带的录制者,在自己的家里与高槻偷情。
在那之后,万尼亚这一角色就成了一个诅咒,家福把自己缝进了这一游走在舞台上的亡魂躯体之中。
“互文”带给创作者和观众的快感,始于对应关系:面试的表演场景,刚好是阿斯特罗夫情难自抑地引诱了叶列娜(教授年轻的妻子),而沉湎于情欲中的二人刚好被曾经的万尼亚——家福再次目击,高槻——阿斯特罗夫、音——叶列娜、家福——万尼亚,构成残酷的对仗关系。
家福失态地摔了椅子、当即叫停高槻的吻戏。
“互文”带来的快感不止于此,真正产生对话并且超越元文本意义的,是错置或者重置对仗关系。
家福下意识地行使了他作为梦之神墨菲斯的神力,他要摆布并且亲眼看到高槻(万尼亚)目击到他所爱的叶列娜、他的青春和他的理想所系的女神把脸埋进另一个男人(阿斯特罗夫)的怀里。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冠冕堂皇地摆布情敌更能享受复仇快感?
《万尼亚舅舅》里最有魅力的角色是阿斯特罗夫,他是个真正“活着”的人,他强壮、充满动力、为生命奔忙,治病救人的同时也会因治死了人沮丧酗酒,拼命挽救被砍伐的原始林地、以科学的精神和方式绘制着森林消亡的地图……索尼娅和叶列娜都爱他,他的声音、他的气息和他的步伐,是她们——本能拥抱生命却眼看着自己陷落进脚下生活的年轻女性对生命力——的追求。
在契诃夫的剧本里,阿斯特罗夫只是过客,他的步伐不能停驻在生活里,他注定要追逐生命本身。
曾经身为医生的契诃夫,以剧作家的悲悯,留给世人的是索尼娅和万尼亚。
被封印的聆听者、被复活的叙事者家福第一次听磁带,是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为了筹备舞台剧并能够始终沉浸在文本中,他请音为他录制了《万尼亚舅舅》的对白。
听磁带的过程是单向对话的过程,音在诵读角色对白的时候,会专门为万尼亚的台词留下间隙,家福在开车时可以在这些间隙中诵出万尼亚的台词,严丝合缝。
家福与音之间的默契超越了夫妻关系,也不同于亲密朋友间的关系,二人在磁带里融为一体。
家福引以为傲地在其后的“叙事”里把音和他绑成一个主体,他在和高槻的对话里饱含着优越感地铺设潜台词:他和音之间的关系早超越了夫妻,并不是高槻这样的人能插得进来的。
这是家福由衷的骄傲,同时也是他抵抗妻子出轨真相的护心镜。
此外,家福和音曾经共同蒙受丧女的悲恸,并永远共同被包裹在失去未来生命的阴霾里。
其实,这一苦难对家福的分量,远非悲恸,而是另一意义的“二人一体”。
就在家福目睹了音的出轨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了女儿的忌辰,这一举动似乎在说明着关系维持下去的理由。
音去世两年后,家福和高槻在SAAB 900T 后座上的对话,家福平淡地讲述了他与音共同熬过炼狱的事实,并且暗示了这一羁绊远高于亲密关系包含的情欲和爱欲。
就像《万尼亚舅舅》的对白录音带,爱女的早夭,固置了家福与音之间的联结。
这种基于“死亡”的联结,更恰当的概括应是:束缚。
在音猝死当天的早晨,她曾经嘱咐过家福,晚上有事要认真谈一谈。
家福回到家,发现了妻子的遗体,他“侥幸”躲过了一次直面惨烈真相的契机——如果不是蛛网膜出血,音很可能对家福坦陈她的出轨。
也正因为这次意外,家福才得以封印真相,并且在意识里强行避开了妻子和他“并非一体”的事实,他以录音带里的声音和万尼亚的文本麻醉着自己,带着对“完美”亡妻的哀悼、带着对自己的可怜,继续活下去。
视觉上,这一“自欺”的时刻,呈现为家福看到的镜像。
当时他因为航班问题推迟了出国,回家进门,家福经由镜子看到音正在和高槻共同陶醉着肉欲。
那一刻的家福的视点里,妻子和她的情人始终在镜子里,直到家福悄声离去她们都不知情。
其间,出现过一个反打的镜头,是镜中错愕的家福,那一视点既非某个角色的主观视点、也不是第三人称视点。
角度和位置,更接近于音的视点看到镜中的家福,但是,在客观事实上,音全程都紧闭双眼享受着肉体之欢,她并未察觉家福的存在。
这一“吊诡”的“反打”,缝合的对象究竟是观众还是家福?
家福被置于镜子里,他成了自己的“他者”,自此他把发现了真相的自己封印进了镜像之中、也同时封印了出轨的妻子的镜像。
除了《DRIVE MY CAR》,在村上春树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里有另一篇故事——《雪哈拉沙德》(译名参考自赖明珠译本,即另一译本的《山鲁佐德》)也被滨口龙介拿来植入到“音”的角色里。
电影《驾驶我的车》,开场的情境就是音以一贯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调讲述着一个故事:暗恋着高中同学的女生经常翘课潜入到对方的家里,呆上一阵子,留下不易被发觉的某种“痕迹”再离开。
这一故事的开头,是音在与家福做爱之后讲给他听的。
聆听着故事的家福就把故事的细节一一记下来,事后再复述给音,音再继续整理成剧本。
凭借这些文本,音参加剧本比赛成为了编剧,并继续创作。
家福目击了音的出轨之后,两人上床的时候,音随着身体的高潮也把这个故事推到了高潮段落,然而次日早晨她问家福故事的细节时,却被告之“没记住”。
极富意味的镜头是,家福用前臂遮住自己的双眼与妻子做爱,他拒绝了和音的真正联结。
家福以这样的方式,打破了他和音之间的默契,报复了出轨的音。
次日晚上,音猝死,这一故事也“死”在家福的记忆中。
两年后,家福和高槻在车上对话,故事有了另一个方向的突转。
原本,家福是想故意压高槻一头,想告诉他:家福和音之间除了共同走过炼狱之外,还有一重超越了性欲的亲密关系,那就是:作为叙事者的音通过肉体之欢即兴讲述故事,作为聆听者的家福记录故事——二人一体,共同创作了音的剧本,音以此成为出色的剧作家。
这毫无疑问又是家福的自欺之梦。
家福没想到的是,高槻作为另一个聆听者,续上了音创作的故事,并且使之完整成篇。
毫无疑问,这一故事也是村上春树大多数故事指向的: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曾经发生过至暗的反人类的行为,但那个地方的人们从未真正反思、至今仍在和平繁荣的表象下若无其事地生活,黑暗的历史成为禁语,那黑洞一般的真相被每个人共谋着掩盖。
作为如此震撼人心的故事的叙述者,音已经不在人世,是高槻重新讲述并“复活”了她的故事,让她的作品生命得以延续——毕竟车上还有渡利也听到了——只要有倾听者,故事就能活下去。
司机渡利在其后对家福说的话,刚好印证了:经由高槻的讲述,渡利倾听并且开始思考这个故事,进而对音、高槻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被他者听到、甚至启发了他者,这也正是音的作品生命延续的意义。
至此,家福的封印——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杀死”音的行为——也就被破除了。
鉴于音只在做爱时创作故事,高槻之所以能复述完整,当然是以肉体为媒介,记录并补完了她的作品。
音受到肉体——生命刺激而生发的创作,得以由肉体——生命的结合而存续。
高槻的存在,祛魅了家福自怜的说法,并且以最原始的方式——性交中的身体状态记录下的故事——还原出了一个更为完整但是并不完美的音。
在家福的车里,音的故事终于战胜了家福控制下的音的声音,音也被“复活”成为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
渡利后来温柔质问家福:“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一个既爱着你也和其他男人上床的音小姐的存在呢?
”这句话刺破了家福的梦之铠甲,让他哭了出来,并且承认“自己被深深地伤害了”这一事实。
被凝视的舞台、被侵入的后台《万尼亚舅舅》这一经典文本,在滨口龙介的电影文本里被激发出更出人意料的力量,远远超越了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文本所能承载的限度。
滨口龙介充分调动了契诃夫原作的各个层次,解构了其中的空间、语言、时代性,甚至打破了戏剧的媒介——舞台本身的属性,并将之重构为某种对话或理解的可能性,试探着敲开当下人的——由于主体与他者不可调和的对立所造成的——孤独而自恋的茧房。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家福把自己困在他的SAAB 900T 里,困在磁带播放出的音的声音文本里。
在第一个“他者”被塞进他的空间之前,他都以视而不见的姿态照例播放着音留下的声音文本。
在初到广岛的几日里,临时司机渡利对家福而言是如同空气一般的存在。
渡利出于职业操守,以及对家福爱车态度的尊重,从不擅自进入那辆红色的古董车。
家福对《万尼亚舅舅》的“筹备”,可以说是每天都在进行,他的车就是排练场。
两年间,他每日都在和那些被妻子赋予声音的魂灵们对话。
在选定演员之后,家福顺理成章地继续以文本为指归,在他的命令下,所有的演员都要不停地围读经典文本,去除带感情色彩和表演痕迹——正如音在录音带里的状态。
有演员背地里抱怨围读“像诵经一样”!
围读会的布局,刚好框死了视觉空间,家福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主创全部封印到不带丝毫感情的文本之中,时间被模糊,个性被抹杀。
家福尤其盯紧高槻,多次粗暴纠正他的表演意识,令他“只能和文本对话”,并且无视演员们的抗议(詹尼丝曾用英语说“我们不是机器人”)。
李允儿(索尼娅),第一个攻破了家福的壁垒。
滨口龙介特地铺排了一场“道歉”的家宴,家福被拉进一个幸福的家庭,同去的还有将会成为家福亡女镜像的渡利。
在家宴里,李允儿——索尼娅以身体的而非声音的交流方式破除了家福的语言习惯,让向来以“聆听者”自诩的家福捉襟见肘。
一番“对话”下来,家福被李允儿夺走了话语权。
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语言隔阂的突破:先是由李允儿——索尼娅以手语(身体的)表达,经由她的丈夫——导演助理尹秀翻译为日语,再转述到家福——导演这里。
对话间,家福得知李允儿曾怀孕流产,她也不再是一名舞者。
为了走出阴霾,李允儿随尹秀赴日,鼓起勇气报名了《万尼亚舅舅》。
在家福面前,他俩是一对更为完美的患难夫妻,他们的家里养狗、种菜、享受烹饪,一切都是家福和音所缺失的。
家的影调在视觉上暖到极致,是前四十分钟里家福和音所处的所有空间的反面。
李允儿和尹秀共同经营的完美家庭,是家福和音永远无法企及的乌托邦。
此后,李允儿调皮地要求家福尽量多夸夸演员们,家福罕见地大笑不止。
回驻地的路上,家福与渡利谈起了各自的羁绊,家福活在对妻子的美化叙事里,渡利则感恩母亲教会她驾驶。
尽管交流的是各自的自欺幻觉,他们之间还是发生了能被称之为“交流”的对话,而这刚好是在感叹了李允儿和尹秀“是多么好的一对儿”之后。
次日,家福居然真的破格,暂时抛开剧本围读,让演员们代入角色去排演几个段落。
这一排演行为,止于高槻和詹尼丝迟到后糟糕的表演。
面对高槻,家福还有坎儿没迈过去,他让大伙儿再次回归到剧本围读,桌子被重新围起来,所有人又再度被困。
第二个让家福破例的是司机渡利。
在和渡利“参观”过广岛的垃圾处理厂之后的一天,家福把整组演员带到了户外、带到了渡利眼前,让渡利看到了排演。
索尼娅和叶列娜在温暖的大自然里,在接近古典戏剧剧场的空间中,找到了文本之外的某些东西。
此后,高槻受困于自己迟迟无法进入万尼亚这一角色,再次邀家福喝酒。
回程中,家福的车里破天荒坐下了三个人(此前要么是自己、要么是家福和音、要么是家福和渡利——关系也就只限于驾驶员和乘客)。
高槻补完了音的故事,彻底颠覆了家福精心钩织的文本之茧。
次日,演员们开始带妆彩排,高槻的表演得到了家福的称赞,却被警察带走。
高槻——以身体直感为行动本能的青年演员、音的情人、音的故事的另一“聆听者”——出于愤怒本能误杀了偷拍他的路人。
一个很可能是过激的但却是全新的“万尼亚”就此不见,家福只能重新面对他逃避许久的角色。
家福与高槻,这两个万尼亚,第一次见面是在《等待戈多》的后台化妆室,音领着高槻拜见家福,在不容他人踏足的空间,家福把音和高槻都隔绝在了门外。
两个万尼亚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舞台,家福作为凝视者,看着高槻成功地甚至是超越地诠释了本该是家福的角色——万尼亚,发出了由衷的赞赏。
这一对仗与错置,再次把万尼亚和家福缝在一起,家福利用《万尼亚舅舅》的文本催眠了自己,又必然通过这一文本对他和音的关系祛魅、对他把自己缝合进万尼亚的这一自怜的心态祛魅。
经由北海道之行,《万尼亚舅舅》公演,这次公演是对《万尼亚舅舅》(音去世后)的首演的一次颠覆:首演的万尼亚独自在后台泣不成声,第二次的万尼亚在后台被教授拍肩鼓励;第一次的万尼亚没有观众、台下一片漆黑,第二次的万尼亚出现了多次、多角度的不同的凝视者——从后台的詹尼丝看着闭路电视、到观众席上的渡利和尹秀等人的凝视。
在和渡利共同直面他们各自的曾经的创痛之后,家福的舞台空间得以开放,形成真正意义的纵深空间。
在李允儿——索尼娅的手语引导下,家福——万尼亚被催眠般地“聆听”着手语台词——在音的录音里从未出现过的台词——“我们要继续活下去”——正是此前家福对渡利所说的话。
此刻的镜头,前景是索尼娅安抚万尼亚、后景纵深处是渡利的凝望。
家福从舞台回到舞台,重新诠释了《万尼亚舅舅》的文本。
“活下去”的台词段落,通过李允儿——索尼娅的手语,传递给家福和渡利,被他们真正“聆听”到。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与依赖身体本能的高槻不同,家福依赖语言、信奉理智,自律到冷漠的程度。
两人之间曾有一段充满了戏谑的对白:高槻因为迟到向家福道歉,说自己去“听”詹尼丝倾诉烦恼,家福当即质疑他“明明连语言都不通”,高槻的回答则是“所以上了床”(大意)。
看似戏谑的回答,揭示了高槻的聆听才是真正的“聆听”。
到后来,在车上的对话,高槻道出了对音的仰慕,而这份爱的前提并非纯粹的肉欲,高槻对音有着他自己的观察和体认,他的结论被局外人——渡利所认同。
倾听了高槻对家福的剖白,渡利告诉家福:她能感觉到高槻说的话是发自心底的。
语言不通,是否就妨碍沟通?
家福一直沉迷的《万尼亚舅舅》,其对白表现方式是来自各地的演员以各自的母语沟通。
家福一直强制演员们反复“围读”剧本,在各自语言存在先天隔阂的前提下,每一位演员就只能自说自话,独自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自呓般的“对话”,而不是与他者进行交流。
家福从李允儿和尹秀的家里回到驻地后,开始研究其他演员的语言,对叶列娜——詹尼丝的对白部分进行标注,这一举动在视觉上正是家福开始跨越鸿沟的尝试。
影片中,家福出演过《等待戈多》,是一种实验性的戏剧,艾斯特拉贡和弗拉基米尔语言不通、自说自话。
当时,家福以日语和另一角色以印尼语“对话”,引发台下观众的笑声。
尽管这出戏否认了沟通的意义,却没有否认“沟通”的事实。
最后的《万尼亚舅舅》,角色之间同样是各说各话,最极端的是索尼娅用手语,但也正是索尼娅的手语引导着万尼亚走出幻灭和自弃情绪。
滨口龙介借此给出了沟通的可能——以身体而非语言沟通,打破自我建构的镜像,让自说自话的人能透过身体的冲突和借由身体去“聆听”、去发现并走近他者。
在影片中,舞台犹如“巴别塔”的废墟,发生于其上的交流可能超越语言的沟壑,达成真正的理解。
在《那些欢乐时光》里,滨口龙介回顾电影《欢乐时光》的创作历程多次谈到“聆听”、“身体”、“围读”、“通往肺腑”……他的“表演工作坊”花了很长时间让演员们彼此“聆听”——并不是简单地听对方说话。
滨口龙介在书里说:“在一种被人倾听的实感之中,人们发出‘美好的声音’——让原本真假难辨的‘叙述(欺骗)’有了可信度,让人觉得那些叙述表现着叙述者自身的真实。
我试着把这种‘美好的声音’移植到我自己一直以来从事的领域——剧情电影的时空。
”这一说法的语境,是滨口龙介曾经到东北地区拍摄地震灾后专题纪录片时,发现叙述者之间超越了历史时间空间的彼此倾听。
进而,滨口龙介悟到了他的表演方法。
可以说,影片中对《万尼亚舅舅》的排演,以及家福和渡利相携着重新直面过去的段落,都贯彻了滨口龙介的这一理念。
家福缺席的尾声部分,渡利独自走在充斥着异域语言符号的迷宫般的超市里,她自如地以韩语购物、结账,开着曾经只属于家福的红色SAAB 900T ,车里还有一只属于她自己的狗。
渡利不再是孤身一人,行驶在异域的公路上。
如家福所言:要是女儿活到今天,刚好与渡利同岁。
渡利美纱纪在电影文本里是家福永远缺失的女儿的镜像,她唤醒了家福对“他者”的关注,先是侵入了家福的车(作为保护壳的移动茧房),继而又成为音的语音文本的另一个聆听者。
作为局外人的渡利还听到了家福对过去的自叙、家福对高槻的报复性的叙述、高槻对音的叙述。
不止于此,渡利在家福认可了她能做司机之后,还允许她进一步侵入(车内吸烟),她还对音的声音和行事风格甚至为人印象做出了独到的虽未谋面却冷静客观的同为女性立场的读解。
渡利之所以能让家福心甘情愿地“驾驶我的车”,成为真正意义上侵入了家福的他者,绝非只是因为年龄上的巧合,而是因为她和家福各自被亲密关系严重伤害过,并且都建构了另一套叙事,她俩都封印着被伤害的真相,甚至,也都保存着通往幽暗处的入口。
对家福而言,创痛的口子是音诵读的《万尼亚舅舅》的语音文本,他带着它随时收听,像任何人都会抠破结痂的伤口——上瘾地屡次抠出血——再等待结痂——再次抠破,家福就是要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音”,催眠的同时享受着被伤害的痛感。
渡利始终保留着她左颊上的一道显眼的疤痕,那是她“杀死”妈妈留下的印痕,她故意不做祛疤手术,让自己随时能惩罚自己,也沉迷于这样的自己。
尽管家福和渡利都曾自欺地编织了另一套叙事——在他们的叙述中,音是默契的伴侣、妈妈是渡利的驾驶老师和唯一的依靠——家福和渡利却也同时留住了这一创口,他们随时都能打开通往过去幽暗世界的门。
正如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的“井”、《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胖女郎守候的入口、《舞!
舞!
舞!
》里海豚宾馆漆黑的第16层……黑暗世界的入口一直都在,有些人选择视而不见,有些人结伙拼命掩盖,有些人则会一直带着它、直到那个自我唤醒的契机出现。
回到北海道的上十二泷村,面对被泥石流掩埋住的“家”的废墟,家福和渡利直视自己的深渊,他和她都被各自的挚爱——妻子和妈妈——深深伤害,也都以自己的方式“杀死”了她们——音和“佐知”(妈妈分裂出的另一人格、渡利唯一的朋友)。
家福说:“活着的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死去的人,无论是以哪种形式。
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和你,也会一直这样活下去。
”家福和渡利接纳了那个不可原谅的自己,呓语着脱胎于《万尼亚舅舅》里的台词——“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相互紧紧拥抱住对方,各自的他者。
5 ) 真心与谎言的迷宫,戏剧和现实的重叠
《驾驶我的车》名义上来讲是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同名原作,但实际上契科夫的《万尼亚舅舅》我觉得更是中心灵魂。
滨口导演在这部作品所展示的野心真是非常之大,大胆地同时基于两大名家的作品进行改编,编织了一个更大的框架,将两部原作融合在了一起,打上了滨口龙介自身鲜明的烙印。
可能其他导演对于改编作品相只是简单当了裁缝,滨口导演在本片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了一个织梦者,以自己的思考和感受驾驭名作并拓展为自己的广阔世界。
本片在主要剧情上分了三条线穿插推进:1. 作为一名舞台剧演员兼导演的主人公家福与作为剧本家的妻子从亲密相处到怀疑猜忌的过程,并最终完结于妻子的意外身亡。
这一部分是为全片最为重要的基石,也是后两条线故事线的源头与终点。
2. 作为导演来到广岛指导《万尼亚舅舅》戏剧演出,与剧院的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所产生的各种连接,特别是与妻子旧识高槻的交流,挖掘了亡妻所不为人知的过往。
这部分窃以为是本片最精妙的部分,不仅以戏中戏的方式呈现了《万尼亚舅舅》,同时以《万尼亚舅舅》的剧本做了隐喻,对于现实的人物关系做了映射。
3. 自己与女司机渡利在行驶中互相深入,互相解救对方的过程。
这一部分应该是改编自村上的原作部分,我其实本身是没有看过《驾驶我的车》这篇村上的原作的,对于本片与《驾驶我的车》原作的连结知之甚少,还请多多宽容指正。
前面也说到,本片不是基于原作的改编,而是滨口导演的一种借壳探讨,甚至我认为可以算得上是原创故事。
本片的核心,在我看来,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建立与维持和理解他人的困难性探讨。
以家福为视点,无论是妻子音还是高槻还是渡利,抽象到更宏观的层面来讲,都是一段关系中的相互试探与猜测,只不过因为角色的不同,在关系中的付出、索取乃至心态有着很大的差异。
但究其本质,都是自我对他人画像侧写与他人真实人格的冲突与修正。
夫妇线——真心与谎言的迷宫滨口导演用了足足40分钟的时间,铺垫了这对夫妇的相处关系,甚至还刻意放在了演员表之前。
影片的开头非常有神秘感,黯淡的凌晨、摇曳的身姿、不知所言的故事。
只有在寂静的深夜,潜藏于不知名暗处的精灵才会一显身姿,伏于身畔,耳语那些欲望的呻吟。
家福望着妻子半裸的胴体,却看不真切,仿佛处在现实和梦境间的裂缝,任凭那些虚幻的触须在自己的脑子里留下烙印。
【她有自己的原则,她会要求自己能做某些事情,不能做某些事情。
】【她可以偷偷溜进他家,但不能在那里xx。
】【没错。
】
荒诞的故事是妻子对自己的谶语,至少在当时,妻子还是非常自信自己不会陷入欲望的漩涡,尽管欲望之海已悄然没过了她的的膝盖。
家福在出差的意外间撞见了妻子的偷情现场,但最终没有声张,仿佛无事发生过。
但内心的裂痕避无可避。
越是不能正视现实的痛苦,越要面对内心的崩坏。
但实际上,家福撞见的那刻,妻子也同样通过镜子看见了他。
因此在家福回家后,续写了自己的故事。
女孩终究是越过了自己设定的边界线,想起了自己作为 八目鳗 的前世。
但是这一切发生后,两位当事人的内心在各种无端的揣测与翻涌,却要在表面上维持风平浪静的假象。
即便在言语上密不透风,行为的细节却早已变质,海市蜃楼总归是会被撞破。
妻子决定踏出这一步,无论现实在主观上的好坏,终归是不可掩盖的真相,只有真相的忽视才是最大的伤害。
但在一切成行之前,她却意外迎来的生命的的终结,一切结束。
其实通篇下来,妻子对家福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在于,人是无法拥有另一个人的。
越是爱之深,越不会将自己认为自己的丑恶恶心的部分展现给对方,只会顺应着去表现对方想要看到的自我。
但这些难以名状的黑暗并不是不存在,人是无法自己否定自己的,你只能分割开来,让不同的人去回应你不同的部分。
也不要期待能有世界上另一个我,能无缝全盘接受,毕竟二重身的传说,最终都只剩唯一的留存。
万尼亚舅舅线——演出上映于现实与戏剧的重叠滨口导演以一种近乎“断章取义”的方式将《万尼亚舅舅》打散并重新以自己的视角做了再诠释。
影片非常巧妙地将《万尼亚舅舅》的人物关系与对应演员之间的关系关联起来,使得同一个情节场景在现实和舞台上双重上映。
滨口导演再一次给我们展示了他最熟悉的魔法,但这次不再是梦与现实的交融,而是舞台与生活的重叠。
场景一。
高槻的第一次试镜。
阿斯特罗夫——高槻,万尼亚——家福,叶莲娜——Janice(家福音)。
这一幕其实很明显,是家福撞见妻子家福音偷情回忆的具像化。
这段三角关系被直接地套用高槻饰演阿斯特罗夫对叶莲娜表白这段试镜中。
一方面以这些戏剧角色去展现高槻、家福乃至音在当时的心理活动,作为观众更能以《万尼亚舅舅》的戏剧角色的理解丰满影片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高槻以表演的的形式重新演绎家福回忆中类似的剧情,引发了家福与高槻的人物冲突。
特别是最后家福作为导演的对表演突然打断,这契合了《万尼亚舅舅》中万尼亚对阿斯特罗夫的打断情节,但在现实中是不合时宜的,这也表明了家福内心的动摇。
再以试镜的表演先谈谈高槻的的人物形象。
高槻的表演是充满攻击性的,他习惯以更加主动的的方式去“侵入”目标。
所有的肢体接触都是从高槻发起,在第一时间就展现过量的情感,这种激进在其他人物里是缺席的,这也是高槻在片中最特别的地方,这种激进我会在最后总结详细再做对比展开。
场景二。
高槻与Janice迟到后第一次排练表演。
万尼亚——高槻,叶莲娜——Janice(家福音),教授——家福。
试镜结束后,家福出乎意料地将万尼亚的角色给了高槻,这一戏剧角色的转变也正是代表着这核心三角关系又出现了再平衡。
万尼亚暗恋着作为教授妻子的叶莲娜,但同时对于教授又饱怀尊敬,从上帝视角来看,无疑这样的关系才是最贴切现实的人物关系。
但其实全片本就是贯穿的家福的视点。
在过去,他认为自己无法把握妻子的身体与内心,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万尼亚,总是在艰苦地追逐妻子剪影。
但在第一次在酒吧高槻对家福的坦白中,高槻直言了自己对家福的嫉妒,对于家福而言,他才终于能明白妻子不仅不是抓不住的镜花水月,反而双方都是对方的束缚。
但对于高槻来讲,他不过是音的弃子,是真正的求而不得。
场景三。
双姝的对手戏。
叶莲娜——Janice(家福音),索尼娅——允儿。
这是一场很特殊的戏份,这一幕没有高槻没有家福,无法寻常地将三角关系对应起来,但没错,这一场就是家福音的独白。
音并没有特别处理自己与家福和高槻的关系,她对两人只是顺势自然地发展,至少行为上是如此,即使在她意外死亡之前想要去打破僵局,却也应为自己的意外死亡而无法成行。
在契科夫的笔下,叶莲娜同样也知道万尼亚、阿斯特罗夫对自己的苦恋,她同样也没有特别处理这两段关系。
因此滨口导演巧妙的将家福音置于与叶莲娜同样的境地,借契科夫之笔,与家福做了一次跨时空的对话。
而允儿在全片到底是一种什么角色?
索尼娅在《万尼亚舅舅》中可谓是纯洁、坚强、美好的化身。
同理,映射在影片中,允儿同样担当的是这样的角色。
她以天使之姿,在表演台词的同时更是对对端人物的开导与安抚。
更由于她身为longya人,代表了一种无法赋予谎言属性的纯洁,是索尼娅在现实中拓展。
场景四。
高槻最后的悲鸣,被捕前的排练。
万尼亚——高槻。
万尼亚最终发现了教授的虚无,过去十几年所奉行的信仰轰然倒塌,那些过去曾经支撑他在平凡中淡然的理由,此时都被反攻倒算,变成了复仇和愤怒的燃料。
高槻在车内与家福的的对话中发现了,家福根本配不上自己心中完美的音,他根本上不过也是无知、自私、软弱的一条败犬,那些音曾经预言的谶语,家福不知道全貌却自以为很懂,表面上相似的夫妇随着愈发地深入,裂痕被百倍的放大,以至于貌合神离。
即使这样,家福和音的关系中从来不存在他的容身之地,而自己作为第三者,只感到了对自己无尽的哂笑。
在对现实发泄了自己绝望,高槻淡然的走向了自己的结局,以故意伤害罪被警察逮捕。
在这场闹剧关系中,无论家福和音有多么的愚蠢可笑,但在关系中,永远没有他自己插足的余地,他只不过是心怀幻想被遗弃的小丑。
场景五。
现实与舞台的同时完结。
万尼亚——家福,索尼娅——允儿/渡利。
随着高槻的离开,家福不得不重新面对万尼亚的角色,怀着与万尼亚一样的对过去的悔恨与痛苦,立于生活与聚光灯的台前。
契科夫为我们写下了结语。
惨烈也好、苦痛也好、不堪也好,在时间长河中,人总要与自己和解,或者说不得不与自己和解。
明天来临之后,你总得去做点什么,或许拾起熟悉而亲切的旧时光,或许斩断所有的留恋踏足新世界的未知,就这样假装正常到自己真的正常。
家福与女司机渡利的故事线我不再做详细展开了,这是属于两个困于过去的人的互相舔舐,在共同经历下,去深入对方的情感。
最后的旅途,来到了渡利痛苦的起点,上十二泷町,他们要去探寻回忆的正体,去击败最后的心魔。
看,那是什么,一座辨认不得的废墟,这就是回忆的正体。
世界永远不会为你个人降下束缚,只有自我封禁才是永恒的牢笼。
渡利之于家福,从侧面最终解决了家福的痛苦,并且又年龄上的暗示,渡利与家福的女儿是同年,索尼娅也是万尼亚的外甥女。
所以来讲,本片其实存在两个索尼娅,允儿在戏剧所代表的隐喻中扮演索尼娅,而渡利在家福的现实中扮演索尼娅,最终都是拯救家福的关键。
相处、感受、理解、心之壁滨口导演在本片对人与人之间相处做了很多实验性质的探讨和尝试,也是我认为本片最主要的内核意义。
相比于充斥本片的大量对白台词的表达方式,导演想表达的却是,语言是最不可靠的交流方式。
正如在排练的情节中里,家福对演员的要求,将台本的每一句刻画成自己的本能反应,而在真正表演的时候,不去思考每一句台词的含义,有更多的精力去捕捉去体会与自己对戏的演员的情绪和动作,并基于此给对方以反馈。
滨口导演实验性的地方也在此处,《万尼亚舅舅》这场戏剧排演,演员们都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每个人都是用不同的语言,更近一步,还添加了允儿的手语表演。
其实演员之间根本就听不懂对方的对白,那么因此也就无需听懂对白的含义,只能从话语之外的地方去感受对方的表达。
那么再转回家福与妻子的夫妻线,其实家福和妻子分裂的原因也在于过于去揣测言语的含义,他们想要从对方的言语中去获取对方的全貌,但现实是只要有言语必然有谎言,甚至应该说是言语促生了虚假。
如果一个行为发生了,那它就是真实,它是已经发生的现实,行为即真理。
但言语发生了,它并不代表着什么,行为不与它有任何强绑定关系,它正好就是发生与未发生的薛定谔态。
还有一部分,是关于高槻的。
高槻在所有的角色里是最为激进的,他在关系的的初期会更有攻击性和主动性,因此会让人了解的更快也更直接,但我们以最后高槻的结局来看,滨口导演是更倾向于内敛,也是因此,影片充斥了家福对高槻的批评和指导情节。
其实也可以理解,对于一段长期关系而言,自我暴露可能远比不上让对方挖掘。
正如布莱希特所言:“如果你追逐幸福时跑得太快,那你会将幸福甩在身后,而不是得到它。
”如果基于这个角度,那么高槻在车内对家福的坦白和规劝就显得比较玩味了。
家福作为内敛型关系的实践者,最终也免不了与妻子关系的变质,那么实际上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最终也不过是殊途同归。
可能正如高槻所言,人是无法完全理解他人的,这就是人的心之壁,但同时这也是人的独立性象征,人总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就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正确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去做诚实的选择和表达。
写在最后足足将近三个小时的电影,还伴随着无比巨大的台词量,但整部影片让人观感极佳,顺滑流畅,不得不说滨口龙介导演在这部电影剧作和台本上的控制已臻化境,但在视听语言上,可能就稍显质朴了。
虽然我没看过《驾驶我的车》原作,但村上的书我看过的还挺多的。
在这部片里,包括李沧东的《燃烧》,都很好的抓住了村上的精髓——隐喻。
从《海边的卡夫卡》到《1Q84》到《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到《刺杀骑士团团长》,村上春树用隐喻为读者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一段最优秀的文字需要去映射出每个人的内心,电影也是如此。
6 ) 救赎和延续:用新颖的套层结构去讲述归一的故事
《驾驶我的车》采用了传统的套层结构叙事,即我们日常所讲的“戏中戏”——众人排练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作为“第十届广岛国际演剧节”的参演剧目。
影片并没有像一般的“戏中戏”电影那样,采用单一的层次处理,将冲突局限于剧场内外;而是开辟出“车”这一事件场景,借助其本身即有的窄小内景和显著意象,将部分重要剧情迁移至此,更好的讲述了一场有关救赎和延续的故事。
一、录音带: 妻子已然死去,其出轨的事因、去世当天意图与男主沟通的事情、前世是七鳃鳗的少女的故事,都成了尚未解答的隐谜。
为了让这些悬念和“妻子”本身即具有的意义延续下去,滨口龙介巧妙设置了这盘由妻子录制的、纪录有《万尼亚舅舅》文本的磁带。
它贯穿剧情始终,在车内循环播放。
男主与妻子的声音排戏、揣摩台词的同时,也是与亡妻的幽灵、经历相似的万尼亚之间一场“另类”的对话。
此时的车子,已经成为了剧场之外的另一个舞台,它联结着现实和原著,阳世和阴间。
更重要的是,它是男主意识与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无意识)唯一相接的通道。
在车子之外,男主是逃避自我的,家庭中的寡言,剧场内的强势,都是对其已经破碎的人格的掩饰。
他不愿让妻子和渡利驾驶,是因为车子是唯一属于自己的领地。
只有在契诃夫现实主义情结的呼唤下,他才能直面内心的不解、憎恨、歉疚和眷顾,将万尼亚作为自我的外在映射,使现实的悲剧同剧中人物的悲剧对照在一起,放下芥蒂,谋求出路。
这样的动机是便于理解的。
它使得《万尼亚舅舅》内重要场景、重要台词虽然多次复现,但观众并不会觉得刻意。
不同于传统套层结构中剧场“内-外”单调的对比,滨口龙介通过男主和录音带,设置了一个特别的缓冲区域,对单线叙事下的单一冲突进行了分割,随着车子驶向不同地方,随着录音带的不断播放,契诃夫的剧本作为一种再现、互补和暗示,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最终完全重合,即《万尼亚舅舅》的上映。
二、七鳃鳗和幸存者 男主和女主关系的破裂,应该是自爱女死去之后开始的。
她是不可替代的,女主不愿再次生育的想法肯定了这一点。
女儿血管内的激潮虽然淹息了,但更加汹涌的追忆令她并没有消解,而是硬化成海底的一块化石。
他们依附于此,直至成为两条水草般单薄的七鳃鳗。
“幸福时光”已经宣告终结,但他们毕竟“要继续活下去”。
于是,“那个东西”出现了。
它到底是什么,影片中并没有交代。
它可能是对重新开始的希冀,可能是爱的表层化示像,也可能仅仅是“继续活下去”这个执念本身。
无论如何,生活有了新的动力,他们继续做爱,分享着女主性高潮前梦一样的灵感,依旧保持着“紧密”和“充实”的关系。
然而,女主是清醒的。
大概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发现“那个东西”,并没有赋予两人真实的生机,反而放大了他们作为七鳃鳗的寄生特性。
他迷复于自欺的深垒中,依托旧情的余烬去拉扯渐远的关系;而她则沦陷在欲望的沉渊里,曲附血肉的交汇来麻痹阵痛的母性。
有些事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就像少女无法选择忽视杀人的事实那样,再虚假的激情也无法填补那段有关逝者的空白。
他们该做的是沟通,是共同面对真像前的那枚摄像头,同过往进行痛苦的诀别,让时间继续流动下去。
女主给男主讲了七鳃鳗的故事,可后者即便知晓其中的隐喻,还是“假装它没有发生”那样,合上了电脑。
他再一次选择了逃避,女主只得在等待后,选择了更直接的告别。
男主成了幸存者,但他并没有解脱,而是“一直思考着死亡”。
挚爱的离去让所有的未知化作米诺陶洛斯巨兽,一日不停的追逐着男主,任其逋逃于歉疚和依存的迷宫内。
三、½+½=1 男主家福,仅知道“七鳃鳗”故事的前半段,是后半程的万尼亚; 情夫高槻,知道“七鳃鳗”故事的后半段,也是前半程的万尼亚。
两人通过妻子音而相遇,并在音“声音”的牵引下,逐渐放下戒备,最终在车中吐露真情。
家福获知了真相;而高槻则因袭了万尼亚的宿命,他“内心空空如也”,捧着玫瑰,却发现阿斯特洛夫(这是他本来试演的角色)正拥吻着叶莲娜:家福与音的戏剧是共通的,这是他们彼此爱着对方的证明。
他只是音肉体情欲的某个对象,爱而不得的他选择追随音,成为了另一条七鳃鳗,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完成了殉情。
完全对称的侧光和剪辑 男主家福,拥有½的妻子;司机渡利,拥有½的母亲。
两人是同样的幸存者,被至亲的死亡所负累。
依然是通过“音”,渡利看起了契诃夫的剧本;而从她开车的那一天,家福就让渡利进入了他的世界。
妻子或母亲的形象对于两人都是不完整的,但他们最终发现,那与爱并不矛盾。
高槻,1989年出生,比村上春树的原著晚了将近二十年;渡利,23岁,如果家福和音的女儿还活着,恰恰是同样的年纪。
高槻、渡利,作为冥冥之中音的延续,代表着“年青”的意象。
在两人的影响下,家福终于拼凑出生活的原貌。
前者代替音向家福道出未曾出口的珍重,而后者则完成了两年前就该进行的救赎。
在话剧的最后一幕,在同样的布景、光线、服装和动作中,家福依旧低着头喘息,只不过这次让他艰难的台词不再是第一幕的“那个女人的忠诚,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而是“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影片结尾,渡利开着家福的爱车向远方驶去。
家福去了哪里?
如果将时间拉长至“我们死后一百年或者两百年”,这个问题连同这个线性叙事下有着“½+½=1”复调内核的优秀故事,都将变得不再重要。
生活会一如既往的继续下去,不管是“在天赋的事物以外再创造新的”,还是一味的“毁灭”,人们总会“继续活下去”。
渡利不仅仅兼具了家福和音的影子,更蕴含着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她是女儿庄严的重生,是并非来自血缘关系的传承,也是契诃夫在苦难的现实里依旧坚定的寄托。
7 ) 车选得非常应景——Saab 900 Turbo
车选得非常应景,Saab的品牌特质和男主非常契合——理性,内敛,进取,外加些许直男。
这部Saab 900 Turbo曾经作为詹姆斯·邦德的坐骑出现在80年代早期的三部《007》小说——License Renewed(1981),For Special Services(1982)和Icebreaker(1983)中,也侧面暗示了男主曾经事业的辉煌。
此车技术非常超前,以至于油管上有人将其称为“那个时代的特斯拉”:1. Turbo,即涡轮增压技术。
现在已经普及的涡轮增压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排气气流驱动一个压缩机,将空气压缩送入气缸,使得小型发动机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
Saab不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也不是第一个把涡轮增压应用于汽车的制造商,但却是第一个将这项技术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制造商。
涡轮增压技术的普及最大的问题在于耐久性,为了向公众证明自身技术的可靠性,Saab于1986年在美国Talladega环形跑道进行了一项世界纪录挑战,使用原装市售车辆,只换人不换车,连续高速行驶16天,累计里程80000公里, 平均时速213.691公里/小时,这个将近40年前的纪录放在今天来看都多少有些魔幻。
但这代表了Saab的品牌特质——技术与进取。
2. 迥异的动力系统的布置形式。
笔者第一次看到Saab 900的设计差点惊掉了下巴。
先简单进行一下科普,对于传动内燃机汽车来说,发动机/变速箱经典的摆放形式基本有两种:横置——发动机/变速箱轴线与车轴平行,纵置——发动机/变速箱轴线与车轴呈90度角。
产生这样区别的原因在于驱动轴的位置,如果使用前轮驱动,发动机横置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反之如果采用后轮驱动,那么纵置便更有利于布置中央传动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轮驱动结构不能使用纵置发动机布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奥迪,因为奥迪兼有前轮驱动和四轮驱动两种驱动形式,因此奥迪有理由使用前置发动机纵置结构,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变速箱结构会更加复杂。
Saab 900 Turbo的设计非常有趣,首先和传统发动机/变速箱串联式设计不同,发动机和变速箱为上下布置,即发动机被变速箱顶起直接装配在变速箱上方,这样变速箱上端盖可以直接作为发动机的油底壳,同时可以压缩纵向空间,非常聪明,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整个动力总成的重心太高,以及整机高度过高塞不进机舱,对此Saab的解决方案是,将直列4缸引擎倾斜摆放,解决高度和重心问题;其次是离合器的位置,用作动力接合/切断的离合器通常位于发动机变速箱之间,这也导致维修更换异常困难——需要将整个发动机/变速箱拆下,Saab的设计实际是将发动机沿纵轴线调转了180度,再通过链条连接发动机曲轴和变速箱输入轴,也就是通常向后的离合器被转到了车头的位置,非常易于维修。
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到过第二台这种设计的前轮驱动汽车。
3. 发动机盖开启方式。
浑身都是戏的这车连发动机盖的开启方式都和正常车不一样,正常车是向前,而这车是向后的——和很多跑车一样。
开启方式异常复杂,解锁后需要先将整个机盖整体向前拉,然后向上翻转,但姿态非常艺术。
4. 独特的钥匙孔位置。
保时捷和Saab应该是世界上唯二两家钥匙孔不在转向柱上的汽车制造商。
保时捷的钥匙孔在转向柱左边的中控台上,Saab则改到了手刹前面。
造飞机的瑞典工程师认为,这样的设计在碰撞中可以提升安全性。
5. 手刹。
是的你没看错,现在世界上99%的汽车,手刹都是作用在两个后轮上的,而Saab 900的前期款相反,作用在两个前轮上。
Saab的工程师就是这么与众不同,美国人很喜欢在自家门口的斜坡上把一个车轴支起来自己修车,一些比较倒霉的车主因此经历了特技时刻。
6. 左舵。
细心的人会观察到电影里的车是左舵的,而日本是个左侧行驶的国家,也就是说正常应该是右舵。
这里有一个梗,日本虽然名义上为右舵但并不排斥左舵车上牌,于是路上出现很多诸如奔驰S之类的左舵的进口车。
另一个点是,Saab 900这部车实际上存在符合日本法规的右舵版本供应英国市场,但电影中呈现的依旧是原汁原味的左舵版,而且选择了一台大红色,在日本的雪中非常漂亮,要知道在欧洲市场红色并不是主流,Saab 900保有量大的颜色是黑白银。
最后插句题外话,在右舵国家里开左舵车始终什么体验?
首先,会很不方便,比如停车场入口机器是在反方向的副驾驶一侧;其次会有安全隐患,无论左侧还是右侧通行,不变的是主驾驶永远靠近路中央,片中这种开法相当于坐在副驾驶开车,视野是严重受限的,也许主角的车祸于此也有关。
同理,副驾会被移动到路中央,本来是看路边风景的结果看到的确实对象车冲过来,笔者曾经在德国搭乘一台右舵英国牌照的车,说实话作为一个老司机坐在副驾差点被吓尿。
7. 片中渣男小白脸开的是沃尔沃V40,沃尔沃整个产品线里最低端的产品,也是一部瑞典车,符合他的人设。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台湾女坐在外侧,因此这部沃尔沃是符合日本道路规范的右舵车,和主角的Saab也算是遥相呼应。
从两车并行的镜头看,小白脸的沃尔沃在慢车道,主角的Saab在超车道,在被超车时突然加大油门非常不礼貌,多少可以反映出渣男的心绪,最后不出意外的在下一个弯道撞了。
8 ) 是的,我们应该活下去,哪怕带着伤痛
驾驶我的车 (2021)7.92021 / 日本 / 剧情 / 滨口龙介 / 西岛秀俊 三浦透子 以下内容超长,根据叙事线将家福如何从男孩成长为男人、渡利的十五次开上家福的车每次不同的变化,每个人物的发展线以及画面和剧情中的一些象征和意象分别拉了出来了。
多图预警。
妻子所讲述的前世是七鳃鳗的女孩的故事中,有讲到,女孩每次都会带走一些东西,留下一些东西,有一次留下的是卫生棉条,最大胆的一次是讲自己的内衣脱下塞进男孩抽屉的深处,女孩希望通过这种交换使男孩获得对抗母亲的力量。
在男演员高月后来的转述中,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女孩杀死了一个小偷,她在男孩房间里最后留下的东西是一个人的生命。
故事其中的一个意思是,女人可以给男人以获得”成长的力量“,在故事行进过程中,家福通过男演员高月(逝去的妻子音的代表),女司机渡利,以及哑女演员最终完成“成长”可以得到印证。
其二是关于七鳃鳗,七鳃鳗是有刺的通道,“成长”需要通过一次次的有刺的通道,经历这些伤痛才可以完成,这点在故事行进过程的后半部分,家福开始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自己的伤痛以及”真相“时,红色小汽车经过的一个又一个的隧道可以得以印证。
其三关于杀掉小偷,留下生命,大概可能对应着,妻子音用自己的死亡,用自己的生命来促成了家福的“成长”。
(也有可能我过度解读了) 家福与音之前有一个女儿,但因为肺炎去世了,这是他的伤痛其一,后来妻子去世,家福一直不能走出这个阴影是伤痛其二。
其次汽车、磁带的设置也暗示了家福是个没有长大一直在逃避的男孩。
家福有一台开了十五年保养的很好的车,并且他非常喜欢开车,并且他在车上听妻子音的对白磁带,汽车是男孩的玩具,这辆红色的汽车就是家福珍爱了十五年的大玩具,妻子的声音在车上出现就像是母亲的声音那般,共同给家福营造了一个子宫一般的安全空间。
家福在撞车之后,被诊断出青光眼的时候他第一关心的不是他会不会失明,而是他还能不能再开车。
由此可见,他对车的珍爱和情有独钟;妻子出轨,家福目睹了这场出轨之后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在电影后面的讲述中我们的得知,家福太爱音了,他害怕音离开他。
所以离不开音。
但其实也是他不想面对一直逃避的结果。
这是家福在故事最初面对痛苦的事情的应对方式。
汽车,以及汽车里的声音侧面印证了家福似乎是一个还未长大的男孩,故而,音的存在、车的驾驶权以及车上是否放磁带也成了判定家福是否从男孩“长大”成为男人的一个象征。
汽车与磁带声音一体 妻子音去世之后,家福在舞台上没有顺利的演出,是否能够再次扮演万尼亚舅舅,是否能够在台上再次顺利的演出是判定家福能否成长的另一个象征。
妻子音去世后家福在台上没有顺利演出 基于以上,家福的成长之路开始了。
(成长不一定是非得要扔掉过去开开心心的活,背负着伤痛活着也是一种”成长“) ”成长“之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是要让位车的驾驶权,戏剧节这边因之前的艺术家开车撞过人为由给家福请了一个司机(渡利),家福三番两次的拒绝未果,只得让位车的驾驶权。
但他还是要在车上听磁带,并且每次都是坐在后座,并没有坐在副驾驶,之前妻子开车的时候,家福是坐在副驾驶上面的。
妻子开车时家福坐在副驾驶
渡利第一次开车时,家福听磁带并且坐在后座。
渡利第二次开车,镜头没有给内景,一直是车外的镜头,声音也依旧是磁带利妻子音与家福对台词。
渡利第二次开车渡利第三次开车,家福跟她说下次可以在车里等待,她在寒风中等她会让家福心有不安,交谈之后,又打开了磁带开始放对白,妻子音的声音再次响起。
渡利第三次开车第四次开车时高月第一次找家福酒吧谈话(中间插播一下高月的内容,再来说后面几次开车的变化。
) 第二个困难是要面临妻子音的影子,演员高月。
之所以说高月是妻子的影子是因为,首先高月是妻子音出轨的对象,家福曾经目睹过二人的交欢,交欢这类图景本身就是一种合二为一的象征。
其次高月知道一些妻子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家福不知道的,某种程度上来说,高月是妻子音的一部分延续。
第三,高月几次找家福谈话都是围绕着妻子音展开的。
高月第一次来试镜的时候,面对高月和台湾省女演员的亲密互动,家福站起来,动静很大的打断了两个人的试戏,大概是在这场试戏中看到了当初回家妻子音出轨的场景,他此时还不能面对,所以急忙打断。
高月第一次找家福去酒吧聊天,高月说他真的很喜欢音的剧本,因为喜欢音的剧本,所以来到这里,要抓住这次机会。
而此时的家福否认说,他的戏跟音的剧本不一样。
在第一次高月与家福的谈话中,二人并未直截了当的挑明高月就是妻子音所出轨的对象,只是间接的说了一些,高月和妻子音,以及家福和妻子音,都是互相相爱的。
家福还是在下意识的否认妻子跟眼前这个男人有交欢的事实这件事。
家福此时还是放不下妻子音。
第一次酒吧对谈留了一个伏笔,高月因路人拍照的事情与人起冲突,为后来的那次冲突并且被警察抓走营造合理性。
第一次酒吧对谈第五次渡利开车在与高月家福的第一次对谈之后。
内景,前景是渡利的半张脸,似乎此时磁带的声音不再是磁带发出的,而是渡利在向家福说话。
妻子音的位置似乎正在被开车的渡利慢慢取代。
第五次渡利开车第六次开车时去哑女演员的家中聚餐。
渡利第六次开车 在哑女家中,家福第对渡利表示认可,表明渡利在他心中的地位开始渐渐上升。
在家福表示认可之后,众人没有说话,渡利默默的离开饭桌,蹲到一边,摸哑女家中的狗狗(这是渡利第一次与狗的接触)。
渡利第一次与“狗”有接触 哑女演员(李永娥)是家福成长之路上的第三个重要的人物,哑女同样也有伤痛的过往,她曾经是一个舞蹈演员,但流产之后她再也不能跳舞了,但她没有选择就此逃离,而是选择以另一种方式,演话剧的方式来”输出自己的能量“。
这是剧情中面对伤痛比较正向的人物,与家福丧女之后地反应形成一些比对。
哑女在剧情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疗愈人心的力量,像小天使一样,她虽然没有语言,却很有力量。
她是唯一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对周围的人报以微笑的人,给周围的人传达鼓励和爱的人。
并且哑女一家其实提供了一个美好家庭、美好生活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影响了家福,也影响了渡利,所以从哑女家中出来之后,渡利在车上与家福有了真正的一次“心灵对话”
李永娥小姐姐像天使一样她在这次家庭聚餐中,希望家福可以多夸一夸演员,
点赞,夸一夸在第一次室外排练的时候,哑女与台湾省女演员擦出了一些表演上的火花,打动了台湾女演员。
因为以上哑女所表现出的这种有力的温暖人心和疗愈人心的力量,使得下次家福再次站到舞台上,在长长的无声的没有对白的场景中,被哑女环抱着慰藉着并且得到成长提供了合理性。
从哑女家中出来之后,渡利跟家福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家福也跟渡利讲述了磁带的故事和妻子音的故事,二人真正有了一次心灵对谈。
这是渡利的第七 次开车,虽然还是打开了磁带的,但妻子音的声音已经被渡利和家福对话的声音盖住成为了背景音。
家福讲述磁带和妻子的事
渡利讲述自己为什么开车好以及她的身世 第八次开车为促成高月的迟到,揭示高月在与台湾省女演员调情以及引出家福高月的第二次对谈,在家福与渡利的人物关系线上不承担作用。
第八次开车,家福坐在车上看高月与台湾省女演员在一起,磁带中妻子音的台词是:“我确信,真相,无论是如何,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未知····跟他这样的男人调情,陷入他的怀抱中,我猜···我也会有点爱上他的”
在家福与高月的第二次对谈之前,需要给家福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剧情上荡开一笔,先讲点别的,让家福做好准备之后,再迎来真正的真相。
第一层铺垫
第九次开车,渡利带家福去了垃圾焚烧厂
第二层铺垫 垃圾焚烧厂应该是象征着家福需要真正的扔掉,放下以前的事情。
在这场戏中,家福和渡利有了第二次“心灵对话”二人关系进一步上升,上一场车内对话家福只说了磁带是妻子音的声音,而在垃圾场外的海边,家福跟渡利讲述了妻子音两年前去世的事情。
以及渡利第二次与狗“接触”,一个狗狗玩具飞碟打断了二人的谈话,渡利讲飞碟扔了回去。
渡利与狗的第二次接触第三层铺垫是渡利的第十次开车,在这次开车时,他俩第一次穿越隧道,与之前音讲述的前世是七鳃鳗故事似乎有所对应,七鳃鳗是有刺的X道,而家福在真正面临真相之前,也需要通过长长的隧道像分娩一样迎来光明和好天气。
第十次开车途径隧道
出隧道之后是一座大桥通往彼岸,并且是个好天气。
多好的天气
是啊第四层铺垫是家福的戏剧有了顺利的进展,他们到户外排练,哑女与台湾省女演员的对戏产生了火花。
两位女演员之间产生了一些火花第二次家福与高月(音的影子)的对谈开始了第十一次开车,高月进入到了家福的车内的私密空间中。
上一次家福与高月对谈是高月开自己的车。
这次高月讲自己的车去送修了,所以高月进入了家福的车中。
(在家福撞见高月与女演员在一起的时候,高月的车追尾了,所以车去送修了。
)从这次开车往后,妻子音的磁带,再也没有在家福的车内响起。
第十一次开车
与上次家福撞破高月与妻子音的私情同样的道具
在酒吧中,家福夸高月表现得还不错,并且阻拦了高月与偷拍路人即将发生的冲突。
这是高月第二次与路人发生冲突,在第三次冲突时,高月会在剧情中”消失“
高月与偷拍路人的第二次冲突被家福阻拦
高月与路人的第三次冲突 第三次冲突时不表结果,作为音的影子的高月,需要在合适的时机”消失“第十二次开车
第十二次开车,家福在车上跟高月讲了他知道妻子音与不同的人出轨的事情,承认了他曾经目睹过妻子出轨的事实,家福第一次真正的面对了过去的伤痛,讲了出来。
高月告诉了家福前世是七鳃鳗的女孩的故事的后半段。
在故事的讲述之后,高月像代表妻子音说话一样,告诉家福”忠于自己的内心,正视并深刻的看待自己。
至此,高月的“任务”完成,他(作为妻子音的代表)也该离场了。
在这场结束时,给了一个像是永别般的镜头。
一个汽车的后窗视角,摇摇晃晃中,高月的身影渐渐变小,渐渐远去,象征家福也在跟过去的伤痛慢慢的告别。
在此后的排练中,高月因前面所说的第三次与偷拍路人的冲突,打人并且致死,被警察带走。
高月被警察带走之前向家福深鞠一躬
家福这次坐在了副驾驶上面
第十三次开车
在第十三次开车时,家福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面,不再仅仅只是把渡利当做是一个司机(在此前家福坐副驾驶是妻子音开车的时候)家福可以让渡利在车里抽烟,并且二人一起点了烟,手举过天窗并排在一起,两颗孤独的心也并在了一起。
家福真正的接纳了渡利。
因为高月被警察抓走,家福不得不面临着要么取消演出要么自己去演万尼亚舅舅的选择,但家福并不想取消演出,于是便跟渡利一起到了渡利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进行了又一次的“疗愈之旅”。
在路途一开始的时候,车辆不断不断的经过隧道。
第十四次开车
在最后一个隧道之前,家福“承认”说,他杀死了他的妻子,因为他的晚归,所以造成了妻子的死亡。
渡利说,她也杀死了她的母亲,因为山洪的时候,她逃出来之后没有替母亲呼救。
渡利讲自己脸上的伤疤就是那次事故造成的,但她并不想抹去。
(对应片尾处,渡利摘下口罩,脸上没有伤疤。
)家福说他如果是渡利的父亲,他会抱着渡利的肩膀说,“这不是你的错”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家福对自己说的,妻子的死并不是他的错,女儿的死也不是他的错。
相比之前渡利和家福对谈身世,这里更进了一层也更深了一层,当谈话挖到最深的时候,人物的成长也就完成了。
经过隧道只有,二人坐了渡轮,第十五次开车来到了渡利长大的地方,白雪茫茫一片,这里片中进行了消音的处理。
白茫茫的一片大雪什么都盖住了,连声音也没有了,两个角色的过往苦痛也可以被“盖住”的。
第十五次开车
在这里,渡利也真正的同曾经带给她伤痛的母亲告别了。
家福拉渡利上来,渡利真正的道破了所谓真相,家福所说的关于妻子的一切是真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把妻子音想的如此神秘呢,想简单一点会很难吗。
家福像个孩子一样在渡利面前终于承认了他对音的思念,他想要音活着,想要跟她聊一聊,想要跟她大喊大叫,但是已经晚了。
那些一直思考着死亡的幸存者,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你和我一定要这样,活下去。
这里点题,放下伤痛是一种成长,背负着过去的伤痛继续这样活下去也同样光荣和伟大。
雪地里的一束光照亮了小汽车在这场戏中,二人在剧情上的成长已经完成了,家福面对了妻子出轨,妻子去世,妻子可能没有他想的那么神秘,或者说妻子没有那么爱他的事实。
渡利也与母亲(幸)告别了,在此之前,男演员高月也用自己的行动向家福所谓“赎罪”了(赎罪这个词适当理解吧,大概这个意思,但说赎罪似乎重了一些)那此后需要用一些场景来印证剧中人物确实完成了蜕变和成长,就是之前的,家福的车、磁带的声音、能不能顺利的上台演出万尼亚舅舅,以及渡利脸上的伤疤。
在之前第十一次开车的时候,也就是家福与高月第二次酒吧谈话时,汽车里的磁带声音再也么有响起过。
家福在哑女小姐姐的环抱中,完成了万尼亚舅舅的演出。
最后的台词依旧在点题,活下去。
渡利与狗的第三次“接触”渡利抹掉了脸上的伤疤,开着家福的车,带着一条狗,在韩国,脸上带着坚定的,活下去。
并且此时家福并未在车中出现,片中也并没有表家福到底是因为跟渡利在一起了所以渡利在开车还是因为把车送给了渡利。
但根据电影的文本猜测,应该是家福把车送给了渡利。
在之前的剧情中,家福不再听那个磁带了,也让位了车的驾驶权,并且完成了万尼亚舅舅的演出,那么最重要的道具也就是汽车也应该给出去,才能真正的完成“成长”。
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在垃圾场那场戏中,渡利曾经说过自己的车在广岛坏掉了,所以她开始驾驶那些垃圾车,开车时她唯一会做的事情。
9 ) 声音的多重奏 ——分析滨口龙介电影的声音景观
滨口龙介作为近年来日本影坛的杰出代表,先后凭借2021年的《偶然与想象》,《驾驶我的车》和2023年的《邪恶不存在》横扫欧洲三大电影节和奥斯卡等权威的电影奖项,他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通过观看滨口龙介三部获奖作品以及其余作品,可以发现滨口龙介电影中声音通常作为一种游离于画面外的元素存在,不单是处于一种抒情或确立影片基调的作用,而是作为具有导向多义性和情感厚度的主导性力量存在,可以说是与影像平起平坐,甚至超出的表意性的关键存在。
一、日常话语在电影中的抵达1.电影声音的起源在1927年以前,电影中的“声音”多是以现场乐队演出的背景音乐为主,其作用也往往被局限在为影片特定桥段表抒情作用而存在。
然而,随着1927年10月6日,《爵士歌王》中艾尔·乔森开口说了话:“等一下,你们还什么也没听到呢。
”这句话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在声音通过同期录音以及后期录音的技术得以收录后,声音作为一种扩展视听感知和情绪导向的技术应用让电影制作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早期影片对声音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成为编剧写台词、演员说台词、摄影机拍台词的一条由声音贯穿的线性模式。
声音重复影像的方式遭到了一些理论家的诟病,如爱因汉姆(Rudolf Arnheim)便认为声音的出现会抹杀电影作为艺术的独特性。
他的《新拉奥孔:艺术的组成部分与有声电影》(“A New Laocoon:Artistic Composites and the Talking Film”,1938)从莱辛《拉奥孔》的思路出发,就“对话缩小了电影的世界”与“对话使视觉动作瘫痪”两个观点对电影声音展开了批判。
因此早期声音的运用仍然不能摆脱对于画面的关联,对话和环境音效等有赖于声音使用的应用并无美学和突破性的造诣。
2.电影声音的多义性随着罗伯特·布列松在《死囚越狱》对巴拉兹的文章《电影理论:声音》(“Theory of the Film: Sound ”,1930)探讨了声音中噪声、静默、空间、亲切感、视听关系等问题的回应,有声电影的声音表现开始趋于多样性与多义性,电影声音与画面的关系也从附属性转至独立表意的单独存在。
在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的文章《电影中的声音:身体与空间的衔接》(“The Voice in the Cinema: The Articulation of body and Space”,1980)提出声音拥有一个“幻想的身体”,探讨了电影与声音幻想的身体之间的关联性,为声音界定了一个存在于视觉感官层面,独立于听觉空间的意识,跳脱于画面当下的立意游离在观看于被观看双方的间隙。
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像下,安东尼奥尼与费里尼铸造着纯视听情境;法国新浪潮下,戈达尔在《法外之徒》创造了“静默一分钟”大胆抽掉音轨,用这样的恶作剧,拒斥着好莱坞电影对于声音的驯化,暴露出电影自身的材料属性;黑泽清在《东京奏鸣曲》对于日常声音体系的异质化挪用,创造幽灵的质感。
对声音的认识已然进入新的研究方向——寻求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摆脱对影像理论的完全依附。
电影声音不是影像的附属产物,而在电影诞生时便自然存在,这也是电影声音理论现代化的演化方向。
因此寻求电影中的多义性以区别与画面内容的强制关联性是需要被重视的。
3.日常与即兴的声音在开始探讨滨口龙介电影中的声音前,先从电影史上寻找滨口龙介电影“日常话语”是如何建构而来的。
对于声音的本真还原与纯记录伴随着电影制作的一般化,即走出人为设计的摄影棚(好莱坞大片场),这一创作方法严谨系统的应该发源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发展于法国新浪潮运动,复兴在“道格玛95”。
对于“真实电影”的追求是全球文化范围内数位电影人所追求的状态,而声音作为一部分也被视为真实所必不可少的元素,而真实所指即是摄像机对日常状态不加修饰的捕捉。
在了解这一思维创作模式下,以下试着列举对滨口龙介对构建“日常话语”影响最为深刻的影人。
日常性很重要的一点来源于对生活随机的记录,在滨口龙介的《偶然与想象》中第三个故事完全发生于日常的随机事件——多年没有谋面的两人再度重逢,最后两人却都认错了人。
这样的随机性在侯麦的许多电影是作为创作的根基而存在,常常是两个素未谋面的人相识,再以日常的对话姿态讲述着多是哲学,文学的形而上的有别于日常话语的内容,在日常性的形式灌注了异质的内容,如巴拉兹所述,观众聆听电影中的声音产生了与聆听生活中的声音不一样的感受。
侯麦无意去塑造一个观众“身边的人”,而是以电影来结构文学,在日常性中倾诉有别于物质属性的对话。
这一点在滨口龙介中人物间亲密却又疏远的人物关系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在滨口的电影里会通过人物大量的对话来保持有机的叙事流程,演员的即兴(音色,声调,节奏,气息)在对话中是影响情绪制造起承转合的关键要素。
而约翰·卡萨维蒂对于长对话以及日常氛围的营造是相当敏感。
他为妻子所写的人物无不以原生浑然天成的契合吉娜·罗兰兹本身,她们游走于不同故事中,却总是同一种桀骜不羁,自由和脆弱:《醉酒的女人》中疯癫的家庭主妇,《首演之夜》中敏感的舞台女伶,《女煞葛洛莉》中离异的女杀手,亦或是《爱的激流》中的孤独的女子她们都或多或少呈现出性格的共性,进而推延至语气音调等声音特质的独属于卡萨维蒂电影中人物的形象,声音的物理属性构成了电影中的有机性和独特性,在卡萨维蒂所制造的氛围下自成一体。
两人互为夫妇的身份为卡萨维蒂提供了人物最贴合的蓝本,在相互成就下抵达日常的捕捉,滨口龙介在《欢乐时光》中从演员工作坊汲取的灵感,从而选用四位年近40岁的女性素人,展开长达五个月拍摄训练以求抵达日常的却不同于科班的表演(卡萨维蒂最初筹备《面孔》也是在纽约大学教授表演课后有感创作),相信滨口对于即兴的“声韵”也是在对偶像卡萨维蒂名言的实践——我不执导电影,我只设置好一种氛围,让氛围去主导电影。
其他对于滨口影像风格影响的导演有杨德昌,成濑巳喜男,黑泽清及小津安二郎等等碍于篇幅就不加以展开介绍。
二、聆听与讲述:再造电影声景 保罗•帕索里尼在《诗的电影》当中初次直白地提出了“电影的本质是诗性的”他在文章中提到,电影必须要回到它最为原始的叙事方式,以解放电影叙事除传统的叙事程式之外的表达可能性。
滨口龙介通过构建连续时空的长对白,以此将文本与画面中人物的形态,外貌,声调相结合,将对白视觉化的同时观众延展了可视化的想象空间。
以一种轻盈的技巧发掘潜在的情感厚度。
1.聆听:话语的可视化 师从黑泽清的滨口龙介曾记得老师说,导演只是决定了摄影机该放在哪里,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对此他并无深刻见解,直到日本“311大地震”滨口与酒井耕在2011年-2013年分别创作了《海浪之音》,《海浪之声》和《讲故事的人》三部纪录片,在倾听大量的,冗余的劫后余生人们的话语,他开始对语言产生难以割舍的迷思,每个人不同的讲述方式都是节奏的视觉化,形成了诗一般的连绵。
因此,聆听成为滨口龙介电影的一种常态,《欢乐时光》四人面对摄像机吐露相互间的真情;《驾驶我的车》司机渡利倾听舞台剧演员家福的“车内排演”;《偶然与想象》每段故事开始前直接将“聆听”这一动作交由观众,进行直白的旁白阐述。
2.讲述:可感知的声景 1967年法国学者居伊德波提出“景观社会”并将景观从地质环境推向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强调了被凝视的产物以及由人凝视后感官所产生的主体意识,“景观”由此成为一种含有个体审美内涵和涵盖观看过程整体的感官体验。
“声音景观”便是发展演化下的产物,挖掘声音在空间性,人文性,景观化是导演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指引。
滨口龙介对声音意识的敏锐感知,形塑的声音景观构建了独特的听觉文化场。
《夜以继日》中亮平和麦的扮演者东出昌大曾在采访中说:“我们提前进组主要进行的就是‘朗读剧本’,不带任何感情,没有抑扬顿挫,没有声音变化,去除所有有意识的设计,就只是在那里一遍又一遍的朗读台词。
大概反复进行了好几百遍。
这多于我来说相当困难,因为我总是喜欢胡思乱想一些东西。
比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其实读得都一样,但是导演一会说,‘你这次还是带感情了’,一会儿说‘刚刚这遍声音还不错’。
”深受让·雷诺阿的“意大利的彩排”影响的滨口认为,演员只有通过这样的练习,像复读机般不假思索地说出台词,才能抹除先入为主的观念与说明性的动机,从而抵达无意识的场域。
同时,滨口将这样的练习直白的在《驾驶我的车中》向观众传授,使用日语,韩语,汉语,菲律宾语,韩国手势的演员们照着各自语种版本的《万尼亚舅舅》排练,并且要求倾听并不熟悉的语言然后按照各自的语种对戏。
通过消除语言间表意的不准确,还原到叙事意义前的层次,于是,在影片的最后失语者李允儿用手语,摩擦与击打着自己的胸脯、手掌与身体增添了一种作为物质的声音的维度。
在《欢乐时光》中作家不加语气的平淡的朗读自己所写的散记,也为声音提供了想象的维度。
最近的《邪恶不存在》滨口更实验性的将声音生硬的和画面切割开来,彻底抹除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说明性的动机,力求声音的纯净。
让·雷诺阿在《黄金马车》中将戏剧搬上电影,在戏中戏中找寻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滨口龙介在《激情》、《偶然与想象》、《夜以继日》等等作品中强调与构建着戏剧舞台,在这样的舞台上形成聚集声音的场域,声音成为可感知的景观,源源不断在戏内外同观众交融。
三、结语电影声音理论与声音景观的有机融合是对于电影研究与创作的突出方向,滨口龙介的多部电影成为其研究的有效范本,对电影声音的挖掘与创新是重要的实践举证。
滨口龙介电影中的声音景观将声音从意义的附属品当中解放,从社会,文本,时代和观众间给予心理层面的美学观照,为情感与记忆获得一份真实的厚度。
10 ) 当我们谈论开你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 ドライブ・マイ・カー》这种看起来像是悼亡、亦或走出的电影,总因为车的广延与路的伸展,看起来叙述的是某种认识的转变:被动的转变、主动的转变、甚至无奈的转变、和解的转变......所有一切都源于现实的改变。
基于如此转变中所蕴含的现实意义,《 ドライブ・マイ・カー》或许也可以归结到公路电影,而不仅是因为看似道路和人生没有终点的“开放式”结局。
如此告别所谓过去与走向未来,总结起来,其实是找寻一个终极解释的过程。
如同家福在《等待戈多》对同演所说的台词一样:等戈多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至此,一直以探究亡妻生前留存秘密的家福,在一个已然孤苦一人的追寻旅途中,无非需要的是一段自我发现并建立生活新秩序的历程。
在家福与音的家庭中,女儿亡故后对破碎生活的重新认识,建立在他们本应该转变为父母又被迫退回夫妻的角色的扮演之中,简言之,与生活转变的戏剧性有关系,这种转变的现实看起来只与悼亡与失去有关,而与他们原来的生活无关,也就是说,如果女儿还活着,他们会是幸福但普通的一家而已。
从这个角度出发,当家福体悟实然事实与应然所想间存在着巨大的经验鸿沟之时,自我面对与自我发现毫无疑问必然重合,近结尾处互相拥抱的家福与渡利则必然充满悔恨与但又可以放下执念。
悔恨不在于曾经爱过而现在不爱,而在于自我发现:他以为为爱的自我牺牲,在一个被爱之人看来成为了悖论,即面对一个你也爱之人,你怎么会希望对方牺牲自我,而对方如果不自我牺牲,你又看不到对方爱你的证明。
因此作为鳏夫的家福一直不能放下作为亡妻音留下的“秘密”,其间最大的悲哀,既是渡利不解母亲为了与她更亲近是真的精神分裂,还是装精神分裂,依旧原意相信那份亲近的爱,是发自母亲的真心,但却在意外发生后,不愿去施救的决绝。
家福由此审视自己,其苦苦追寻的秘密,或许就是生活已然巨变后,自己对待妻子的一系列深思熟虑,其自我发现,直面心内真实后的放手,正是发现爱的{反义词}并不是恨,而是深思熟虑,是不爱。
这种深思熟虑,或许正是滨口龙介作为预备役大师“令人惊叹”的叙事水准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的标志,从《 ドライブ・マイ・カー》的片情设计:家福与音的戏剧工作,甚至做爱、开车、日常对话都时刻与戏剧相伴,演员大部分时间进行着疏离的表演等等各种细节......都能看出滨口把戏剧形式用电影调度搬演到故事中,不断地悬置思绪、悬置情感,已达到延缓其落实的目的。
这在某称程度上,或许可以概括为《 ドライブ・マイ・カー》所谓的作者气质,而愈是深入故事,愈是可以发现故事的展开、收束,都是以面对和发现后的认识为中心,汇聚到一点后,再展开反讽,完成升华,电影虽然于此结束,不过故事依旧可以继续,超越所谓影像世界,直指现实中每个观者,从而延宕出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就像电影中大书特书的戏剧:万尼亚舅舅,看着姐夫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那个他献出自己最好年华服侍一生的偶像,偕着年轻的续弦妻子来到庄园,但他的著作没有一行会流传后世,他无声无息,是一个十足的废物,自己一直信以为真并奉献一生的生活失去了意义,被“毁了”的万尼亚舅舅,在激愤之下向教授开了枪。
于此,为了挽救自己,和面对尼采所批判的虚无主义:这种即便无数安息日的道德点缀也不能掩饰的对人类本身的巨大诋毁。
此情此景中西岛俊秀饰演的家福,发现自己对待亡妻用深思熟虑填满所有本应因缺乏才产生的无爱之爱,重新建立生活超级秩序的终极解释当然就十分合理且必要唯一。
但对于戏剧来说,尤其是电影中的《万尼亚舅舅》与《等待戈多》,其主题中人类精神危机和生活意义缺失的困境所呈现出的面相,却并非是收束到一个核心认识的奇点之上,无可避免地,滨口深思熟虑想要达成的生活新秩序与戏剧调度可能也并不会收束到某个终结解释的自然必然之上,故事与形式间一定会存在着充满维度的张力。
其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正如滨口如果要用{无爱}&{深思熟虑}来与观者进行沟通且建立表达,那就不仅需要有定义的一致,而且还要有判断上的一致。
结局中,家福还是去饰演了万尼亚舅舅,这似乎表示了,对过往放手是一回事,而获得对过往放手的结果则是另外一回事,但实际却并非如此,我们所谓的“放手”,也是由已然放手这个结果中的某种标准的恒常性决定的。
在电影中,家福可以对自己下命令、可以服从自己、可以惩罚和责备自己、可以对自己提问并给与解答、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走出阴影......我们甚至看到了看起来句读排演,但实际上用各自不能直接沟通的语言在进行独白(用各自不相同的语言的词语甚至肢体的动作)的一众演员们,就像自说自话一般的在实际的“自言自语”,观察他们并聆听他们的观者们,也可能成功地将他们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的语言。
生活中,我们也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语言,其所指的他/她的感情、情绪、内在经验、感觉等只有说话的人自己才知道,是他/她的私人感觉,因此除他/她之外的其他人不可能懂得这种语言,而如果这种私有语言是可能的,其最有用之处,大概就是用来表达私有感觉了。
显而易见,即便家福与高槻面对的是同一个爱人的离世,家福与渡利面对是同样至亲的死亡,家福与高槻和渡利的快乐或痛苦也会是非常不同的。
那么词语、动作肢体构成的“词语 ”与 被命名的感情、情绪、内在经验、感觉之间,也就是名称与被命名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是怎么建立的?
这个问题也就是:人是怎么学会名称例如“无爱”一词的意义的?
一种可能性是,词与感觉间原始、自然的表达相联系并且用在了这些地方:妻子在丧女之后频繁出轨,丈夫没有离婚,选择了隐忍,时刻深思熟虑怎样面对自己依恋但失常的妻子;不知道母亲精神的真实状况,面对对自己时好时坏的巨大差别,女儿时常感觉厌恶,但又不愿离开,总是深思熟虑如何面对自己不知所措的母亲.........那么{无爱}这个词实际上指的就是{深思熟虑}吗?
正相反,深思熟虑的言语表达代替了无爱,而不是描述了无爱。
这时只有我知道我是否还有爱,其他人只能猜测这句话,从一个方面来说是错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无意义。
因为我们不能说其他人仅仅从我的行为举止来获知我的感觉的,对于我,并不能说我知道了我的感觉,而是说我就有感觉就已然足够,因为感觉于我就是直接得到的,此时的“知道”是从爱或不爱的环境和外现的公共性推断出来的。
所以深思熟虑,并不是在描述家福和渡利无爱的感觉,而是无爱感觉的一种外在表现。
前文所述大量用戏剧台词融合电影内的现实生活的映射;明显只对银幕前的电影观众有效的排演段落、表演等调度手段,很大程度上故意制造了环境外现和内在感觉的混杂。
所以,“此时此刻,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是否还有爱”这句再明显不过的语法错误表达,只在向别人说明爱或不爱的“意向”一词意义时才会说,“意向”这个词在此时面向一个人自己的时候,这个词极易隐没的内在语法、说话者(隐藏作者)必然被误解的深邃广袤之经验表达才会消失,也只有此时高槻讲述音的完整后续故事给家福听的私有感觉才消失;渡利向家福诉说自己母亲死亡真相的私有感觉才消失;家福一直拒演万尼亚舅舅,拒绝面对虚无诘问的私有感觉才消失......此时此刻,此处的“知道”凸显着意向永远可以被怀疑的无限推演才能休止。
从可以穷尽的有限环境与外现出发,妻子与母亲离世,就是不能逃避的公共外在,人的私有感觉能成立的根本,并不是每个人拥有他/她自己的范本和说辞,而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其他人有的也是这个还是另外的某种东西。
我们用“我无法想象{只有自己知道是否还有爱}的相反情形”,来抵挡私有感觉这样的语法命题,此时语言与感觉间相互联系的自然,是滨口将戏剧形式交给了作者性设计后,契科夫让舞台出离情节,把角色心理交给了观者真实与隐忍的自然必然,也是现代世界中被人们奉若圭臬的自爱自欺欺人的假象破灭后,依旧需要真正的爱、需要亲密关系的必然自然。
相视而行,戏剧处于生活 与 戏剧就是生活般人生如戏的生活形式,没有爱过的人依然可以懂爱,这是爱的知识与爱的经验的区别,不过它们都建基于活着的整体的人。
所谓自我面对于自我发现中的自我,并不提供任何显像、外现和公共性给我们,它们只是语法构造的错误指摘。
而这个世界上,当然有人愧疚,而觉得自己没犯什么错误,都是别人的无情与失责;当然有人觉得抑郁,而觉得没什么原因,甚至觉得是生理的病。
此时产生的语法命题,是愧疚的语法中就包含着错误,是抑郁的语法中就包含着病态,相信问题的特殊,相信问题背后藏有特殊的本质,当然就可以逃避和拒绝一个人的愧疚其实就是犯了错,一个人的抑郁就是有来由的这样的视角。
最难的事,莫过于不自欺。
最终,渡利可以看透家福的疼痛,家福也能明白渡利隐忍的伤口,并不是因为感觉的共通,而是用于描述这种感受、促使互相的理解的途径,在语言中早已存在,是语言外构的共通,是公共性,是总有的另一种可能,是别的视角,是他人。
当人选择不孤独自爱的时候,去追问{爱是什么},我们从不去直接回答它是什么,而都是在回答{爱不是什么},因为自爱的不可经验,只有语法概念不断强化的现实信念,而否定性永不停歇的解蔽,可以给予他人与自己并不严苛的框架与规范,确定爱的确实,如同穿梭于日本这样一个施行左侧通行,都是右舵车的国家中,行于路上的左舵萨博,里面存在一个在车中宛若在生活中上演着和解的舞台独白的确实,在停下来时,车又真的只是一辆车而已,但其中的人和故事,早已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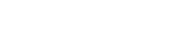














































































































暂时消化不了这个,也没有好好吸收过他的其他作品,按道理来说我是应该喜欢的,滨口龙介,一种有营养但又厚又硬的肉片,为了不伤到牙齿和咽喉无奈整个吐出来了,牙缝里全是文本。
要不是花了整整三小时忍受精英文艺中年直男的miserable shit我也不用谁提醒我要好好活下去不是么。I mean it&#39;s a fine film but it’s also 3 hours I’ll never get back. Saturday would be a lot cooler had I spent that time watching not one but two Jackass movies. Fuck this.
看到滨口这样地误会和错误地使用自己的才华,把多出来的一小时用来彻底地抹消前两小时的静谧和美妙,这痛心和无语的感觉能类比看杜琪峰拍献礼片
救命啊!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感受不到这部电影的魅力,任何一场都没有。为了这部电影,我还专门挑了周六一大早来看,我还准备了热红茶,冰淇淋蛋糕,披着大厚毛毯在沙发上蜷缩着,结果看到我发呆放空,几度电视屏幕上反射着我在沙发吃蛋糕的画面,电影里还说着:“我们要活下去”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一切都太疯了。
假如一切都可以用文本解决,那还要电影干什么?文本和构思再巧妙,也掩盖不了对影像表现力的忽视和对文本哲思贪恋般地滥用。
村上的小说骨架很小,被生生塞成了一个大胖子,浑身都是赘肉。所谓的“世界性”就是把到处收集来的纪念品堆积陈列,从这一点上来说,导演也算得到了村上的真传。不过村上还是比他真诚多了。或者说,目的性再强的文学,也比目的性的强的电影要真挚一些。
已阅
似乎就是一双极度自我束缚之人的互舔疗伤之遇,拖沓又余泄滞。
7/10。多语表演和非常肢体化的手语拍摄进行得如此顺畅,可见演员的感情领悟力都很强。滨口龙介将听的力量置于人物心结的联结与解开,特别是家福反复听妻子念的车内录音来背台词、排演时聚在一起读本,以达成契科夫戏剧与电影人物关系的互动:从镜子映出妻子背叛的性愉悦时家福没有表情,他认为车是私密空间,不允许妻子之外的女人坐驾驶座为他掌握方向,但接受了与死去女儿同岁的司机渡利,近结束时两人驾驶着车前往白雪覆盖的灾变地区,都用手点着烟祭奠,对家福而言妻子的出轨和对渡利而言母亲的暴力,都不过是肉体上的死后就成了灰烬,继续活着总会有新的希望,这种毁灭与新生的情感历史也是拍摄地选广岛的原因。导演直接引用了《万尼亚舅舅》里万尼亚开枪未射中教授后自杀未遂、善良的索尼娅指引他克服痛苦的戏,很好地补充了家福和渡利的人生方向。
满意!可能因为最近看的新片都一个比一个看不下去,这部三个小时结束我甚至感到再来俩小时也行,所以这个五星今天依旧是相对评分。添加的做爱讲故事桥段实在太村上了,导致我回忆半天是不是哪个短篇里用过这个;重新整理和强化了契诃夫与原作故事的关联,这一部分也特别巧妙,尤其最后将索尼娅的名句用手语面向观众表演出来,我恨不得当场起立大喊“妙哉!”。我并不觉得滨口的时长、大量利用戏剧空间与戏剧张力以及大段对话哪里冗余,但本片确实有冗余的部分,那就是突然开车去北海道,那段的添加似乎意味着戏剧内部的closure是不够的,对家福和渡利来说他们都还需要一个物理意义上的closure。
无意义,矫揉造作的片子
3小时候的观影成本太高了,唯一亮点:台湾人衣服上醒目的美国国旗
岛国娄烨,一堆惺惺作态。
西岛俊秀和冈田将生在车后座那段对话真好啊。起初西岛说了一堆丈夫胸襟话,冈田不时短短回应一点情夫挑衅话。而且,两人的表达方式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你已经在屏幕前不自觉瘪嘴蹙眉了,可又不知道从哪时开始,冈田直接地讨论起两人之间那位离世的女人——她在性高潮边缘口述的创作。西岛:这个故事我听过,结尾是…… 冈田:不,故事结束的地方不在这里,而是……当冈田讲完他所听到的结局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们的沟通在第三人身上完成了嵌合。电影延展了不少小说中没有的内容,很多细节相当不错,要一一去谈得讲好久好久。
A / 从第一个镜头起就不断抛出同一个疑问:声音从哪来?若看不到嘴唇蠕动,它是否就来自黑暗,或是那之外的虚空?如有肉体证明它在场,是否可以压抑音调、排除它从而直面文本?又或者声音预先丈量好时间,继而在高度贴合的轴线上将自己抹平?这一切幻想都在那个磁带与车轮的叠化之后被一一拆解。正如一种声音构成了一具身体的轮廓,鲜红的车体也成为镜头无法闪避的“自我”的躯壳;而当声音不断地死亡、被清扫又不断地回返,车也在穿行于绵延的隧洞时逐渐地生成一种具身且“非人”的目光,从而包容了那声音不止息的溢出——在这之中,我们回到了《偶然与想象》第三段的启示:眼泪的真实可以来自药水滑落一瞬间的惊悚,情感的真实同样并不依靠单一的起源——而滨口龙介自己,在概念的游戏中,再度赋予这些标记着语词的人物以超越概念的负重。
即使是三重文本,也实在太无聊了太无聊了
四星半。当婚姻关系中出现了第三者,丈夫究竟是该追究对错,还是默不作声放任自流。滨口龙介给出了独特的设问,“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已知,哪个更难解答”。由始至终反复出现的戏剧台词、舞台形式和角色的情绪嵌合在一起,抽丝剥茧式地探索男主角心中的迷惘,而这样的过程悄然间也给了一路陪伴的女司机对过往困苦的解惑。整部影片的结构又恰如多幕戏剧,时而晦涩,时而通透,充满着戏剧本身的独特魅力。若能适当压缩篇幅,观影效果会更加舒适。
说实话…我觉得并不怎么样…
今天想明白我不喜欢滨口的原因是他不会留白。能用故事表达的东西非要用台词讲,也是一种Japaneseness。即使如此,这部也是好的。
放佛在看一场黄瓜如何蔫儿掉的影像记录,不管体验能否成为体现,这都是一场汤里加汤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