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亚·佩雷斯》剧情介绍
丽塔是一位资历很高但总被低估的律师。她工作的事务所更感兴趣的是让罪犯摆脱困境,而不是将他们绳之以法。 有一天,她得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出路。毒枭头目马尼塔斯雇佣她来帮他金盆洗手,并实现他多年来秘密准备的计划:像他一直梦想的那样,成为一个女人。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蓝色监狱深海大鱼残雪飞歌如获至宝期末考一路向前报告老师我是东北银金子轻松出来吧灵魂刺杀令加德满都,天空之镜心碎的感觉林中女妖军民大生产凶男寡女煽疯点火母女情深晚酌的流派4~夏篇~维琴河第一季你燃烧了我橙花盛开半城SPECサーガ黎明篇『Knockin’on冷泉’sSPECDoor』~絶対預言者冷泉俊明が守りたかった幸福の欠片匆匆心动我不是酒神张震讲故事你永远比那些家伙年轻不翼而飞黑手党战争PendingTrain-8点23分,明天和你造梦师
《艾米莉亚·佩雷斯》长篇影评
1 ) 男人负责制造混乱 女人在收拾烂摊子
我看到很多人在吐槽歌舞片的那些情节,觉得混乱,可这恰恰就是墨西哥当时的现象最本质的体现。
在混乱中,每个人都想寻找秩序,比如跑调的歌曲,错乱的步伐。
但是大家请看歌词,在反馈主角内心的变化以及每个人都在挣扎的过程中,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以及是我判断此片是一个非常不错影片的有利基础。
其次讲变性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噱头,可是这就是主角内心最真挚的体现,他一直是有两面,一面负责制造混乱,强权独裁杀戮,可他女性的一面,让他最终走向了救赎的道路。
这是人性光辉,也是勇敢的表现。
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因为司法的缺席、腐败导致最后的结局—就正如律师为了救艾美利亚还是让人带上的武器奔赴的现场。
这也是在暗示女人想拯救这个世界是不行的,那些制造混乱的男人才应该醒过来。
回顾全片最可怜的就是两个孩子。
从毒枭大本营到瑞士再回墨西哥,他们的人生和里面的每一位都是一样的—被时代推着走、无法自我选择,挣扎与痛苦。
2 ) 一部四章节的女人史诗
戛纳电影节以最佳女演员四黄蛋形式创世纪,借“毒王女人梦”的奇情故事,注脚波伏娃“女人是后天形成的”的电影主旨,以四个女人在艾米莉亚·佩雷斯身上的性别流动,开启一部波澜壮阔的女人史诗。
毒枭马尼塔斯是艾米莉亚身体的宿主,电影即是他的变性故事,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逃避警察和仇人,而是他从小就自我认定为女人,却不得不扮演男人,文身、镶金牙、比猪圈里的混蛋更加混蛋,最终登顶父权制下男性极权的塔尖——黑帮老大。
变成女性,是现实世界的权力倒置,身体身份的改变也改变地位站位,从男权的顶端跌至女性的社会底层,她才能从这个视角开始正视墨西哥社会广泛存在但却无人发声的人口失踪现象。
丽塔艾米莉亚的“护法”,她是一名律师,熟稔、拿捏并操纵了男权社会的穿行规则,让艾米莉亚成为现实。
她几乎是一个没有性别的人,参与了制造艾米莉亚的全程,也能在艾米莉亚毁灭后,承继母职。
杰西是艾米莉亚的前妻和灵魂的终极救赎,她是片中男凝的女人味担当,永远玲珑曼妙,永远弱小无助,却在片尾以最暴戾的方式与男权玉石俱焚。
埃皮法尼亚是艾米莉亚的爱情。
代表着女性的现实,长期被家暴,丈夫遭黑帮暴力劫杀失踪的五年是生命赠与的一段最宁静的时光,她寻亲的目的只是为了坐实丈夫的死讯。
脱离了男权的她如获大赦,立即投入女性的温存。
这是阿莫多瓦化的雅克·欧迪亚:阴阳倒错、性别暴力、怪诞奇情、虐恋撕扯、血浆浓艳如花。
(016)
3 ) 太商标能扯了
编剧脑子是被河间神兽踢了吗?
硬生生为了蹭变性的醋,包了这么一锅不伦不类的饺子。
穿插一堆乱七八糟的歌舞,音乐难听又混乱,歌词押不上韵就强行改成念白,完全不挨着,别说跟La La Land,芝加哥比了,就连蹭“因果报应”的三哥弱智歌舞片Maharja都比不了。
评价只有四个字“什么玩意儿”!
儿化音是免费赠送的,不谢。
4 ) 《艾米莉亚·佩雷斯》短评
一个渴望变性的大毒枭和一个善于帮助罪犯脱罪的律师携手合作,共同演绎了这部带有浪漫主义成人童话色彩的犯罪惊悚歌舞片,已经结婚生子的大毒枭在律师的帮助下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性别,实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梦想,然后金盆洗手,弃恶从善,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死于非命的结局(既可以说是因为自己对原来的妻儿的牵挂而死,也可以说是因为自己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而死),“毒王女人梦”这个译名可以很好地传达这部电影的精髓。
作为一部以跨性别者为主角并且涉及犯罪的电影,本片的题材看似有着比较大的尺度,但是具体的故事内容的尺度其实并不大,故事的核心主题则是对跨性别者的生理性别、心理性别、社会身份的探讨。
不过,这种故事完全没有必要拍成歌舞片,歌舞元素反而成为了本片的累赘,本片中的舞蹈真的很难看,那几段半说半唱的台词也很出戏。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艾米莉亚·佩雷斯的女演员卡拉·索菲娅·加斯科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就跨性别者的身份而言,艾米莉亚·佩雷斯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她在本片中的表演也算是本色出演了。
5 ) Quite enjoyable to watch
Quite enjoyable for me. Cinematic scenes, colours, drum beats and music. So, it is true. I am a musical fan About what many people are criticising about, the unrealistic plots. Doesn’t bother much, as I just can’t be too serious with the film. I mean, come on, it’s talking about a cartel boss transitioning into a woman?! Why so seriousOh, forgot to mention. I figure out why our so-called “Radical Left” always said LGBTQ+ stick together. Can resonate her pain, sometime.
6 ) 关于真实和虚幻
一、跨性别演员的选角与争议 卡拉·索菲娅·加斯科恩的“本色出演”饰演毒枭变性为艾米莉亚的演员卡拉·索菲娅·加斯科恩(Karla Sofía Gascón)本人是跨性别女性。
她此前以男性身份(原名Carlos Gascón)活跃于西班牙和墨西哥影坛,并与妻子育有一女。
她的个人经历与角色高度重合,成为戛纳电影节首位跨性别影后。
争议点:尽管表演受认可,她因未完成生殖器手术且法律性别仍为男性,获奖后引发舆论质疑。
此外,其过往涉及种族歧视、宗教歧视的争议言论被曝光,导致剧组与其切割。
“四黄蛋影后”的特殊安排戛纳电影节将最佳女演员奖同时颁给四位主演(卡拉、佐伊·索尔达娜、赛琳娜·戈麦斯、阿德里安娜·帕兹),理由是“共同构成女性情谊的完整叙事”。
但实际戏份分配不均,配角阿德里安娜仅出场几分钟,被质疑是政治正确妥协。
二、文化真实性与口音争议 “非墨西哥制造”的墨西哥故事尽管剧情设定在墨西哥,影片全程于法国巴黎郊外摄影棚拍摄。
导演雅克·欧迪亚(Jacques Audiard)承认对墨西哥文化仅基于刻板印象创作,例如毒枭、仙人掌和亡灵节符号化呈现。
声音团队不得不通过音效库模拟墨西哥城市场景,被批评缺乏真实临场感。
语言与口音问题 赛琳娜·戈麦斯:因西班牙语不流利,其角色设定被改为“美籍墨西哥裔”,台词经多次调整仍显生硬。
佐伊·索尔达娜:多米尼加裔背景的西班牙语口音被墨西哥观众认为“不够地道”。
导演的语言障碍:欧迪亚本人不会西班牙语,剧本由法语撰写后翻译,导致演员对白呈现“法式西语”风格。
三、歌舞元素的挑战与突破 佐伊·索尔达娜的舞蹈回归佐伊为饰演律师丽塔,时隔20年重拾舞蹈功底。
片中长达57分钟的歌舞段落需平衡演唱、舞蹈与表演,被《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盛赞为“职业生涯最大突破”。
音乐与叙事的融合实验声音团队创新采用“说唱结合”(parlé-chanté)技术,模糊对白与歌曲的界限。
例如用卡车引擎声增强节奏感,或将市场环境音与多普勒效应结合,营造虚实交织的魔幻氛围。
四、导演的创作争议 类型化叙事与议题拼贴影片融合犯罪、家庭伦理、性别认同、歌舞等元素,但被批评对社会议题(如墨西哥失踪案、跨性别群体困境)的探讨流于表面。
例如艾米莉亚成立慈善组织的剧情被指“圣化跨性别者”,与现实中的暴力边缘化形成反差。
棚拍决策的利弊导演坚持棚拍以强化“歌剧式宏大感”,却牺牲了墨西哥本土文化细节的真实性。
例如搭建的市场场景依赖音效库合成,被墨西哥观众嘲讽为“法式墨西哥”。
《艾米莉亚·佩雷斯》的拍摄花絮揭示了艺术创作在跨文化、跨性别议题上的复杂挑战。
从选角争议到文化真实性质疑,影片的场外风波甚至比剧情更具戏剧性,成为观察当代电影政治正确与艺术价值博弈的典型案例。
7 ) 艺术呈现与现实议题,“电影”的秀肌肉之作
在今年的奥斯卡提名名单中,《艾米莉亚佩雷斯》得到了近乎压倒性的数量优势。
从根本上说,这代表了奥斯卡对“电影”作为艺术形式,其在直观、沉浸、感性之表意独特性的一种强调,也是面对短视频时代的“秀肌肉”。
本作以音乐歌舞片的类型入手,雅克欧迪亚精细而完美地营造着每一个段落的氛围,在现实与歌舞之间切换,前者的现实主义、后者的美好舞台,都得到了极致的拉满,深度地作用于观众对两种风格的感官体验,在声画角度上做到了高完成度。
同时,他又给出了非常“短视频”式的奇情故事,作为引子的女律师处理杀妻案,作为主要事件的女律师帮男毒枭变性,从手术开始,到男毒枭重入社会,都非常地奇情而吸引眼球,具有十足的短视频时代特征,依靠大尺度+脱离生活的强“传奇”,迅速引发观众的好奇心。
并且,每一个小节点都会用地名进行标记,更是将影片分为了短视频长度的数分钟一“独立段落”,且完成音乐与现实主义的切换,由此让本片成为了短视频的大串联,但又远胜于此,不同的小段落对应着主题呈现的不同阶段,且由演唱、剧情等层面的内容设计,引导着将阶段的递进,逐步完成核心主题的拆解、推导过程,也带着人物逐步走出层层堆叠、深入的困境,迎来最终的“女性崛起之自我认知的胜利”,破除既有环境---从外部客观到内化心境--的诸多干扰,完全接受作为女性而强大的自我。
由此一来,雅克欧迪亚就将“短视频”做成了更具有连贯性的作品,而非单纯的平行关系串烧。
这正是他对于短视频的秀肌肉,展示了电影的能量,能够做出全面升级、声画与戏剧艺术完美结合、且高度调用声画层面而具有直观感受性的“短视频终极形态”,在你的基础之上,利用你的打法逻辑,依靠电影艺术的魅力,最终全面超越你。
雅克欧迪亚将焦点放在了女性主义之上。
女性身处在既有环境的规则之中,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社会的男尊女卑之观念,一方面则更加深度,是女性在争夺性别地位、在环境中争取胜利之中的认知困境。
她们会在不知不觉间停留在“基于既有环境之规则”的桎梏之中,从而让自己无法真正超脱出去,继续受到既有的束缚,而既有的本质规则即是由男性主导,由此让女性注定无法超出后者的高位,在对方的“BGM”中去试图契合、扭转颓势,也就注定了失败,承受对方基于资源分配、物质力量(从肉体力量到掌握权财)等客观层面的强势。
作品的世界围绕着“男尊女卑”这一客观存在的既有理念而运行,让女性处在先天的巨大劣势之中,不平等的待遇与分配导致了注定的弱小。
因此,当女性的追求目标围绕着“当下规则”之时,就注定无法实现“性别平等”这一心灵与情感维度的目标,获得真正想要的尊严,而非“客观社会中的物质地位”---这也是女性主义往往被误解与诟病的点,似乎只是利欲熏心与追名逐利---反而会遭遇心灵的挫败感。
只有完全脱离既有环境,让自己从“争取物质、资源、名利地位”这一“既有客观环境之丑恶本质”的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但这永远不会落实在现实之中,唯一的现实只有当下,带着难以摆脱的“男性色彩”,女性想要迎来拯救,就必然需要巨大的创伤,甚至停留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情境,寄托于虚无缥缈的“上帝”。
女性同时面对着内外的困境,束缚于双重的“既有环境”,其心灵与情感受到压抑与挫败,又在努力争取的时候得以爆发。
人物之于音乐歌舞环境的进出,歌舞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对立,在切换之间的精巧过渡,过渡的“无伴奏演唱”承载的寓意,正是主要的表现形式。
它也与戏剧层面的递进相结合,加持了人物在不同阶段的认知受挫,在受挫---爆发而解决---下---下一环的更深度受挫---再爆发而解决之中不断推进,让困境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借助人物与音乐环境---内心的极致正面世界---的微妙交互、融入程度之变化,推动她们对愈发深化的困境的沉浸、脱离、再沉浸入下一困境、再脱离,在其中甚至还有着微妙的“认知偏差、自以为沉浸成功而误解”的部分。
音乐歌舞片的主要载体,当然是“演唱”。
在第一组镜头中,雅克欧迪亚就展示了演唱的寓意,以及其在既有环境中的状态,作为女性人物所面临的核心困境。
几个男人在演唱,声音却是女性,这意味着男性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他们借助了女性的歌喉,作为自己对外展示、站上舞台、取得成功的资本。
相应地,女性的地位也随之出现,在城市的“定场”远景之中,影片切到了这一标准手法的现实主义风格,女性演唱的声音仍在,镜头的下移为之做出了定性,即“阶层与社会地位的向下”,落在了底层人的废物回收车之上,现实社会里的女性阶层之低下,从性别延伸到了物质财富的层面,后者是既有社会里的资源分配结果,对应到性别便是“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正如同“利用歌喉”所体现的那样,借助女性的力量,在男尊女卑的既有规则中获利,自己拿走了本应属于女性的分配资源,又用其力量反过来进一步维系性别层面的压制性,用话语权去继续巩固性别优势。
“音乐”同样是对此的表现形式,从最开始的美妙旋律被“扭曲”成了收废品喇叭里的普通声音。
戏剧层面的内容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贴合、交互关系。
女律师正是“被剥夺、利用歌喉”的存在。
她出现在了收废品声音环绕的环境之中,由此成为了既有环境里的一员。
这是影片的第一个小段落,由地名进行标记,困境来自于外部规则的“男尊女卑”。
在第一场戏中,非音乐的现实主义风格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摇晃的手持镜头,冷光为主的自然光线,以几个对细节的特写镜头作为情节设定的交代,环境音取代音乐伴奏,一切都非常地标准,且构成了歌舞片的反面。
这一小段落的剧情其实非常简单,是第一个“外部困境”的呈现。
女律师处理着丈夫杀妻的案件,她被男律师告知要处理成自杀,非常不满,却又在男律师的高位权力面前无可奈何,只能听从,并在法庭上甚至要给不成器的男律师打下手,将自己写的辩护词提示给他,而站在台前取胜的名誉却都让给了男方。
雅克欧迪亚的重点不是剧情,不是《坠落的审判》那样的法庭内容,从案件真相到开庭辩护的内容都短而糙,重点是这一“全方位男尊女卑”的简单情节与“音乐歌舞”的交互设计。
在现实主义的段落之中,女律师书写着听从男律师吩咐的辩护词,文字在特写镜头中得到了强调,正是“演唱”的反面,即“无旋律性的干唱念白”,在全片中作为“心境抒发被扭曲”的表现形式,而女律师也给出了“演唱”本身在现实环境中的扭曲形态:先是在房间中边写字边念诵,随后场景变化,瘙痒的脚部特写引出了日常生活化的氛围,她在超市里边复读辩护词边购物,作为现实主义风格的延续。
随后,现实主义与音乐环境开始交互、变化,女主角走出了超市,对辩护词的语气愈发愤怒,是对其“既有规则产物”的主观反抗情绪,并随之引发了环境的变化---情绪的激烈导致音调的起伏,随之逐渐变成了抒发内心反抗的演唱,贴合上了音乐伴奏,她也步入了群体歌舞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这发生在现实的街头,由此形成了对“既有现实环境”的不满与改变意愿,但也意味着她之于此环境的并未脱离,随之出现了现实场景与之的并立。
在“你要杯咖啡吗”的日常生活问话之中,她继续敲打着男律师命令的辩护词,服从着既有现实里的性别弱势,而同步的歌舞“愤怒”则没有真正取代这一切。
雅克欧迪亚迅速地给出了这一阶段的结果,再一次的脚部特写将环境再次带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庭审环境之中,女律师默念辩护词,台面上的男律师则与她同步,甚至要让她来提醒内容,对应着序幕中的“男性借用女性歌喉”,是其象征性表意在现实层面的具体形式。
他光鲜亮丽地利用了她的“声音”与文字、工作努力的成果,完成了开脱男杀人犯这一性别优势结果的判决胜利。
场景画面中的灯光设计同样重要,男女律师共处于媒体环绕的走廊之中,女律师身后的男方在镜头前侃侃而谈,高度明亮的打光与女律师周围的暗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光的操作显然非常细致。
在这一段中,戏剧层面的“简单符号式”得到了表现。
女律师对同性要了卫生巾,离开男律师接受采访的“男强”环境,去到“属于女性”---特写镜头里的女标识的厕所世界,意味着她在职位、性别等现实层面里的“下层”,在昏暗的光线中处理着生理问题。
月经是女性在肉体层面的生理“困境”,即客观维度的“劣势不可解”,形成了既有环境的困境之深,从女性物质肉体的“自我”出发,根本地定义了“男尊女卑”的客观物质层面现实。
作为一种深度的“客观维度”不可解,女性对“肉体”(外在美)的优化追求等同于对“物质资源、名利地位”的追求,都是受缚于客观的既有环境与观念规则,因此会像“月经”一样地无法解决,导致女律师被剥夺本属于自己的胜利荣誉。
特别是女律师的身份,她掌握着既有社会里的现行法律,正是既有环境与规则的确切融入者,其工作更让她必然地以此为凭依手段,去获取收入、地位的胜利,也是对应现实工作身份、法律规则的“物质名利”之既有客观观念的胜利,以此完成相应属性的女性飞升。
她极其具体地身处在了“律师”的自我困境之中,从外部发展到了内化,必须破除“律师”的自我认知,还原成“女性”本身,将“女性飞升”去除既有规则与观念的束缚,真正聚焦在女性自身,扎根于“女性崛起”这一情感层面,纯粹于心灵满足的实现,而非以此去得到什么物质客观层面的奖赏与回馈,不让它变得世俗与功利,才能最终胜利。
在第一阶段,“男性主导的外部规则”成为了最先出现的困境,改变的契机也随之出现。
毒枭在厕所恐吓式地联系了女律师,随后在“男罪犯得到开脱”案件的报刊旁边绑架了女律师,即为初步的困境打压,随后让她安排自己的变性工作,并妥善处理自己的家人。
就形成了女律师之于“男性强势者”的逆袭,由自己做主,掌握一切资源,去引导他完成直观到粗暴的性别地位扭转,直接从男性变成女性。
毒枭的身份同样非常“符号式”,具有最强的暴力、财富,加持在其作为男性的肌肉形象之上,作为全方位的男性优势者出现。
女律师面对着他,需要调用的是自己作为律师而掌握“现行规则”,以及对方给予的物质财富。
因此,此阶段的“困境”来自于“既有外部现实”,被其打压的女律师面对着困境凝结而成的男毒枭,通过对资源与法律的运用,引导他完成变性手术而解决这一困境。
困境的开始是她被毒枭暴力绑架、随后不断威吓的“压制”,结尾则会是她得到“物质追求”金钱之报偿。
从争取目标到实现手段,“男性语境、男性规则、男性优势资源”始终主控着一切,也让女律师针对“物质事业成功”的扭转弱势之追求,只能得到虚假的结果,对应着毒枭由男变女目标的不完全结果。
在这个部分中,“演唱”的用法进一步地拓展、细化。
在二人见面的时候,段落先延续了此前庭审的现实主义风格,随后毒枭开始自述想要变性的内心,念白逐渐地情感渴望强烈起来,也开始具备了起伏的音调,却没有配合到音乐。
这正是演唱在“无音乐”的现实主义环境之中的被压抑状态,即“女性情感”被现实困境的笼罩。
相应地,女律师同样以这种念白作为回应,却逐渐争到了独念的“权力”,暗示了她的首次逆袭成功。
她开始主导毒枭的变性,“女性崛起”占到了上风,环境也随之产生了变化,现实主义的自然光开始减弱,画面内部光源的车内灯关闭,以此强烈地提示了外部人为光线的存在,也让场景从现实光源的氛围变得更加“表现主义”起来,同样是暗沉的环境,却不再是现实感,而是对毒枭“无法彻底归于女性内心”之痛苦心境的沉浸,也具有了一种舞台的光线氛围,对应着女律师愈发接近“吟唱旋律”的念白。
并且,雅克欧迪亚也用镜头设计去“弱化”现实主义风格,不断地给出毒枭的局部特写,让他只以眼睛、嘴巴出现,淡化了完整形象的男性特征,突出了此刻“想成为女性而不得”之心灵痛苦的抒发,眼与口正是心灵的两种输出媒介。
这让镜头作用于“女性”的内心表达,而这种运镜是固定中远、客观全景的现实主义所少有的,由此形成了“女性对既有现实客观环境的冲击”。
但是,女律师在这个阶段的追求同样扎根于“既有现实”,看中了毒枭的金钱回报,这也对应了她在其中的凭依,需要依靠对法律规则的了解,安排毒枭的行程,并妥善处置妻儿,获得新的合法身份,要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
因此,她必然会受挫,无法走出困境,只是在战胜“外部客观环境”后走入下一个更深度的困境,即“受缚于既有的自我”的心灵困境,迷茫大于欢喜。
雅克欧迪亚给出了几个小地名标记的小段落,作为这一细分阶段的递进呈现。
首先,女律师来到了首尔,完成“获得物质层面劣势的暂时扭转”。
在转场的设计中,毒枭抛给她的黑卡上的星星标记变成了飞机降落的灯光。
在此前的段落中,她身处在现实感的办公室中,滥用着毒枭的经费去坐头等舱,“律师”身份、“物质财富追求”加持的“性别逆袭”完全匹配了这一环境,在说出头等舱瞬间的镜头迅速位移,正是她在此阶段的“主观情感爆发”。
因此,头等舱飞机就成为了她对毒枭金卡的滥用结果,随即降落在了“物质追求、暂时胜利”的首尔环境之中。
作为其情感爆发、胜利实现的歌舞环境随即出现,她先是与男性医生进行“对抗”,后者与毒枭一样地无音乐“干唱”,低沉而又跑调,是本片中“被扭曲心灵情感抒发”的表现形式。
女律师与之轮流独唱,逐步获得了主导权,演唱也愈发地优美起来,最终引出了完全的歌舞时刻。
这个变化同步于对话内容,女律师不停地推动着毒枭变性手术的进展,让医生接受了手术请求。
但在其中,导演提示了潜在的“女性非强势”,女律师只是在不停地应允男医生的诸多问询而已,实际上显出了被动的状态。
这也导致了歌舞部分的戛然而止,旋律在中途被刻意地中断,切换成了现实主义的环境:飞机再次出现在远景之中,“起飞向首尔”,而女主角则被“留”在了自家,在现实主义的定场镜头中,身处于环绕的黑暗中,只拥有局部的黄色明亮,她试穿着律师的西装,工作身份与“肉体美审视”都是对“既有客观物质化现实”的潜在受缚,并遭遇了毒枭的惩罚,承受暴力,因为她“坐头等舱去享受”的物质追求。
于是,“首尔”歌舞场景承载的“物质追求之暂时胜利”由此消失。
“物质追求”形成了更加内化的心理困境,引出了“瑞士”的小标题段落。
雅克欧迪亚将之做成了“首尔”部分的明确对比。
她面对着另一个男医生,再次与对方针对变性手术的问题而轮流“干唱”,这一次却逐步争取到了独唱的权力,不再是配合对方的“应和”、合唱中的“不停应允”,也更确切地说服了本不愿手术的男医生。
随后,这种胜利也扩展到了现实主义的部分之中,作为她“取得既有物质客观环境之胜利”的表现。
她发挥了自己的法律特长,不仅安排了毒枭的假死,脱离出犯罪之暴力规则世界,也给其妻儿安排了新的身份,并让她们接受了丈夫的“死亡”,自己也获得了毒枭给的金钱回报。
但在这个小段落中,她其实并未真正走出“物质追求之心”的内化困境,其身份、手段、解决“外部”问题、追求目标,都只针对了外部环境,实际上却让自己深陷于此,在利用与追逐着既有外部环境的游戏规则、“成功意义”(目标),观念的受缚很明显,也就不足以摆脱“月经”所象征的“生理肉体之客观物质层面”笼罩,无法突破“男尊女卑”的现状。
因为这是既有环境所定义的客观规则,不能放下对其环境的“物质名利追求”观念的执着,不能将“女性崛起”提纯、洗清意气为借口的“名利渴望”、只留下作为“女性”对认可与尊严的心灵追求,就必然只能处在内化困境之中。
在“瑞士”的段落中,雅克欧迪亚剥夺了歌舞场景,正是对此的强力表现。
女律师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到主观情感爆发、个人追求实现的状态之中,有的只是被既有环境所扭曲压制的“干唱”而已。
“首尔”还有着手术室里的暂时歌舞,是对于外部困境消除的暂时成功,随后进入了内化困境,并停留在了这里。
此阶段的非现实主义场景、“歌舞”要素的场景,同样以非常扭曲而弱化的形式出现。
女律师带着医生去见毒枭,此前的头等舱飞机灯光变成了车灯,场景也就成为了后者反映“负面心境”的外化舞台。
女律师遇到了毒枭的妻儿,随后更是看着一家三口的其乐融融,这让她感到动摇,因为帮助变性便意味着对这温馨一切的打破,由此伤害同为女性的对方妻子,反女性崛起而行。
在一家三口仰望天空的时候,美丽的星空出现在极其遥远的彼端,女律师与毒枭一起只可远观,正是此阶段中二人身处内化困境、无法达成“女性崛起”之根本目标的暗示。
并且,“歌舞”出现在了这里,却是完全陷于现实主义全局的状态:医生与女律师坐在车中,音乐在音响中播放不停,医生甚至嫌它太吵,想要关掉;女律师在车外等待,其他人载歌载舞,她却没能融入歌舞之中。
特别是最后的部分,手术合作达成,医生离开,女律师得到了毒枭的许可,直接“让他们关掉音响”,这无疑意味着二人在“变性成功”中的本质结果,反而让自己远离了歌舞世界所象征的心灵世界圆满、情感追求落实,而“音乐停止”的两阶段决定者则是男性的医生与毒枭。
在答应手术的时候,医生说出了关键的台词:我没办法改变他的心灵。
这正是外部手术的局限性,只能改造“物质肉体”对应的“外部客观环境”,无法解决的是内化的自我认知,即心灵层面的困境。
一切的根源是女性与想要变成女性之人对“既有环境中根深蒂固之规则与观念”的受缚,只能靠她们自己解决,彻底让自己走出既有环境的身份、生活、下意识的依赖、对观念的潜在深信。
当医生与毒枭商量手术的时候,二人身处在了周围黑暗的框体之中。
毒枭的自白与“手写笔记”的画面交叠出现,后者是对应女律师“写作辩护词”的“文字形式抒发内心”,同样以受抑制的内容出现,她遵从男律师的指挥,在男医生的手下只进行“肉体层面改造”。
因此,当毒枭完成手术、其妻儿也得到妥善安置的时候,女律师得到的反而是妻子的痛哭,即女性之于“既有现实”---利用法律规则与犯罪规则而获取的新身份,丈夫接受的物质层面手术,“客观可行现实”中肉体层面的性别转换,出于客观安全考虑而对妻儿的安置---的受挫。
变性手术完毕后,毒枭第一次作为女性去照镜子,对嘴和眼睛的局部特写镜头再次出现,却是以“绷带包裹”的状态给出了更甚于上次(自白手术愿望)的负面性,其作为女性的形象在绷带之下遮掩而“受抑制”。
并且,女律师得到了金钱的回报,现实名利追求被满足,情感层面却是受挫的:毒枭作为“新女性”而宣告了“永别”,对她用完即弃,其妻子作为女性则对着她痛哭失声,双方之间带上了毒枭丈夫秘密导致的隔阂。
女性之间的“互助互促”之正面协同关系、基于“女性崛起”的心灵情感纽带,以女律师帮助毒枭变成女性、帮助其妻子安全生活的方式出现,也符合女律师对自己的生活追求。
但它们同时受到了抑制,因为一切都过于围绕“既有客观现实环境的规则”,最后被颠破的则是女律师自己的内心层面:她被宣告“永别”,坐在黄色车灯的出租车中,黄色对应着此前“身处下层黑暗中的自家”部分的室内光线,象征着“客观现实环境里的暂时成功”,也随即让她露出了极其复杂的情绪,混合着大笑与痛哭,因为财富获取而笑,也感受到了情感层面的受挫、让毒枭妻子受苦而哭,更深层次的痛苦则来自于其对受缚于既有现实中腐化观念、只追求名利目标、甚至不惜伤害其他女性的自我认知。
在这种复杂多重、最终归于哭的表情特写之中,女律师显然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既有观念束缚”之内心困境,却无法脱离出去,只能处在痛苦之中。
这构成了“伦敦”的下一段落,外延到了毒枭的同等困境。
在他摘下绷带,展示出女性身姿的时候,黄色光线再次以黄昏日光的方式笼罩了一切,并将她的身体逆光虚化,“艾米莉亚佩雷斯”的新名字也随之被动摇了意义。
同样被抹除意义的,还包括了“文字”:在变性手术完成的前后,毒枭的旧身份在外部现实语境的“新闻口播”中归于“发现尸骨”的假死结局,同时出现的则是变性手术笔记的烧毁,即作为女性阿米莉亚佩雷斯的新身份的同步“死亡”。
手术是外在肉体层面的改造,被烧毁象征着其意义的虚无,也是“脱离演唱”的“文字”作为“抒发内心媒介”之扭曲形式的巨大局限性,对应着女律师追求事业成功而无果的辩护词文稿,让“艾米莉亚佩雷斯”处在了男性与女性身份同时“死亡”的尴尬状态之中,无法完成剥离男性、纯粹女性的“手术成功”,不能确凿女性认知、圆满心灵追求。
在这个阶段中,变性的毒枭成为了新的女性角色,其作为“外在客观物质层面”的女性肉体,以及并未彻底接受女性的混合内心,无疑是对女性内化困境的最有力呈现:她用手术完成了女性化,却尚未扭转“既有现实”对应的“过往生活”给予自己的男性认知部分,让其与女性认知部分形成了冲突,无法真正地作为纯粹女性而“崛起”。
他会面对男性丈夫身份所承担的妻儿家庭,面对妻儿因自己的痛苦,也会面对曾经男性身份带来的诸多生活问题,只改变肉体并不足以完全重新开始,而只以金钱、犯罪规则、法律条文而帮助了他变性的女律师,也同样需要面对对方妻子,更扎实地引导毒枭,更妥善地处理好一切问题,并重建与毒枭妻子的关系,也随之找回自己“女性互助”中的纯粹女性自我,完成只之于性别的心灵圆满,而不是物质层面的功利“圆满”。
在影片的第二幕中,雅克欧迪亚直接呈现了女律师与毒枭的更高一层困境,是主观内心中对于“客观物质社会”的潜在受缚,让她们始终以非情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试图以财富、名望、权力、法律等手段去支撑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此达成自己的情感化目的,即最终极的“女性心灵达成”,确立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律师不再被男性利用、压制而彰显自我价值,毒枭更是非常直观地“完全成为女性,彻底接受作为女性的自我”,排除掉自己作为男性的心灵阻碍。
这种努力由于解决方式的“外部社会化”,注定让她们始终身处于社会环境之中,只是试图依靠资源与地位的强大,由此陷入了既定社会的游戏规则之中,反而无法将自己还原为纯粹的“女性”,始终是“律师”与“毒枭”,因此也就无法超出“男尊女卑,资源分配”的固化现实铁则,难以完成单纯女性身份的认知确立与崛起。
“墨西哥城”构成了第二阶段的主体舞台,让律师、艾米莉亚、毒枭妻子一起身处在自我认知的困境之中,并以各自方式试图冲破它,正是第一阶段中“东京与瑞士”(通过变性手术而获得女性地位)的升级。
雅克欧迪亚使用了艾米莉亚的“毒枭”身份,这密切关联着她在男性时期的外部社会身份、高权力地位、巨大物质财富,乃至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暴力等犯罪资源,一并归拢在“男性主导的固有社会规则”之中。
同时,艾米莉亚身上的“毒枭”过往也与其情感与心灵的追求构成了排斥,她的女性之心让自己必须放弃毒枭的身份与性别,但这又压抑了她作为人的爱情与亲情,被迫与妻儿分离。
她想要弥补这种情感的缺失,又不能承认自己作为毒枭的丈夫、父亲之男性身份,因此只能借助女律师的帮助,作为“借助法律与财富帮助变性”的再延伸,发动自己的财富,编织出“姑姑艾米莉亚”的谎言。
这也进一步外延到了她对“毒枭犯罪过往”的消解:曾经作为男性的她以自己的犯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与暴力,导致了很多平民的死亡,让其他女性陷入失去亲人的痛苦之情,现在变成了女性,必须清偿毒枭男性的一切,才能彻底确立新的女性自我,也“解决”掉情感抑制的部分,通过赎罪的方式抹除象征“男性主导、既有社会”的物质力量之罪,让自己能够与其他女性一起得到正面的情感共通,消解一切“男性现实丑恶”的部分,完全让自己沉浸在女性内心之中。
作为帮助艾米莉亚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人物,女律师也可以借此完成未竟之事,即本片中有意强调的“女性互助”,作为女性实现另一名女性的自我确立、走出困境,也就此让自己证明了作为女性的价值。
“女性互助”同时作用于女律师与艾米莉亚、二人与受害者家属、女律师与艾米莉亚妻子之间,与二人的自我“女性确立与自证”高度相关。
但是,在这个阶段中,艾米莉亚与女律师始终下意识地依靠着自己在外部现实社会中的资源,从地位到财富到“运用法律”甚至“凌驾于法律之特权”,相应的身份也始终是著名律师与超级富商,即在外部物质社会中的名利地位。
因此,二人无法真正解决掉物质社会里关于“男女资源分配不公”的根本铁则,艾米莉亚无法获得妻儿的爱、赎清自己作为毒枭男性的罪与“男性过往”,女律师也无法通过对她的有效帮助而完成自我意义,也包括对其妻子的帮助、弥补夫妻问题,一并构成了“女性互助”的难成,女性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在现实化的问题基于现实考虑的猜疑、恐惧、隐瞒、利诱之下被打断,彼此都处在了情感受抑制、被迫处于“物质现实心境”的状态。
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正是她们对“外部社会环境”认知的无法脱离,并落在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形式之上:艾米莉亚始终无法消除掉“男性毒枭”(男尊女卑之现有社会的浓缩)的过往经历,始终被其困扰着。
作为呈现手法,雅克欧迪亚拓展了音乐元素,以及音乐与现实环境的交互切换。
“伦敦”是这个阶段的起始,作为“自我认知困境”本身的呈现部分。
女律师得到了毒枭的报酬,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在宴席上侃侃而谈,甚至得到了男性“为了你而换桌”的殷勤关照,一切都处在女性崛起的状态之中。
但是,女律师的成功得益于物质财富与“非法犯罪”,此时的结果也是社会面的律师身份与物质财富之成就。
因此,当带有她“图财而违法”过往、犯罪暴力属性的艾米莉亚出现的时候,一切的成功也就摇摇欲坠,让她产生了巨大的动摇与恐惧,恢复到了弱势自我、承受男性威压的意识之中。
艾米莉亚先隐藏了身份,与律师在女性友爱的氛围中交谈,更是从英语变成了西班牙语,带到了“拉美裔墨西哥人在美国的弱势民族崛起”层面。
随后,艾米莉亚揭晓了身份,女律师马上感到了恐惧,“你是有意靠近来灭口的吗”。
这正是她对二人目前关系的定性,立足于暴力与犯罪的极端现实,女性互助、帮助对方变性而拥抱本心的情感纽带被扯断,被她的现实考量、负面情感所取代。
这源于她帮助毒枭的理由,是为了自己的财富,而非真的对对方友善,始终没有真正地接纳、信任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
艾米莉亚试图解释、建立信任,却始终无法成功。
此时,灯光明显暗淡下来,从现实氛围变成了歌舞的舞台,但二人的低吟穿插、交互默念,始终没能演变成真正的合唱,甚至没能在“干唱”中提高音调的丰富度,音乐质感完全缺失。
这正是此阶段之于第一阶段的负面推进,二人似乎走出了“外部现实”的困境,实际上却进入了下一层的“自我束缚于既有现实之认知”的内化困境。
随着负面的升级,“音乐舞台”也被剥夺了“爆发展示正面内心情感”的能力,她们作为女性的情感受到了自己的束缚,于是作为表达形式的“歌唱”也就只能处在“干唱念白”的“扭曲”形式,停留在第一阶段“歌舞开始”的现实前导环节。
随后,戏剧与音乐的交互继续推进。
艾米莉亚与女律师形成了再度的合作互助关系,想让后者帮忙设计方案,不暴露自己真实身份地迎回妻儿,随后更是遇到了自己作为毒枭的犯罪过往,让女律师帮自己“赎罪”,建立寻人组织,将死难者的尸体带回给其亲人,弥补对方的情感缺失,也让自己能够洗清现实暴力规则导致的罪孽,获得女性身份的全新、洁净自我,将从小到大的“女性内心认知”圆满。
但是,女律师从她这里图谋的依然是现实社会里的名利,而其帮助手段也依然是谎言与财富,对其妻儿继续隐瞒真相,利用财富与权力去组建公益组织、推进寻人计划,而她自己得到的也是社会层面的。
她回到了影片开头的小吃摊位,彼时的她在这里被男性律师要求,无奈地写着辩护词,尚且能够激活歌舞,穿梭在音乐与现实之间,暂时地爆发作为女性的反抗之情,但到了此时,她似乎完成了女性律师的逆袭,却在这里反而失去了曾经的内心爆发。
这符合她在此时的言行举止,提出“我要带孩子”的单亲妈妈、独立女性内容,以此拒绝帮助艾米莉亚,直到艾米莉亚说出“我可以帮你买一个丈夫”,并真的把保镖划给了她,再次给予财富去完成“性别逆袭”,她才应允下来。
随后,当场景再次来到地摊的时候,女律师更是与艾米莉亚一起,看到了二人无法靠“变性手术”解决的、由毒枭过往导致的“女性情感抑制”。
母亲发放着失踪儿子的寻人启事,始作俑者艾米莉亚与其帮凶女律师只能沉默以对。
毒枭人生带来的“女性创伤”并没有随着变性手术而化解,也牵绊着艾米莉亚,让她无法彻底抛离男性毒枭的自我,完全成为女性艾米莉亚,从而构成了二人的下一步举动,用艾米莉亚的财富去建立寻人公益组织而“赎罪”。
女律师帮助艾米莉亚,继续使用外部社会的物质资源去争取女性的情感圆满与内心释放,而她自己的女性目标也同样由社会层面完成:在公益组织成立的段落中,她与艾米莉亚一起接受采访,与对方轮流获得话语权,也出现在了电视之中,由此逆转了开头时被男律师剥夺话语权的弱势事业地位。
在两个阶段中,女律师都从“地摊”出发,面对着外部社会--男律师的打压,男性无罪化的开脱,以及“男性毒枭”作为客观经历与结果的动摇女性情感内心---的打压,也似乎找到了反击的出路:帮助艾米莉亚,完成对方与自己的飞升。
但是,第二阶段的她处在更深度的自我内化困境之中,“地摊”段落也失去了音乐与歌舞,而是全程保持在现实环境之中,艾米莉亚与她只能低吟默念,而寻找儿子的母亲成为了“第一阶段里的女律师”,即身处在男性主导客观社会里的弱势女性,其低吟具有了更强的旋律感,却终究只能是无音乐的干唱,被艾米莉亚与女律师压抑了亲子之情,也对应着三人作为女性的互助与内心纽带,没能得到二人的真相。
此外,二人联手解决艾米莉亚家庭问题的情节,也同样反映着这种状态。
当艾米莉亚与女律师初步商量的时候,镜头从现实主义的定场远景开始,黄色灯光的豪宅房间被周围的黑暗所笼罩,正是第一阶段中“女律师在自家被毒枭攻击”的再现,房间的位置更高,象征着社会阶层的上升,但”局限性内心实现”的黄色光线、周围的现实黑暗仍然存在,让二人仍然处在客观现实社会的环境之中,“既有环境内的阶层上升”恰恰是对环境的脱离失败,因此作为“女性”在“男尊女卑之社会规则”的逆袭也就无法成功,而是会在各种社会身份中深陷。
此时,女律师紧张地反对着艾米莉亚对儿子的擅自靠近,明确抑制了她的情感。
而在她接妻儿到艾米莉亚家中的段落中,镜头更是反复在几个女人之间切换,不停地呈现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各自的心境:女律师紧张地望着艾米莉亚,随后表示自己“要回伦敦”,二人的互助、信任、正面情感关系显然不强,而毒枭妻子则错愕地望着女律师,并对艾米莉亚的突兀热情不置可否,对二人的纽带同样被怀疑、错愕、猜忌所破坏。
在这个阶段中,妻子正是电影暂时给出的“正面女性”,其没有律师的功利社会身份,也没有艾米莉亚的两性混杂属性,由此成为了艾米莉亚与律师的反衬,也是对主题的积极展示。
她只是单纯的“女性”,面对着律师与艾米莉亚凭借现实资源编织的巨大谎言,是其“现实维度”的弱势受害者,也试图去怀疑、推理、反抗、冲破它。
雅克欧迪亚给出了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段落。
妻子独处在房间中,所有的物质财富之奢华都成为了她的攻击对象,并唱出了“这只是金钱的牢笼”等歌词。
她是三人中唯一获得歌舞段落的“内心抒发女性”,在嘴巴的特写镜头中给情人打电话,说出“我是为了你回来的”,此时的镜头处理对等于第一阶段中说出变性意愿的毒枭,是音乐形式之外的“女性抒发”表现。
并且,她也与第一阶段中地摊段落的律师一样,在歌舞与现实房间的环境中来回切换进出,以内心情感爆发的“女性”去对抗“物质财富”环绕的“客观社会牢笼”。
在戏剧层面,这落到了律师与艾米莉亚依靠各种资源堆积出来的谎言之中,从变性开始就伤害了妻子的爱情,到了此时更是囚禁了她,而她则以结交新情人、重获爱情的方式进行反击。
同样的歌舞处理,也作用在了“受害者亲人”的层面,在公益组织的场景中演唱。
在这里,作品拓展了性别与年龄,让男人、女人、孩子一起歌唱,由此强化了“阶层”的属性,以底层人对失去家人的情感去对抗“毒枭犯罪”。
阶层分化正是物质分配的最根本凭据,在毒枭变性、洗清“男罪”的行为中得到了扭转,成为了影片给予的“圆满出路”,让所有底层人改变了性别、扭转物质与阶层化所注定的“男强世界”,艾米莉亚也成为了自我救赎与拯救世界的复合存在。
但在这个阶段,这一切只是暂时的成功而已。
在戏剧层面,妻子与受害者亲人都处在律师与艾米莉亚的谎言之中,面对着变性的“毒枭丈夫”而不知,也身处在“姑姑艾米莉亚的豪宅”与“公益组织”里,情感的抑制也就不可避免,而二人寄托在她们身上的女性心灵诉求也同样得不到实现。
同时,这更落在了音乐歌舞的终结部分的处理之上。
妻子的演唱段落戛然而止,被“切回现实一方”所直接打断,而受害者们组成的“艾米莉亚之自救与救世”部分则更为巧妙,一个个的演唱者逐一出现在纯黑的画面之中,逐步形成了“星空”。
“星空”在第一阶段里也有出现,是毒枭一家人眺望的对象,象征着其亲情实现的美好。
而在第二阶段中,艾米莉亚与儿子相拥而卧,星空却变成了人工灯光的绿色斑点,亲情在谎言的笼罩中进一步地弱化,其追求女性心灵的实现,却反而导致了亲情层面的心灵受挫。
在受难者们组成的“星空歌舞”画面中,艾米莉亚对自我、家庭、世界的情感寄托与作用,一并成为了彻底的架空存在,标志着其之于现实维度中的隔离。
对于女律师,雅克欧迪亚更是在第二阶段的开始部分,早早地给出了相应的表现。
大雪覆盖了天地,纯白色意味着情感的极度冷却,序幕中的女声电音齐唱再次响起,女律师随后出现,也再次带来了序幕中“女声齐唱被现实环境扭曲成收废品声音”的升级:她处在更高的社会地位之中,却欺骗着毒枭妻子,让对方回到墨西哥城,女性互助、互信的情感纽带被亲手扯断。
女律师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她在律师事业上的性别逆袭,却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物质社会属性”,名利身份、财富手段、物质目标,都让她无法脱离出去,成为纯粹的女性,只能受到社会的认知束缚,在这一“男尊女卑,资源分配不等”的不可变环境之中,因遵守其规则而失败,直到作为单纯的女性而腾飞,彻底放开抒发女性内心情感的歌喉,完全进入现实中的音乐情境。
在后半部中,作品进一步地展开了艾米莉亚佩雷斯的表意功能,让她分别面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女性”身份,前者对接着基于公益组织领导者与其背后的赎罪诉求、属于男性的自身过往,后者则是纯粹基于女性的情爱诉求,由此构建出了艾米莉亚作为变性者的复杂形象。
同时,无法在心灵层面抹除的男性过往又与权力、犯罪等客观物质社会面相连接,成为了她难以彻底实现女性情感圆满、女性自我认知确立的障碍,即女性面对“客观社会环境”之固有不可变的境遇。
她们更关注心灵的层面,却被物质社会的规则所牵绊,会在物质为先的规则中产生动摇,只有去除一切社会身份,回归“女性”纯粹之身,找准自己的心灵情感诉求之根本,以此对抗物质分配基于男尊女卑而无法改变的“社会”,放弃自己对社会的物质准则的依赖与追求,才能完成自身的圆满。
艾米莉亚被赋予了男性与女性的混杂属性,性别的对立导致了自我认知的混乱,性别又各自对应了物质社会面与内心情感面的诉求,由此将认知混乱的寓意扩展开来,将两种诉求同时投放在艾米莉亚的心中,表现出他的摇摆与混乱。
只有当他真正完成了作为男性毒枭的赎罪、承认过往的存在并付出代价的时候,才能真正洗清、摆脱这一身份,回到纯粹的女性之身,并由此切割掉男性承载的物质社会诉求,确立女性拥有的根本情感诉求,随之成为完全的“女人”,也作为女性而战胜了男性主导、男尊女卑、物质分配与竞逐的客观社会。
作为具体的戏剧表现形式,艾米莉亚在后半部中分别对接了女律师与死难者遗孀,也随之带动了女律师的人物线索。
她与艾米莉亚的关系始终是基于物质诉求、“律师事业”的,通过两次合作获得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也知晓艾米莉亚作为男性的过往,因此始终无法将艾米莉亚与“暴力犯罪富有的男性毒枭”切割开来,随之导致了艾米莉亚自身对男性部分的“无法脱离”与自我认知矛盾。
在这样的关系中,女律师难以与艾米莉亚形成真正有效的女性互助,因为女性互助必须以情感诉求、互相圆满作为基础,是纯粹女性之间的交互,而她们此刻却各自带着物质社会诉求与“男性毒枭认知”,相处始终伴随着权力与金钱的使用、对名利世界的接触,其合作主体的公益组织正是建立在其上,因此也就无法达成艾米莉亚“洗脱男性过往之罪”、女律师“获得自身成功”的目的。
而在另一方面,遗孀的出现让艾米莉亚拥有了完全作为女性的机会,二人的初遇契机是女性对于“被毒枭杀死之人”的哀伤,因此产生了女性情感层面的共鸣,且是对“弱势情感,心灵伤痛”之缺口的弥补。
这衍生了二人的同性情爱,是变性之外的又一非主流社会价值观,以一种激进的形式去凸显女性的性别存在感与情感追求,以此对抗“异性恋、性爱主导者”男性所掌控的主流社会观念,在爱情角度上形成了女性崛起、战胜性别高低不可逆社会的表现。
但是,艾米莉亚对遗孀隐瞒了自己的毒枭过往,导致这种女性圆满停留在了自身生活一半的程度,始终被她与女律师构成的另一半所阻碍、削弱,自我的内心冲突与混乱只能靠另一半的“承认毒枭过往、真正洗清男性经历之罪”,才能实现真正的合一“女性”。
在落实艾米莉亚表意功能之前,雅克欧迪亚先给出了真正的”纯粹女性”,即艾米莉亚的妻子,展示着其对物质诉求的脱离,以及由此完成的情感圆满,而与她对面而坐的艾米莉亚则成为了消极的反衬,甚至被其无意间触碰了作为男性丈夫的过往与隐瞒,并形成“女性”之当下的情感挫败。
如上所述,公益组织的底层人们齐唱着关于“宽恕”的歌曲,化作了非现实的星空,星空对应着艾米莉亚一家眺望的夜空,是她的情感圆满时刻,彼时作为男性而遥远无比,此时变成了尚不纯粹的女性,想要以此得到“宽恕”去洗脱男性经历之罪,夜空却变本加厉地成为了非现实,而合唱承载的“心灵共鸣、情感交互”也同样处在了影片中最虚幻的非现实、纯“舞台”之中,比大部分段落里的“以现实为基础的舞台”更加极端,是后者“心灵呐喊、情感释放无法真正落于现实”的程度升级。
这是属于公益组织领导者艾米莉亚与女律师的情况,随后出现的妻子则并非如此。
合唱的“星空”被现实里灯火幢幢的城市夜景所取代,构成了现实世界的情感圆满之地,而它的拥有者正是妻子,身处在情人的车中,“心灵共鸣”的音乐环绕着二人。
她因为丈夫毒枭的变性与隐瞒而失去了爱情,是女性之于男性的受创者,又让自己以纯粹女性的身份得到了爱情的弥补,因为她除了爱情之外别无所求。
在二人分别的时候,欧迪亚拉大了音乐的声音,在升格镜头中展示着妻子对情人的敞开胸膛,强调其对传统世俗礼法的全不在意,一切只为了自己的爱情,而段落首尾的两个特写镜头,则展示了她的足部,从“名贵高跟鞋”---亮闪闪的形象让人想到了此前女律师拿到的黑卡钻石与头等舱飞机灯到“裸足”,此前她独唱的“这里不过是金丝编制的牢笼”也是同样的寓意,也反衬着此前女律师被反复特写强化的“穿皮鞋的足部(事业装扮之身份)”。
她以这样的“摆脱物质诉求之纯粹女性”形象,坐到了艾米莉亚的面前。
艾米莉亚试探着自己妻子的“外遇”,妻子则直白地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弥补与圆满,让艾米莉亚只能尴尬地沉默。
在妻子的映衬下,提及夫妻过往、考察妻子“忠贞”的艾米莉亚成为了性别认知不纯粹的女性,与妻子的“女性互助、情感共通”也无法实现,被其隐瞒的变性经历与真实身份所阻隔,而她也无法像妻子那样地实现爱情圆满,反而作为男性的部分遭遇了被“出轨”的挫败。
于是,与艾米莉亚的男性、社会面相关联的女律师,也就成为了她的同状态者,并反过来牵扯出了艾米莉亚作为男性的部分,让它始终无法被规避绕开。
二人参加公益组织的晚会,女律师抗议着客人的名单,有太多的腐败官员、犯罪分子,艾米莉亚却表示她只认识这些人。
公益组织是为了洗清男性部分而存在,但其运转又离不开艾米莉亚作为男性而拥有的物质社会资源,由此成为了男性主导下客观社会之中的存在,女律师与艾米莉亚投注在其上的女性诉求就成了泡影。
女律师想要借此获得社会地位,完成物质层面的逆袭,却发现自己必须依赖于这些男性犯罪者,始终是力量弱小的存在,臣服于黑暗的上层男性与性别高低之铁律的不可变。
这导致了她与艾米莉亚的矛盾,走上女性互助与共通的反面,也让艾米莉亚暴露了自己“只能依赖而非摆脱男性部分”的事实。
但与此同时,二人作为女性又拥有着一种共通的可能,即对无法摆脱男性主导之弱势自身的无力与愤怒,各自的歌词都是对女性自身的宣示、男性社会的抨击,由此引出了这个段落中的歌舞段落、心灵世界。
歌舞的风格在这里开始丰富起来,由此对接到了人物状态、心灵情感的更细致、多面内容。
二人轮流演唱着歌曲,共处于此间的状态意味着“被社会所压制与反击”之心的共通,而音乐与舞蹈风格又有所区别,给出了现阶段的暂时冲突:女律师的部分变成了输出愤怒的rap与战士舞,在片中首次出现,是她对男性主导社会、女性被物化(剪下金发女郎的头发)的反击之情,这意味着她的人物线索推进,此前一直流连于既有物质社会中的成功,让自己始终有所妥协、配合,直到此刻才终于产生了彻底的愤怒,敢于去敌对它,而艾米莉亚的部分则依然是“被扭曲心灵”的干唱,甚至更接近于此刻她在现实维度中的“演讲致辞”,是弱化的“反击”,与女律师的交互拥有倾向的共通,也有着“各自风格、独自演唱”的程度区别与冲突。
基于“反击与愤怒”的基础共通与互助,足以给出一定的效果,在歌舞的结尾变成了撼动这一环境的“地震”,指向了二人作为女性的未来出路,即“反击之怒”的升级极致、贯彻到底。
在现实层面,二人的交互成果是公益组织,其命名为“微光”,暗示着“夜空”的现实化落地。
但是,在二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欧迪亚使用了电视画面的形式去呈现,让她们始终被笼罩在“收看电视之人”的眼光之下,暗示着外部社会对其的掌控,并聚焦在了采访者的男性身份上,始终引导着对话的进行。
具体到二人的身上,女律师率先回答问题,话筒却迅速转到了艾米莉亚一边,镜头间或带过女律师,她几次试图开头、夺回发言权,却都被艾米莉亚与采访者无视,最终只能尴尬地闭嘴了事。
在这里,艾米莉亚拥有女律师认知的“男性部分”,而采访者则是完全的男性,由此形成了男性对女性的话语权剥夺,而“采访里的发言”正是女律师在影片开头被剥夺的东西,是对她工作成果理应的回馈与认可,此前通过公益组织而短暂地获得了它,此刻却再次失去。
随后,二人进入了办公室,镜头先是给到了新闻画面中的公益组织旗帜,只是由文字书写的“微光”,毫无夜空的正面展示,且被笼罩在“现实摄像机视角”之下。
这暗示了公益组织对诉求实现的无能,随即引出了上述的晚宴段落,进行揭示性的落地。
并且,艾米莉亚也对女律师有着直接的“宣判”:女律师抱怨着工作,艾米莉亚则作为组织一把手,看似温和实则坚决地为对话画上了句号,“这是你的工作,你创造了这一切”,将女律师禁锢在了社会身份与其环境之中,只能在诉求难成的公益组织中过活,也让二人的上下级、强弱势关系得到了表现,艾米莉亚由男性毒枭过往而得到的资源,让她始终是公益组织的最高层领导,让女律师难以获得理想中的地位,平等关系支撑的女性交互---特别是艾米莉亚还带着“男性部分”---更是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艾米莉亚与遗孀同样拥有了歌舞的部分,且实现了高度的情爱共通。
初遇的段落从遗孀的匕首开始,她想要反抗可能出现的丈夫,随后则是她与艾米莉亚作为女性的交流,一起体会爱情受创、毒枭杀死丈夫、丈夫也同样是欺压妻子之人的伤痛,最后又在艾米莉亚展示的手枪中连接起了对如此男权社会的反抗之心。
这直接带来了合唱的音乐段落,且具有强烈的现实属性:镜头对准了遗孀的家庭内景,加速昼夜的更替,以此作为现实到音乐舞台的世界环境切换,却又非常自然,一镜到底的效果明显比此前的“切镜”与“现实风格打光关闭、舞台灯光点亮”的有意生硬,来得顺滑而自然,让两个世界形成了流畅的过渡与连通。
这意味着艾米莉亚作为女性而抒发内心情感的“进入现实”。
二人从“扭曲压抑”的干唱开始,逐渐配上了音乐,曲调也愈发上扬,音乐性强烈起来,表现着她们摆脱外部现实遏制、形成爱情交融的过程。
艾米莉亚的手部特写,抚摸遗孀的照片、身体,更是对心灵共通的外化呈现,让二人切实地“接触无碍”。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艾米莉亚褪去了所有的身份,只是“女性”而已,由此获得了女性根本情感诉求的圆满。
欧迪亚将歌唱的内容始终与艾米莉亚的现实层面串联起来,在平行剪辑中强调了艾米莉亚与女律师的“客观现实状态”:艾米莉亚的演唱延伸到了她与女律师工作的场景,女律师没有演唱,完全不能进入到歌舞世界的女性共通,只是在公益组织的社会工作身份中疲于应付,艾米莉亚更要带着孩子,被迫伪装成“姑姑”。
歌唱与否的差异让二人的女性互助共通不复存在,女律师更是此刻的极度失败者,而艾米莉亚也同样不能“完美”,平行剪辑强调了其生活的两面性,纯粹女性的圆满只是其中一半。
歌词之中,她向遗孀承认自己有孩子,却是“他们的姑姑”,埋下了二人爱情之中的谎言,隐瞒男性过往。
这也契合了其与遗孀相爱、合唱的场景情况。
虽然由昼夜更替的伪长镜头,具有了一定的现实连接感,但终究是观众皆知的伪长镜头,是对剪辑的巧妙处理,时间流动的加速也揭示了其不属于现实的状态,最终回到了绝对现实的维度之中。
镜头切到了二人房间的外景,再逐步拉远,强调其之于整体环境的从属,将之落到绝对现实的贫民窟之中,暗示着女性在现实社会里的未能脱离、仍处“底层”,原因正是艾米莉亚对男性自身的未能剥离、洗清,将之带入到了房间与爱情之中。
属于女律师的“另一半”对接着艾米莉亚作为男性毒枭、拥有并追求地位与财富的过往,只有承认这一半,才能赎罪而解决这一半,随之让她与遗孀的“女性”另一半成为生活与心灵的全部。
在艾米莉亚的面前,女律师是承载其男性毒枭一面的存在,也让女律师自身处在了非纯粹女性的状态之中,与艾米莉亚的关系、对其的诉求,始终是男性世俗的物质名利、甚至“暴力借用”,大于对其向往女性之心的理解、女性之间的心灵互助。
因此,她必然地被艾米莉亚判定在了“名利”的环境之中,被告知“你自己创造了现在的一切生活”,限定在办公室里,无法脱离出去。
在这个阶段,女律师坐在办公室中,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够高的名声,似乎是她对外事业的成功,也达成了“超越男性,扭转性别劣势”的目标。
但是,这也让她终究无法脱离世俗社会、名利身份“律师”,而这一环境恰恰是由“男性先天强大力量”之准则所主导的存在。
她的一切都得自于艾米莉亚作为男性时期的权力、金钱、暴力,特别是作为“先天不可逆力量”之象征的暴力,在片中始终归于男性,暗示着其生理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以此指向了性别优劣的不可逆,而艾米莉亚的权力与金钱也都基于暴力而成就。
作品迅速推进了女律师的自我认知,她看到艾米莉亚的“男化”公益事业与犯罪团伙合作,导致其对“男性时期犯罪”的赎罪不可实现,也动摇女律师对此的成功获得---仍存,表达了对如此虚假成功事业的不满,又被艾米莉亚以男性口吻去强调“事业”本身(而非更女性思维的“心灵关怀”),并被限定在了对外事业身份的办公室。
如此一来,她也就“脱离”了女性心灵激发的音乐世界。
她走进歌厅,迷幻的光线成为了此前歌舞段落的升级,即架空歌舞世界的现实化落地,但一切却与她隔绝开来。
她来此与男性犯罪者接洽,镜头再次对准了后者的嘴部特写,金牙带来了暴力与物质的观感,也同此前男性艾米莉亚的处理一样,弱化个体,强调了其作为男性的性别属性,且带着对反打镜头中女律师的强势威压,获得了更大尺寸的特写,以及对话语权的掌握:二人都在说话,男性却是更有力的输出者。
并且,二人的话语被淹没在了整体的音乐歌舞声中,男性只张嘴而未见其声,正是二人所处的男性主导环境之于此“歌舞空间”的隔绝。
作为歌舞的主体,毒枭妻子与其情夫成为了段落中的最强力内容,且落在了女律师的眼中,作为其主观性的存在而出现。
雅克欧迪亚将其处理成了带字幕的音乐MV的形式,与现实舞池中的“二人共舞”相结合。
MV是现实情境里的音乐,其内的毒枭妻子得到了自己作为纯粹女性的爱情圆满,歌词重复着“做最原本的自己”,对比着艾米莉亚与女律师的“男女属性混杂”,而妻子身后的镜子带来了其多重身影,最终归于现实舞池中的“唯一情爱女性”,由此强化了其此刻作为纯粹女性的圆满。
然而,这一切成为了女律师眼中的画面,MV世界是客观定性中的“现实里音乐呈现形式”,于女律师主观而言,却是之于其所处歌厅情境的架空存在,而她也只能旁观其音乐表演,失去了前半部中亲身参与的资格。
这形成了丰富的表达。
只有摆脱名利世俗、回归纯粹的女性才能在现实里达成音乐与情爱,获得作为女性的心灵圆满与幸福生活,它以音乐MV的形式出现,又注定了其现实的相对局限性。
在段落的结尾,音乐歌舞被突兀地切掉,正是对其相对性的表示。
而在另一边,追名逐利、利用暴力与权势的女性则始终要停留在男性主导话语权、得到先天优势的绝对现实世界之中,甚至无法如妻子一样地实现相对暂时的圆满。
女律师与艾米莉亚在片中的状态始终是纠结的,前者先是恐惧于男性艾米莉亚的暴力与男性律师的压制,后又受困于自身事业成功依托男性犯罪暴力的虚无,而哪怕是变成女身的后者,也处在“作为女性而得到情爱”的音乐与“作为暴力犯罪使用者而注定无为地公益活动”的现实主义之间,对应着其出于父爱而接触家庭、女性“姑姑”身份不过是假冒的情感不圆满。
雅克欧迪亚落实了这一层的表达。
艾米莉亚的女化生活是女律师的最大成就,而前者自身的生活困境、无法摆脱男性时期的打扰,也就成为了对后者的撼动,强化着后者成就本身的“世俗男化追求”。
艾米莉亚与孩子们玩着滑雪游戏,虚拟的画面承接了音乐MV,带有强烈的“相对现实、暂时圆满”意味。
冰天雪地同样是妻儿们此前居住的环境,女律师在那里对毒枭妻子撒谎,妻子则体会着丈夫死亡之谎言带来的痛苦与孤独,二人对视时的消极、谎言打破了女性之间的正向心灵共通关系。
而在这里,雪天环境成为了艾米莉亚与孩子们的亲情圆满世界,落在“游戏画面”的相对现实之中,逆转了此前现实场景的消极调性,又带有相对局限的定位。
妻子随后回来,让艾米莉亚停下了游戏,发生了争吵,瞬间打破了片刻的圆满。
妻子不满于“姑姑”对自己孩子的霸占,而艾米莉亚则是出于原始的“父亲”身份,强调着“这是我的孩子”,他对自身男性身份的无法摆脱,由此导致的夫妻谎言、隔阂、冲突、对家庭的破坏,完全地爆发了出来他对妻子的暴力与威胁、居高临下的压制,让他回到了毒枭犯罪者的先天强力状态,压制着女性,而对妻子“你和你的皮条客”的下意识贬低,更是流露出了男性对女性的物化认知。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妻子在这里处在了绝对现实之中,与艾米莉亚的“离开滑雪游戏”一样,同样打破了其自身的“音乐MV”,从相对现实的短暂圆满中脱离出来,重新回到了“男性艾米莉亚部分”主导的世界之中。
这也体现在了她主观层面的变化之上。
她将艾米莉亚与女律师的关系定性成了“老同性恋”,既让艾米莉亚的性别混杂再次得证,也意味着其自身对“女性情感共通关系(同性情爱)”的贬低。
于是,艾米莉亚成为了“男性”,妻子也不再是完全对接女性心灵、可以理解共通关系的纯粹女性,各自回到了绝对现实里的男女优劣地位之中。
同时,妻子的“同性恋”表述,也引出了艾米莉亚情感关系的复杂化。
她被认知为“女性同性恋”,实际上却如同此刻爆发的男性本色一样,对女性的靠拢实际上带着男性的诉求,与女律师的接触始终围绕着暴力与权力,由此削弱了“变成女性”与“公益活动,洗清男性之罪”的效果,而哪怕是与遗孀的情爱关系,实际上也不免带着男性的异性恋需求,只是掩盖在了女同性取向的掩护与谎言之下。
由此一来,艾米莉亚的混杂也就再次升级。
此前拥有的局部纯粹女性部分被打破,归于并激化了男女认知交织的困境,带有了男性诉求与负面谎言,也意味着“局限性圆满”的终究毁坏。
在女律师与遗孀接触的段落中,这一点得到了直观的表现。
二人身处在整体黑暗的办公室中,打破了此前一贯的白天时段、明亮光线,意味着其作为公益组织、洗清男罪之地的不可达成。
作为艾米莉亚“男女部分”的女律师与遗孀在这里合一,却并未形成积极的共通。
二人谈论着艾米莉亚对彼此的情感表达,她关怀女律师,认可其为“让自己得到幸福”的关键存在,也对遗孀敞开了“我关爱我的孩子”的真实心扉,但女律师也意识到了这些表达之中的不彻底、不圆满,她并没有带来艾米莉亚的真正完美“幸福”,艾米莉亚也没有对遗孀完全吐露真相,变性手术、毒枭身份都被掩去。
因此,女律师看到了艾米莉亚作为纯粹女性、与遗孀建立女性共通的不完美,依然要用谎言去掩盖毒枭男性与孩子父亲的身份、避免与对方反目成仇,这本身也形成了对她自己“事业成功”的推翻,意味着其在男性名利社会中诉求的终不可成,而她又无法对遗孀言明一切。
女律师与遗孀,二人各自与艾米莉亚,三组女性关系都不再纯粹与圆满,也削弱了女律师与艾米莉亚作为女性的纯粹度。
段落落在了女律师意识到这一切的沉默之中,正是此刻她感到的绝对真实世界,即“公益组织办公室”环境的虚假美好打破、黑暗笼罩流露。
而在她接到艾米莉亚被绑架的通知、彻底陷入“男性主导犯罪世界”现实的时候,她与遗孀遥遥相望,其构图还原了此前艾米莉亚与遗孀激发爱意时的一幕,心灵共通却从积极的情爱转为了消极的恐惧。
在结尾的阶段,雅克欧迪亚直接带回了最根本而直观的”男性力量”要素,即暴力犯罪,由此揭开了男性做主导、输出给女性的世界真相,也由其破坏性而强调了这一世界的混乱、黑暗定位,揭穿了此前在表面上的流光溢彩、觥筹交错、有礼有节,让它变成了男性的“道貌岸然”。
艾米莉亚带有男性的部分,让他必然地强调对妻子的“物化占有权”,并进一步地付诸于其安身立命的犯罪手段,绑架、威慑了对方的情夫。
而她又带着女性的部分,因此终究是有所软化,对情夫只是威胁而不赶尽杀绝,反过来让自己被纯粹男性的对方所击败,成为了对方暴力手段的承受者,女性的肉体“手指”被暴力切下,并成为了男性口中“价值多少钱”的物质化表述对象,形成了非常直观的“女性被物化扭曲、男力承受”。
这也让女律师与妻子彻底卷入了暴力犯罪的男性世界之中。
女律师被迫处理艾米莉亚绑架事件,而妻子也愈发明确地在现实中难以保持纯粹,出于捍卫爱情的目的,却只能依赖于男性情夫的暴力犯罪手段,与女律师的“依靠艾米莉亚暴力与金钱”走上了同路,其诉求也必然与女律师的“获得男性世界中成功”一样,归于男性世俗语境:艾米莉亚的“男性思维”让他采取手段,剥夺了妻子的经济能力,而妻子也由此落入了“捍卫物质财富”的世俗窠臼,曾经“冲破黄金牢笼”、只求纯粹爱情的心境被打破了。
在这个阶段,雅克欧迪亚改变了音乐的属性,让它成为了男性主导、黑暗现实的呈现媒介,也正是对此前“MV之相对现实圆满”的再延伸。
前半部的音乐有着不同程度的架空化,最终成了“底层人大合唱的虚拟星空”这一完美达成情境,再过渡到MV的“相对现实化”,与现实的距离缩短,随后则是MV“音乐呈现”被打破,即“达成”的失败,进而来到了最终的绝对现实阶段,音乐世界本身的“被男化改变”。
在这一阶段,音乐成为了愤怒的表达途径,这种愤怒最初是女律师对男化社会的情绪,在最终阶段的发出者却变成了“男性”,由此推翻了此前“女性反抗既有社会”的升级形式,看上去是女性反抗之力的增幅,实际上依然是归属于男性语境的“暴力”,并未完全超出男性世界的范畴。
这延伸到了后续的情节,女律师只能拿起枪,用曾属于男性毒枭的暴力犯罪形式去捍卫自己与“女性艾米莉亚”,以此为基础的彻底对抗也在面对男性火力的时候失败了,女律师只能抛下抢,躲到掩体后面,也无法挽回艾米莉亚与妻子的死亡。
女律师接听艾米莉亚的电话,后者正是作为丈夫而爆发着男性之怒,强调“要妻子好看”。
女律师联系了妻子,接收了妻子一方的女性愤怒,同样围绕着“物质财富被剥夺”的既有社会思维,让其成为了不纯粹于情感心灵的“男性包养金丝雀”。
在这一段中,女律师与艾米莉亚的二人并立画面率先出现,女律师居于左侧,是“女性”,随后又被更加“纯粹女性”的妻子所替代,自身去到了“男性”的右侧,最后则是三人并列的画面,女律师夹在了男性与女性的中间,对双方百般协调,却终究无法让彼此和解,也意味着其自身在男女化心境之间的无法自洽调和,归于其心力交瘁的状态。
而艾米莉亚的女性外形,妻子对物质财富被剥夺的愤怒,也让二人各自成为了不纯粹的男与女。
作为对此混乱与扭曲的表现形式,欧迪亚使用了音乐,三人表达着基于性别混杂困境的负面情绪,其言语化作了有节奏的说唱,对应着前半部里属于男性的“干唱”念白。
前半部里的“男性现实”回归,其对音乐的“扭曲”扩展到了女性的身上,意味着其的主导力,也导致了女性曾经“美妙歌唱、抒发情感心灵”的被扭曲,在内容与呈现上都趋于消极。
在最后的结尾阶段中,音乐的演唱状态引出了呈现舞台的同等变化,由此形成了对女性现实出路的短暂建立与再度否定,即对“音乐构成世界”本身的彻底推翻。
女律师决定召集艾米莉亚的犯罪集团去反击,拿起了暴力极致形态的枪,意味着其立足于男性世界、暴力规则、反击男性主导地位的巨大变化,从妥协让步、互利合作变为了彻底的愤怒对抗。
这似乎意味着她的质变,此前始终依赖着不同的男性,从毒枭时期、变性后继续给到物质回馈与世俗资源的艾米莉亚,到上司男律师,再到能支持自己的诸多男性,但到了这里,她终于意识到了男性在现实中对女性的必然压制、逼迫,女性依附他的结果必然是无法翻身的弱势,由此自行举起了武器,试图与男性彻底对立,以对方的游戏规则,站在对方的现实世界之中,完成彻底的逆袭革命。
但是,这终究还是在男性主导世界之下的努力,反而承认了暴力这一现实世界中根基的不可逆,只有依靠它背后的“男性毒枭之犯罪暴力”才能行动,而暴力象征的“生理力量”正决定了男性的先天优势,定义了现实世界中主导者的确凿。
女律师只能用它去反击,恰恰是她对当下现实世界之唯一性的承认,因此也必然会失败,本身已然放弃了隔离于此的纯粹女性身份、有别于暴力物质等世俗存在的情感心灵。
她必须运用暴力,而暴力对应的犯罪正是无可改变的黑暗存在,是对现实世界之沉沦的加剧,不可能带来任何改变。
由此一来,结尾阶段的音乐场景也就成为了男性主导、女性弱势的暴力呈现平台,是女性心灵世界被男性规则现实彻底占领、改变的结果。
在艾米莉亚绑架情夫的段落中,手持DV、粗糙画质的现实主义风格延续了此前的现实世界部分,也打破了女律师此前获得主导权的“新闻画面”情境,让其再次回到了艾米莉亚男性部分的命令与意志之下。
而当艾米莉亚被反绑架,女律师召集人手、以暴力做反击的时候,画面风格则变成了音乐的一方。
在音乐开始之前,画面的剪辑始终伴随着后退的运镜,将之顺畅地连通起来,其流动性正是音乐段落中的呈现特点,而众人讨论反击作战的话语也成为了“干唱”的嘻哈,交换枪支的动作更是带着节奏感,成为了舞蹈。
在这里,歌舞场景完全落在了现实情境之中,似乎意味着其之于女性“心灵圆满”的落地,实际上却恰恰相反,镜头从办公室外面出发,让办公室里的热火朝天被笼罩在了黑暗之中,其内部的顶光是前半部里音乐舞台的打光方式,却在现实情境中被削弱,成为了极其局限的”光明”,对应着演唱“抒发心灵情感”的干唱之扭曲压抑。
在结尾的部分,女性的音乐并没有改变、进入现实,而是男性主导的现实改变、同化了女性的音乐。
女律师与女性暴力者交换枪械,也成为了对方。
在随后的作战中,欧迪亚更是将这一点扩展到了艾米莉亚与妻子的身上。
黑夜中战车行驶的镜头是对前半部里“女律师被带去见毒枭”的再现,女律师似乎转成了主导者,却依然处在其整体情境之中,只带有车灯给予的些许光亮。
在作战中,她高举着枪,却终究没能射击,被迫躲在掩体的后面,被情夫的火力所压制。
而在艾米莉亚与妻子的一边,二人似乎终于达成了极致的和解。
雅克欧迪亚精妙地定位了这一段的内容。
二人从纯粹女性的情感角度出发,围绕着爱情萌生的时刻,又由此达成了一种超越性别壁障的结果,艾米莉亚对妻子的爱是作为丈夫的男性立场,又摆脱了夫妻此前的“物质给予”成分与“地位优劣”实质,罕见地作为男性而褪去了名利与力量,只专注于爱情部分,这又对应了他此刻的女性之身。
因此,艾米莉亚与妻子的和解与共通,同时具有了男性与女性、女性内部的双重性,又让艾米莉亚自身调和了男性与女性的部分,形成了内在共通,男性部分的“女化”。
作为其抒发形式的,正是终于回归的完美演唱,如同前半部中专属于女性之间的完美合唱。
并且,这也意味着艾米莉亚对自身男性毒枭过往身份的承认,这正是他解决与妻子误会、根除父子家庭隐患的关键,也是面对遗孀而坦诚、洗清其男性暴力之罪的关键。
这带来了艾米莉亚一直期盼的“救赎”。
在他中枪倒地、似乎将死的时刻,女律师看到了“神迹”,艾米莉亚一家曾经只能遥望的高空云朵似乎落了下来,凝聚在艾米莉亚的身上,成为了上帝给予的救赎,带给她极度具象的“重生”。
此前承受暴力的死亡成为了罪孽的赎清,随后则是从零开始的新生命,作为纯粹女性的存在,也投注了照亮黑暗世界的上帝之光。
但是,这一切依然没能持续下去。
雅克欧迪亚几乎是“仓促”地了结了一切。
合唱被情夫打断,妻子与艾米莉亚的“共通”对视被后备箱门打断,妻子想要捍卫丈夫地拿起了暴力之枪,也被情夫居高临下的“婊子”与掌掴暴力所打断。
在最后,雅克欧迪亚更是极度地升级了“暴力”与反向的“救赎”,将之完全归于黑暗的现实主义情境之中。
在现实化的世界里,“上帝”的意志引导了意外的车祸,所有人也都归于不可逆的死亡,这才是现实中唯一的“救赎”方式,让女性承受暴力,以毁灭于此的绝对消极方式得到解脱,而此前的“确切重生”不过是暂时的幻象而已。
在这一切不可逆悲剧之后,“上帝”才能带来些许的转机。
女律师取代了艾米莉亚夫妻的“母亲”身份,与二人形成了冥冥之中的女性共通,接纳了后者的子女。
由对方的死亡,她才能解除与对方的“毒枭与律师合作”关系,让自己走出对方的“男性毒枭”的恐惧与阴影,也摆脱了“律师”的身份,不再追求对方已然无法给出的物质名利,激发彼此之间作为纯粹女性的情感共鸣,自发而无功利性地帮助对方子女,也连带着对艾米莉亚妻子的帮助,成为了女性“母亲”。
同时,艾米莉亚的灵魂也终于得到了现实世界中的救赎,遗孀高举着耶稣的圣象,为她演唱着神圣的宗教之歌,请求耶稣洗清其有罪的灵魂。
这是绝对现实之中的音乐,再次得到了正面的复原,而艾米莉亚也成为了歌词里的“她”,男性暴力之罪得以洗清,也与遗孀达成了跨越阴阳分界的女性共通,“同性情爱”,只是一切必须通过生命死亡的途径,借由死亡才能得以“回归纯粹女性”。
雅克欧迪亚处理了此处的耶稣神像,让其与艾米莉亚的形象极其相似,正是对艾米莉亚最终寓意的表现。
艾米莉亚想要借助上帝之力去洗清男性之罪,获得纯粹女性的出路,这意味着其自身在两性之间的完美调和、达成自洽,也是男性主导基础之身的“女化改变”。
这外延到了社会的层面,正是男性主导之唯一现实社会的改变途径,从根本(生理)上改变“男性”这一生基,由此扭转男性主导的“男尊女卑、力量高低”铁则,实现女性的可持续出路:无需妥协、契合男性主导规则,不必强行融入现有社会,去承受必然的性别弱势与努力失败,而是以纯粹女性、忠于本心的状态下,实现作为女性的原始诉求,得到情感心灵的圆满,绝对忠实于女性自身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让自己扭曲为男化的认知。
因此,当“男性”艾米莉亚得到自身调和、洗清男性之罪、成为“男女完美交融”之人的时候,她也就成为了其象征的现实社会的指引,成为了现实中人的耶稣,以自身死亡而登上了“十字架”,承载并消化了现世之罪。
在结尾的段落中,男性与女性共处一堂,完美合唱,正是艾米莉亚之死引导、促成的现世之改变。
底层人们合唱,正是此前架空情境下“受难者家属们合唱之星空”的绝对现实化再现,艾米莉亚此前难以实现的“男性罪孽洗脱”,在死亡的结果中终于清偿完毕,也让他对底层群体所处的阶层化社会---“男尊女卑”为代表的多层面物质分配不均---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给底层人带来了心灵的安抚。
最后一个镜头中,艾米莉亚佩雷斯作为“混合两性身份”的终极身份,与耶稣像一起出现,正是对影片本身与其主题落点的强烈宣示。
但即使如此,雅克欧迪亚依然有所保留。
底层人们得到的终究只是彼此之间的慰藉而已,无助于对绝对客观、整体社会中自身处境的质变。
女律师的结局也是如此,对艾米莉亚和其妻子形成了个互助,但对外部男性社会的“愤怒反抗”依然无果,男性主导、资源分配、物质功利化的世界依然是“唯一现实”。
由此一来,雅克欧迪亚对现实世界的观点,也就落到了一种微妙的状态。
立足于性别极度对立、女性主义过激、大男子主义“超雄”又极度膨胀、两性均秉持“不过度就无重视”的混乱当下,他的理想是两性冲突的调和,当下的性别极度对立局面逐渐好转,却也并非完全乐观,认为改变必然要经历伤痛,承受沉重的黑暗打击,当下的冲突会导致不可逆的巨大负面结果,随后才能让世界去痛定思痛,但即使如此,女性优化与两性平衡的可持续性未来也依然只是理想而已。
伤痛与损失成为了现实里的“耶稣”,其死亡是悲剧,也是不可或缺的必然过程,最终却难以实现完美的整体质变结果。
本片的风格、内容、主题、手法对此同样有所反映。
它针对现实,承载当代世界中多层面议题与冲突,又呈现以“变性、犯罪”等非普遍性形式,在现实主义与歌舞音乐的两种风格中切换。
后者成为了前者的理想国,而前者则是对后者“不可普遍而广泛达成”的明确,共同引出了暧昧的结尾:即使是本身已然虚无缥缈的“上帝”,依然只能在现实里给出心灵层面、内部局限的圆满而已,“心灵抚慰、情感价值”也正是宗教在客观当代现实里的主要作用,对应到电影世界观中,其本身也只发生、有效于女性群体的内部而已。
它显然立足于现实语境,是创作者对当代议题的讨论与观点输出,它指向了乐观与悲观混杂并立的落点,也被创作者延伸出了多层面的对等指向,既对应着男性与女性的具体主题,也由“积极面未来”、“女性圆满情感心灵”的音乐歌舞与“消极面当下”、“男性压抑女性主观体验”的现实主义,完美地契合在了一起,始终维持着多层面的切换、穿插,在彼此独立割裂、相互融会交互的状态之间持续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看,《艾米莉亚佩雷斯》契合了奥斯卡的某种需求。
大胆猜测,奥斯卡想要强调“电影”艺术形式之于短视频的独特魅力,这个艺术的根本,即影院加持的深度沉浸,以此作用感官体验,所形成的输出。
太多人认为电影只是讲故事,所以可以被更简练、更浓缩地“讲故事”形式---短视频---所取代。
所以,奥斯卡要强调“电影”在影院设备+黑暗环境+持续观赏中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深度沉浸、直观感受性。
隐约之间,学院似乎带出了一种对这个艺术门类的历史使命感,而雅克欧迪亚会在这个作品中选择这个风格去转型,可能也有这个意思,从而与奥斯卡心有灵犀,领跑提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8 ) 《Emilia Perez》观后感
刚刚好在澳洲露天影院处上线,才看完整体感觉还是蛮不错的镜头表现能力很好,引人入胜,穿插的一些音乐歌舞元素来描绘人物内心想法,但个人还是不太喜欢这种中间穿插的音乐歌舞元素,中间的某些段音乐还挺难听挺尬的主题立意感觉还是蛮多的,重点集中在变性主角身上,rita作为第三者又身处中心贯穿整个剧情,人物作用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作家,作为一位女性律师,第一个情节或许能解释后期为什么选择和Emilia保持合作并且感情加深而作为影片题目的Emilia而不是Manitas,说明侧重点还是在变性后的女主。
首先,这个主角人物本身就很有争议性,不能说她是个好人,因为变性前做了很多坏事,即使变性后做的这个慈善工作为墨西哥找寻失踪人口与他们家人团聚,还是不能否定她之前所作的一切。
其次,Emilia既然已经决定成为Emilia了那就应该与之前的一切断绝,当时做手术前都说了要无人认识,那也说明决定好变性就是重新开始,说难听点就是抛弃妻子孩子来选择成全自己的新生,干嘛后面又非要以姑妈的身份来和孩子呆在一起,所以从这里开始,结局其实都可以预见了。
怎么可能一切都如你所愿,既可以和孩子永远呆在一起又能作为一个女人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后面这段“half”的音乐其实也能表现出她的想法吧对于Selena饰演的这个人物:最后Emilia坦白的时候,她本可以假装不知道,然后放弃这个“过去的老公”,和男人结婚过新生活,却还是选择救Emilia,在争执中三人一同死亡,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她对Manitas的爱是很深的,她也很依赖他,即使他后来变成了Emilia还是选择救她。
整体来说,影片看的很顺,内容题材对我来说都比较新颖,所以还是给出偏高的评分
9 ) 当权力穿上蕾丝:《艾米莉亚·佩雷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将墨西哥毒枭传奇缝制成一袭荒诞的蕾丝长袍的毒枭变形记。
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墨西哥大毒枭,为了真正做回自己,决定冒险进行变性手术并伪造自己的死亡,以此退休、销声匿迹的故事。
这一设定极具颠覆性,打破了传统黑帮片的男性霸权框架,将跨性别者的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置于聚光灯下。
主角艾米莉亚(由卡拉·索菲娅·加斯科恩饰演)的变性之旅,不仅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更是对自我解放的呼喊。
影片的叙事节奏紧凑,情节跌宕起伏,既有紧张刺激的犯罪情节,又有温馨感人的家庭伦理探讨。
歌舞元素的融入,为影片增添了一抹亮色,使得角色们在深陷毒枭黑暗世界的同时,也能跳出华丽的舞蹈,展现出一种反差感。
这种风格的融合,既是对传统歌舞片的一种致敬,也是对犯罪片类型的一种创新。
演员们的表演也十分出色。
卡拉·索菲娅·加斯科恩凭借精湛的演技,成功塑造了艾米莉亚这一复杂而深刻的角色,从毒枭的暴戾到变性后的脆弱,她用细腻的眼神与肢体语言诠释了身份转变的阵痛。
佐伊·索尔达娜、赛琳娜·戈麦斯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也为影片增色不少。
然而,影片也并非完美无瑕。
部分观众指出,突如其来的歌舞打乱了叙事节奏,尤其在犯罪主线的高潮部分,抒情性歌舞与血腥暴力场景的并置显得突兀,削弱了剧情的连贯性。
此外,影片对跨性别议题的呈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部分台词与情节被批评为对当代性别认知的滞后。
总的来说,《艾米莉亚·佩雷斯》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影片。
它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刻的主题探讨和出色的表演,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关于性别、身份和自由的深刻思考。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和不足,但影片所传达的信息和理念仍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10 ) 在戛纳电影节上,她连续获得十分钟掌声
文/整理/翻译/封面图:深秋小屋部分配图:karsiagascon、teenvogue.com、豆瓣封面图来源:豆瓣参考资料:festival-cannes.com、维基百科、imdb.com注:点击文中“超链”跳转到另一篇关联小屋推文。
Emilia Perez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中。
5月19日那天,由Zoe Saldana、Selena Gomez和Karla Sofía Gascón主演的西班牙语音乐剧《艾米莉亚·佩雷斯》(Emilia Perez)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后,获得了雷鸣般的起立鼓掌。
Selena Gomez, Zoe Saldaña, and Karla Sofía Gascón,©DOMINIQUE CHARRIAU现场爆发出长达十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成为戛纳电影节的亮点,这也是本届电影节上映的电影迄今为止获得掌声最久的一次。
Selena Gomez感动得热泪盈眶;法国导演Jacques Audiard在热烈的掌声中挥舞帽子向观众致意。
而献给主演之一Karla Sofía Gascón的掌声尤其响亮。
【点击查看相关现场视频】Karla Sofía Gascón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贩毒集团的跨性别头目。
影片讲述了生活在墨西哥城的丽塔(Zoe Saldana饰)是一位资深却总被行业低估、排挤的律师。
一天,丽塔被贩毒集团头目马尼塔斯(Karla Sofía Gascón饰)雇佣来帮他金盆洗手,马尼塔斯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帮助他带着孩子和妻子杰西(Selena Gomez饰)逃离墨西哥,并让他完成手术成为一个女人,这样“她”就能以女性的身份生活。
影片《艾米莉亚·佩雷斯》 (Emilia Pérez)首映后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这部喜剧犯罪片在烂番茄上获得了86%的评分。
《滚石》杂志点评《艾米莉亚·佩雷斯》:“无法用文字真实描述出银幕上的疯狂”。
《名利场》点评:“导演Jacques Audiard坚决拒绝把它当作一个喜剧——这是真诚、感伤的电电影创作——事实证明它完全赢得了好评。
”《名利场》还补充道:“以前讲述跨性别的电影,比如《Girl》、《丹麦女孩》,都关注‘跨性别本身’,而不是关注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梦想的人。
“
《Girl》
《丹麦女孩》电影《艾米莉亚·佩雷斯》探索了跨性别转变后如何成为社会新角色的一部分。
正如一位观众观影后写的那样:“一部跨性别、音乐、犯罪、惊悚、爱情片?
是的,这是一部杰作。
”
作为一位跨性别女演员,Karla Sofía Gascón在电影节上对记者直言不讳地谈到跨性别群体所面临的普遍偏见。
我们只是普通人……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受到尊重。
Karla SofíaKarla Sofía Gascón,1972年3月31日出生,是一位西班牙女演员。
她在改变性别前就已经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包括《El Señor de los Cielos》和《The Noble Family》。
2018年9月,Karla Sofía Gascón推出她的自传书《Karsia》,宣布自己是跨性别者,并将名字改为Karla Sofía。
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一个名叫Juan Carlos Gascón的帅气男生。
©karsiagascon/Instagram事实上,Karla Sofía Gascón是从2016年开始转型为女性的。
她对媒体说:“这是我从四岁起就一直想要实现的事情,问题是我出生在70年代,在我青年时代没有办法实现,当时的医疗水平也做不到这一点。
”Karla Sofía Gascón承认,一开始,她的父母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看待她,但后来他们慢慢理解她,并给予了她所有的支持,现在,她的母亲还会经常在朋友面前夸赞她。
在Karla Sofía Gascón还是Juan Carlos Gascón的时候,就结婚生子了。
在经历了艰难的变性过程后,Karla Sofía Gascón表示,她与妻子Marisa之间的问题也慢慢改善。
Karla Sofía Gascón和妻子Marisa ©karsiagascon/Instagram她透露,对妻子来说,最复杂的事情之一就是接受“丈夫”的身体发生变化。
虽然转变的过程很复杂,但她对媒体透露,她从未与爱人分开过。
“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哪怕是一个月,现在,我俩经常会一起在沙发上看电影、照顾我们的女儿Victoria Elena,以及家里人。
”她说。
我们认识快30年了,我和她一起生活的时间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我爱她。
Karla Sofía Gascón和妻子Marisa、女儿Victoria Elena一起旅游 ©karsiagascon/Instagram✪目前,电影《艾米莉亚·佩雷斯》已经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非常有希望摘得本届金棕榈奖。
影片已定于在2024年8月28日法国上映。
别忘了,这是一部音乐喜剧类影片(演员在正常讲台词时,还时刻需要歌舞表演)。
点击观看《Emilia Perez》预告片*本文部分翻译参考原文网址:https://www.arabtimesonline.com/news/selena-gomez-cries-as-emilia-perez-earns-biggest-cannes-standing-ovationhttps://www.telemundo.com/entretenimiento/2019/10/31/actor-transgenero-de-nosotros-los-nobles-sigue-viviendo-con-su-esposa-tmna3570286?image=9044005https://www.thepinknews.com/2024/05/20/masterpiece-gangster-trans-musical-emilia-perez-canneshttps://www.tvynovelas.com/famosos/karla-sofia-gascon-antes-y-despues-actriz-trans-que-critico-a-wendy-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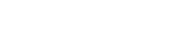


































一个渴望变性的大毒枭和一个善于帮助罪犯脱罪的律师携手合作,共同演绎了这部带有浪漫主义成人童话色彩的犯罪惊悚歌舞片,已经结婚生子的大毒枭在律师的帮助下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性别,实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梦想,然后金盆洗手,弃恶从善,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死于非命的结局(既可以说是因为自己对原来的妻儿的牵挂而死,也可以说是因为自己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而死),“毒王女人梦”这个译名可以很好地传达这部电影的精髓。作为一部以跨性别者为主角并且涉及犯罪的电影,本片的题材看似有着比较大的尺度,但是具体的故事内容的尺度其实并不大,故事的核心主题则是对跨性别者的生理性别、心理性别、社会身份的探讨。不过,这种故事完全没有必要拍成歌舞片,歌舞元素反而成为了本片的累赘,本片中的舞蹈真的很难看,那几段半说半唱的台词也很出戏。
混乱、奇情、狗血…性别流动、身份认知、各种类型片元素杂糅在一起,观感不得不说奇特,看得人很high。似乎有点明白戛纳四黄蛋影后的用意,影片里的四个女性角色其实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女人,一个睿智、感性、敢爱、敢恨、自爱、自艾的女人。你甚至可以说她一个凌驾于性别之上的人。
欧师傅玩这么大,应该更疯更彻底,还是太拘束了这样反而不伦不类。
没看明白怎么就集体戛纳影后了
欧洲文艺片导演致敬墨西哥肥皂剧?堪比朋克教母追古偶了。认真说,如果搬到舞台上改成音乐剧其实可以。
这么奇情的剧本怎么能拍得这么无聊
+.5
西班牙语的歌舞片段挺带感的,剧情也是真的很狗血,但比起俗套还是略偏精彩一些。要说为啥会给四星,可能是因为还是能感受到一些生命力的存在吧
儘管是變性人的熱門主題,從故事到技巧都極富創造性。歌舞片本就更戲劇化,簡單粗暴的情節和光怪陸離的美工在我看來也是刻意經營的感官衝撞。有人說這對拉美文化不公平,但它本就是外人視角的剖析吧。女主女配的演出非常不錯。
奇情得如此清新自然,绝
我的老天 作为一部歌舞片也太难听了
这看得可是忒不得劲儿了,女主角费老鼻子劲儿金蝉脱壳结果有勇无谋,“她”的双商之前真的够当黑老大吗?真正负责又唱又跳的女律师怕不是才是真女主。这片子真的爱女主的怕不是也只有女律师。不知道有傻脸娜,角色并不讨喜。总而言之,是一个题材吸引人但是拍完了不如不拍的电影。
一整个大锅炖,将多种元素,毒枭、变性、歌舞、同性、改邪归正等不和谐地融于一炉,并还以过于狗血降智的情节力求博得观众感动,编剧水平简直不能再低。除去应和了当今人口失踪的国际热门话题外,(这种应和甚至也是以一种过于刻意生硬的方式),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自然也看不到值得获奖,甚至值得一看的成分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迪士尼
我理解美国排这种土嗨片,我也理解有人喜欢有人讨厌。我不理解评论区那么多说着难看挑出各种犀利的毛病的人,为什么都打三星?三星是及格分数但是你们评论明明都和我一样应该是1星啊…….
3.5//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得很开心//用歌舞段落建立类似舞台剧式的人物内心独白 也不算完全浪费特殊元素的介入//不过整体故事的感觉像是娃娃屋 人物则是像扮家家酒一样的分化和割裂//我大概就是喜欢看索尔达娜讲西语吧 有点性感
这剧情到底是什么鬼,转折转得莫民奇妙,一个变了性的黑帮大佬突然去做慈善就算了,当她回馈上帝,突然又跑去谈恋爱,啪唧,又被绑架了~~~~本来觉得大佬变女皇是个有趣的设定,接着南美这天选的魔幻属性真的逃都逃不掉,以至于奇葩歌舞都不那么奇葩了。八一八,我也是很久没关心欧美娱乐圈了,selena gomez都成大姑娘了,不敢认。
喜欢前部分,从爽文节奏开始炮轰性别二元霸权,极尽渲染了顺直女和跨女的非刻板情节。但后面的洒狗血剧情太狗血了,感觉叙事套路还在五十年前……
开始觉得像是带有女性互助意思的狗血文,看到后面感觉就是一篇狗血文。一看就直男导演拍的同类型的电影永远比不过阿莫多瓦,无论是从狗血离谱程度还是人性剖析深度。一个毒枭变性出票子行善就可以洗清过去罪孽被人歌颂了?对妻子发火本来以为剧情要有点意思了,结果还是还是被一场莫名其妙的枪战糊弄过去了。本来以为会在妻子身上对故事进行反讽,没想到妻子开始是婊子到死还是婊子而且有用歌舞片段替代叙事来推进情感之嫌直男伪装成圣母但其实就像开头医生说的,尽管生理上变性,灵魂深处he依然是he。他永远无法理解女人,没有作为一个女性的去思考。而且他甚至没意识到这一点,最后还被作为一个殉道者一样被人膜拜。要说这是女性主义的话那简直是对女性主义的双重侮辱。虽然感觉导演志不在表达女性主义,但我也不知道他志在何处😅
OST挺好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