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剧情介绍
本片根据雾社事件史实改编。 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后,日本遂即武力接收台湾,宝岛各地纷纷被攻破。而台湾山区因道路不通,原住民生活尚暂未受影响,雾社地区的赛德克人之中,马赫坡年轻一代的莫那鲁道(游大庆 饰)英勇过人,率族群与甘卓万人争斗不休。日人垂涎雾社地区的 丰富资源,试图染指但遭到赛德克人强烈抵抗,伤亡惨重,然终于借原住民族群之间的互相仇杀侵入了雾社。莫那鲁道只得忍辱投降,但心中的火苗从未熄灭。时间推至1930年,日本对于雾社原住民的“文明改造”历经多年,日语等所谓文明并未给予原住民平等的生活,日人的欺压和繁重劳作侵蚀着赛德克人的传统和尊严,多年的愤怒累积,终于在这一年全面喷发!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路西法第四季现场清理人第四季被驱逐开勇者派对的白魔导师,被S级冒险者捡到~这个白魔导师超规格~回家看看欢迎光临二代咖啡我是刑警十万分之一残值安检龙舞金瓶蕾拉扬琴手未见其形黄河喜事国家代表2亚人酱有话要说再一次初恋救世超能:永无止境你好乔安请赐我一双翅膀你让我雄起宝宝进城乐咒滑板厨房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第一季齿轮上的时空糖亿人局之迪拜贱客亲爱的吾兄朱莉快逃侯府小千金
《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长篇影评
1 )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历史真相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197637-gb2312.html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
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
”——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
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
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
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
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
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
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
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
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
”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
“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
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
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
《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
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
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
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
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
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
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
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
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
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
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
请收我为军夫。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在当时。
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
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
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
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
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
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
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
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
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
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
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
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
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
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
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
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
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
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
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
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
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
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
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
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
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
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
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
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
”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
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
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
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绝不装逼”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2 ) 焦灼的文明
当我听说《赛德克•巴莱》两部长达四个多小时,还担心自己是否扛得住这个长度,会断断续续把这部电影按照电视剧的节奏看完。
但是真正看起本片时,这种担心显然多余,这是一部故事上连贯精彩抓人,思想上又剖析深入但留有余地的佳作。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华人大作了,说它是什么《勇敢的心》、《阿凡达》台湾版,那是扯淡,与这两部纯英雄主义的电影相比,《赛德克•巴莱》有着更复杂和立体的思想元素,这成就了它的优秀,但是,也多少阻碍了它的票房。
魏德圣在接受《看历史》采访时,谈到为什么选择了“雾社事件”这段历史,一大原因就是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事件是有些“反常”的。
正如片中所述,台湾抵抗日本人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马关条约”后,日本人刚登岛的几年,当地几乎被抛弃的汉人与原住民尽管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都与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影片对莫那青年时代的刻画在影片中其实非常重要,它不但表现了莫那的成长和性格,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表现了当地部落的文化和信仰,也为影片的风格和立场打下了基调:即并无刻意的称颂或贬低。
可以看到,影片在表现那段历史上并未一上来就将莫那塑造成神武的英雄色彩,也没可以歌颂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它一上来从莫那打猎,到与其它部落战斗,直到部落婚礼欢庆,又到他被在唇下打上勇士的烙印,一个当地文化的生态和信仰自然展现。
这是一个处于“野蛮”阶段的民族,他们颂扬英雄,对土地有很强的依恋和边界感,敌人的头颅是他们的骄傲,渴望以自己战斗的血祭铺就走向彩虹桥之路。
这个表现很客观,那种原生态的杀戮,嗜血感与此前很多此类表现文化冲突的“史诗电影”有很大不同,原本你以为这片会表现赛德克人抵抗日本人的可歌可泣事迹,没想到上来就是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包括莫那年轻时候的冲动、莽撞,甚至嗜杀。
但是,魏德圣又巧妙的将视角放在赛德克人的角度上,去做一种“纠偏”和平衡,因为在现今文明下的我们看来,这种部落间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为了些宿怨和斗气,就打打杀杀的举动实在落后和残忍,这是一种现代文明自然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而魏德圣的视角却从赛德克人生活过程,让你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在当时有怎样的理由,给出更多当时的情况,让观众再去判断。
可以说,“雾社事件”之前青年莫那阶段,这部影片的出众之处就已经展现,而莫那的形象也栩栩如生,让你可以在后面体会一个不羁灵魂被压抑数十年后爆发的缘起。
而“雾社事件”的“反常”之处在于,它发生于一个宏观上,当地人与日本人关系缓和的阶段,最激烈的冲突已经过去,正如影片跳过几十年后,两个日本官员看着建立了学校、邮局等文化设施的小镇,对“教化”成绩的满意笑容。
《赛德克•巴莱》最成功的一点便是在上部对这种背景下,个人身份的焦灼感表现。
莫那已经成为一个看上去桀骜之心收敛,理性的与日方博弈谈判,维护部族利益的长者。
但是,尽管当时的台湾已经处于表明的文明化阶段,但是原住民和外来者的在地位、文化上的矛盾依然存在,莫那常常要面对巴万关于为什么他因为优秀反倒被日本教师责骂的困惑。
而这种身份的焦灼更深的表现在被认为是“教化”突出成绩的花岗兄弟身上,而花岗一郎的表现尤其突出,作为比日本同僚更优秀的他,却依然承受着职业上不公正的待遇,被当作展品一般被日本人作为殖民教育的成就指指点点。
他要身负管理责任为日本人做事,管理自己的族人,同时又常常被自己的族人嘲讽,不耻,从一个个这种矛盾的场景到演员出色的表演,都让观众可以代入的体会到,一个姓氏日本化的赛德克人内心的痛苦。
他知道表明繁荣下的危机,他知道莫那内心潜藏的杀气,他知道自己同胞反抗的结局,他更知道自己在族人与日本家人间矛盾将带给自己怎样的命运。
莫那和花岗一郎在山谷溪流边的一段对话,可谓文明冲突的经典桥段,花岗一郎不解(或者说其实理解,但是为了说服莫那故作不解)的问着莫那,如今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大家依然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现代化的设施,孩子可以接受现代化的教育,而面对的又是莫那“被出访”日本时深刻体会的强大的武装力量。
莫那的回答可切中要害,面对所谓的现代化,一句“正是提醒着我们自己的贫穷”可谓振聋发聩,将征服者角度所谓的“教化”优越感直接剖析开来。
外表的和睦常常掩盖着内在的矛盾,毕竟,莫那他们面对的现代化冲击并不是以可口可乐这样的商业化方式为载体的,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枪炮与征服,间接面对的是歧视与不公。
莫那处于一个尴尬的结点,他身上有着上一代人的传统,又直接面对现代化的征服,他为传统被破坏,猎场被夺去感到屈辱,与后来直接接触现代化的人不同,他是有“历史负担”的人。
而对于日本人何尝不是,他们是有征服者和文明者的“心理负担”的人,内在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只是有的人彬彬有礼,与当地人有好相处;有的人粗暴暴力,与当地人势同水火,性格和人品的差异与这种优越感结合,在文化冲突背景下,最终制造了严重的冲突。
所以,那个无礼的“派出所”官员只是一个火星,他引爆的是一个积聚了太多火药的火药桶,一如莫那通过火柴头积攒的火药,每次一点点,长时间后,已经足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这种破坏力甚至已经近乎失控,以现代文明观点看,“雾社事件”中,莫那带领族人的表现可谓一种滥杀无辜的屠杀,而巴万带着一帮孩子把一群妇孺捅死的场面更是令人咋舌。
魏德圣就是这样,不回避现实,他告诉你赛德克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又不刻意美化,比如只是表现赛德克人与军方的战斗,他表现的是,一场以征服为开端,相互歧见不断加深的文明冲突将会制造多么严重的恶性循环,并爆发多么双输的可怕惨剧。
这场惨剧震撼人心,却不是终点,引发的是更大的悲剧,赛德克人走向了不归路,日本人坚定了对其“野蛮人”定位,最典型的是曾经与当地人友好相处的日本军官,也因为丧妻之恨,走向另一个极端。
而“以夷制夷”的思路,让当地部族间的矛盾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但是这一系列悲剧的起点很难说是从“雾社事件”起,还是自青年莫那丧父,屈辱的被征服的一刻开始。
就《赛德克•巴莱》两部来说,我更喜欢上部,而到了下部,魏德圣在保持其旁观者视角略带赛德克偏向立场之余,也犯了些为悲壮而悲壮的问题。
赛德克族在顽强抗击没错,但是如不死圣斗士般就夸张了,而且表现的战斗场次过多,感觉有些桥段完全可以省略,突出两三场大战即可。
当然,这些不足也是相对而言,在下部,我们依然可以体会一种身临其境的残酷,赛德克族女人自愿寻死以便战士有足够粮食战斗的场面让我想起了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从今天的角度你感觉费解,但是这也是那时的一种文明表现。
是的,魏德圣保持着自己的立场,我很不解有人看了《赛德克•巴莱》后,指责这片歌颂嗜血野蛮,有这种“歌颂”的方式吗?
拼命表现英雄“阴暗”的一面?
整部影片让人感受的更多是文明的创伤,个体的悲剧,赛德克人以自己当时文明的表达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魏德圣将之展现给观众,看到那些人,那些事。
也因为这种表达方式,也注定了其影片在大陆地区票房的尴尬,这边影片足够优秀,但是这种非传统英雄主义表达的方式在市场宣传上有些尴尬,而魏德圣严肃的历史观呈现又让影片价值观与观众的认识有些不对路,于是,大陆观众既难以对那段历史产生代入感,又没有传统英雄撩动热血,加之一些如两岸、中日间历史认识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注定了其票房在台湾以外的萎靡。
尽管有一批影人为止呼喊,但是显然收效甚微,魏德圣选择了这样的电影语言,也需要坦然面对一些尴尬的争议和商业挫折,不过,当影片结束时,字幕打出“天使•巴莱”之时,多少也可以感到为这部电影工作的人们的欣慰,魏德圣酝酿十二年,有一部诚意足够佳作刻在自己履历表上,足矣。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item/d811c3ebf41d003a87d9de70
3 ) 严肃文艺,残酷的诗意。
1989年侯孝贤拍出《悲情城市》,这是台湾电影史上罕见的深沉凝重巨作,几近史诗。
二十余年过去,台湾人魏德圣终于拍出了一部史诗,这也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华语史诗大片,必将在华语电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
通常,携带巨量信息和庞大叙事的大片极为考验导演自制力,此片魏德圣完成得相当出色。
在情绪方面导演相当克制,不自恋不傲娇也不献媚不游离,去除个人立场甚至民族立场,用上帝视角冷峻描绘整个事件的方方面面。
在暴力表现上又事无巨细,毫不忌讳,直面残酷。
镜头洗练大气,音乐壮美质朴。
于是,雄浑壮烈的史诗气质被锻制得如暗夜中闪闪发光的刀芒。
魏德圣在视角拥有相当高度的同时,又保持低姿态,这是另一个难得之处。
他会停下剧情的推进,捕捉台湾山间的晨光、日本孩童脸上的骄傲、红烈如火的山樱花、赛德克族跳舞时的足尖。
魏德圣在去商业化和去类型化方面的努力让电影又带上了一些纯粹细腻的自然之风。
原住民黥面,舞蹈以及仪式等文化的反复展现流露出他的内心指向。
不得不提的是这部电影的演员们。
没有一句普通话全片高山族语言和日文,强硬如石的台词,饱满有力的表演让这些非职业演员充分表现出职业演员可能也无法表现的彪悍之气。
莫那作为电影的灵魂人物,那狮王般的强大气场和领袖气质,眼神如刀,抽着烟斗不发一言的身形有着迫人的力量。
为了最后一战忍辱负重30余年,他最好地诠释了赛德克族的民族精神和什么是“野蛮的骄傲”。
赛德克族他们的智慧也好,勇猛也好,都绝不是像日本人称呼的“野蛮人”那么简单,而凝聚为台湾人共通的在地精神乃至世界通明的对自由和信仰的捍卫执念。
这场殖民地战争,不是单纯的战争,而是纵贯数十年的文化冲突。
通过对代表各方立场的几位人物的细细刻画,魏德圣让观众深入到他们的内心,去触碰他们的信念和精神图腾。
随着统治的逐步深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步走向不可调和的必然。
文明的碰撞必离不开血火交融,所有的文明都是在争斗和牺牲中浴火重生。
在死生之间人权尊严都可能被无视。
唯一存在的其实只有内心的信念。
信念让赛德克族人向死而生,不惧死亡。
太阳旗和彩虹桥,这两个对力量的崇拜和对暴力的迷恋十分相似的民族终将决一死战。
这场信念和生命二选一的残酷命题,每个人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4 ) 上半年就指这一部电影活着了
读书时总喜欢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而且是英文,法文,意大利之类完全听不懂再唱什么内容的歌,或者干脆轻音乐。
目的是不被对字面的理解而掩饰音乐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只有听不到才能听到最多。
电影里完全听不懂的对白和大块大块的音乐,对我来说都是最最难得的喜欢。
听不懂却又听得懂,我不知道你在因为什么而怒吼,可我深深对你的愤怒感到恐惧。
在山里唱流行音乐自然会显得怪异不协调,所以山歌的清透又不是在ktv能享受到的。
整篇赛德克的小调贯穿其中,穿梭在森林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除去徐若瑄的出现吓了我一大跳之外,对所有演员表示非常感动,回头看看主演列表,还好我不认识太多的明星,温岚也是只听过歌没见过人,所以她是哪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5 ) 令人震撼,令人尊重
《赛德克·巴莱》。
很希望西方国家的人们能看到这部片子,平时我们看他们的优秀影片太多,受惠很多,这部片子是华人能回馈这个世界的了。
非常优秀。
不论导演、演员、剧情、音乐。
这部电影和这段史诗,都同样令人震撼,令人尊重。
6 ) 简评《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2666》里面有很多奇葩的小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20世纪初期几个欧洲的博物学家偶然跑到一个不为人知的部族所在的小岛上了。
小岛上的居民态度和蔼,面对这群陌生人表现得不卑不亢。
尽管语言不通,这群博物学家发现可以在很多方面和小岛居民和平相处。
不过在习俗上小岛居民和他们是大有不同的,比如当地人打招呼的时候身体接触但是目光不会直视对方,也就是说双方必须把头扭转。
一个博物学家发现这个情况后,愉快地希望分享自己国家的礼仪,于是就正面走向一个土著人,目视着他握住他的手。
土著人十分惊恐,赶忙抽出刀来把这个博物学家砍成两半了。
我在《赛德克·巴莱》中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以及类似的结局。
这也就是说魏德圣十分清楚自己要拍的是什么,怎么拍比较合适,以及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两个多小时中,影片叙事节奏始终与观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人物、背景都高度简化,哪怕是对主角莫那鲁道的塑造都是简约手法的。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魏德圣在本片中放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感,此片多年的心血很可能毁于一旦。
我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导演是一个台湾人(当然他肯定不是原著民),导演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拍电影的。
从这一点,我可以把《金陵十三钗》黑到底。
有人说《金陵十三钗》是情色爱国主义,我看一点不为过。
魏德圣抓住了一个原著民最能被我们这些civilized people所认可的特点:血性。
这一点和姜文导演的风格有一些重合。
还想说一说,本片是导演多年的心血,也得益于台湾政府的辅助金政策。
台湾有电影辅助金政策,我们有最高票房电影再奖励一个亿的政策,从这两项政策的对比可以看出,广电总局的领导们,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就是很讨厌中国,很导演中国电影。
7 ) 歧视与同化——殖民史视角下的赛德克巴莱
可能自己的确是一名历史学学生,看《赛德克巴莱》也不免是历史学的视角。
虽然魏德圣叙事主要着眼于土著居民的信仰,对雾社起义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做了淡化的处理,但依旧可以看到的是日本在台湾殖民政策同化与归化的摇摆不定。
台湾的殖民时期的叙事,历来因为民族主义的缘故,成为最容易被涂抹的地带。
我们熟悉的是史实是,1898年《马关条约》的一次割让,及其后台湾自发的反割台运动。
但其后台湾的历史之余我们是茫然未知的一片。
处于殖民的台湾,究竟如何更是无从得知。
NHK曾经有一部纪录片《“歧视与同化”:日本治台50年》,在我看来,是表现台湾日本殖民时期最好的纪录片。
治台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语。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关于该用日据时期还是日治时期。
在纪录片里,NHK清晰地表达日本对台政策的迟疑与犹豫。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为现代国家的一员。
而台湾是作为日本殖民历史的开端,日本是有意把台湾进行某种模范的打造的,以期待和其他的现代国家英国、法国媲美。
但在殖民政策上,日本不免犹豫良久。
熟悉殖民史,也许会知道有两种经典的殖民方式。
英国式的殖民是 “分而治之”、“精英制度”、“以夷制夷”的政策。
具体表现为非白人自治领,英国殖民者一般会采用本地的精英治理,而殖民地一般会保留殖民地法律,而不是统一采用英国本土的法律。
而法国式殖民则是共和同化模式,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等地区,都大规模进行法语教育,在殖民地也和母国一样实行同样的共和法律。
我无意评价两种殖民政策的高下。
日本在对于台湾殖民上面,也不免受到两种的影响。
日本宪法中将台湾作为本国领土,殖民地列入宪法,但日本又为台湾制定专门的台湾法律,以区别本土法律。
教育方面,则让台湾居民接受日式教育。
但同时又认为土著低等不可教育,始终具有野蛮性质,甚至把台湾土著居民带到世界博览会上展示。
在整个台湾殖民史上的命题就是试图将台湾居民皇民化,但始终从未真正把台湾人当做皇民。
电影中的一郎、二郎就是此背景下,接受日式教育的土著居民。
一郎本人接受了师范教育,远比其他的日本警察学历要高,但是工资却是最低的。
而同事们也仅仅因为他们土著血统,而肆意嘲笑。
虽然始终对于猎首无法理解,但你能感受到土著本身的无奈之存在。
是不是带来了现代文明,就必须感激涕零。
也许文明的同义词就是权力话语。
PS:巴黎一大的殖民史教授认为在处理殖民历史时,需要克服两种神话——红色神话和黑色神话。
红色神话是指处理殖民史的时候,研究者过分喜欢文明与野蛮的话语;而黑色神话,是指后殖民主义的广泛流行,给殖民历史肆意增加了过多的污点。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
8 ) 寻根
读完了魏德圣的导演手记,看过了四个小时的赛德克巴莱。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好电影。
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导演需要一边借钱一边拍片。
后期资金跟不上,韩国、日本团队相继离开,拍到最后连空爆弹都买不起。
面对这样的困境,所谓的“辛酸”与“痛苦”这样的词汇,都显得有些矫情与肤浅了。
魏德圣说,赛德克巴莱这样的拍摄过程,不可能再有了,它也复兴了在台湾电影界已经消失了的一种精神。
这样制作恢弘的一部电影,不是来自好莱坞,也不是来自大陆,而是来自那个神奇的小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看过了金陵十三钗与赛德克巴莱的影迷,应该能默默计算出六亿人民币与七亿新台币,哪个更有价值一点。
不过关于赛德克巴莱,我还是有些质疑要说。
尽管这是一部抗日电影,但与其说赛德克人反抗的是日本人的外来侵略,倒不如说他们反抗的是现代文明对赛德克部落文化的入侵。
在影片中,伴随日本人出现的是巨型蒸汽船、来复枪、火车、电话、学校、邮政所、杂货铺。
而在日本人入侵前,伴随赛德克人出现的是竹背篓、燧发枪、赤脚、茅舍、砍刀、猎头。
这是一种文明对野蛮,都市对荒野的对抗。
用莫那•鲁道的话来说:“如果你们的文明是卑躬屈膝, 我要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
”赛德克人的抗日看起来更像是与狼共舞、最后的武士一般的文化冲突,而非在大陆上发生的赤裸裸的种族对抗。
而日本人所代表的“文明的威胁”完全可以套用到任何来到台湾这个小岛上的统治者——日本人,或者国民党迁台政权,或者即将到来的大陆客。
着重于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好莱坞的拿手好戏。
而把这种理念根植于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中,就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模糊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另外,在这部影片中,到底谁能代表真正的台湾人呢?
是面对侵略碌碌无为最终苟且的汉人?
是接受了日本人文明的洗礼,变得矛盾异常的归化生番?
是从远方越洋而来,自诩为主人的日本人?
都不是,影片一次一次地提醒我们,台湾真正意义上的主人,是那些骄傲而自由的生番——赛德克巴莱。
可这符合历史吗?
现在被边缘化的台湾赛德克人,可能是当年这个小岛真正的主人吗?
台湾这个岛屿,一直漂泊在大陆的另一边,几千年来,不断地移民、定居,再移民、再定居,谁又敢说自己是真正的台湾人呢?
就连这赛德克人,也是千年前移民来的。
本省人,高山族人,外省人,这样的族群在台湾并存,谁是真正的台湾人又要向哪里寻根,恐怕迷茫的不止是魏德圣一个。
再说一些影片本身的问题:1电影的线索庞杂,很多可有可无的线索完全可以砍掉,起码下集彩虹桥就没有必要那么冗长,自尽的戏码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弱化了戏剧冲突,完全可以合并为一出戏。
2尽管是台湾电影,但也没能逃脱YY的命运,在影片中,日军与日警成堆成堆地阵亡,是赛德克人太能打,还是侵略者太过熊包?
这与历史中日军阵亡仅有22个,差距太大了。
镰田弥彦的感叹:“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区见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
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艳红了吗?
”也太狗血了一点。
另外这位老日本演员脱离了日本导演的束缚,终于可以撒花玩了,可有些太过歇斯底里了,缺乏了一个指挥官应有的冷静与内敛。
对比一下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尽管二战中的西线战场远没有东线惨烈,西线德军的兵员素质也没有东线出色,但影片中的美军也绝不是个个都像兰博那样一出手对面就倒下一片。
给对手以应有的尊重,不但是尊重对手,也是尊重自己,在这一点上,赛德克巴莱千万不要向大陆电影看齐。
3影片的结局太罗嗦了,整个影片完全可以在莫那•鲁道独自背着枪走入神木林作结,这样意犹未尽,总比面面俱到好得多。
另外最后赛德克众勇士出现的西游记般的特效场面,咱还是免了吧,还不如直接用山水空镜头配上他们的合唱更好些。
最后揣测一下大陆公映的剪辑版会少些什么。
首先是赛德克人内斗的戏,屯巴拉社以及其头目铁木•瓦力斯将不会出现在影片里。
其次,雾社事件中砍杀妇孺,以及赛德克孩子拿起武器砍杀日本人的戏也不会再有。
两个归化生番最后自尽的戏,恐怕也要被切。
尽管赛德克巴莱并不完美,但是从导演魏德圣到各位原住民演员,都付出了相当大的诚意。
他们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在这一点上,就比很多大陆的所谓大牌导演强上许多。
9 ) 史诗大作的气息激动你的内心
看了这部电影,我完全被她的史诗大作的气息所感染,激动人心的动作场面、扣人心弦的音效,加上那淡黄色的电影质感,真的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部电影。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开头,一来便是紧张的音乐加上赛德克种族特有的打斗场面,让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人耳目一新。
有一场男主角莫那·鲁道跳进河里的场景真的拍的非常好,在水下的翻滚,漂流等场景堪称经典镜头。
在这部太阳旗的上部分表现了,赛德克种族内部之间的斗争,下半部将了日本人占领他们的家园后,赛德克人的心理变化以及莫那·鲁道那不变种族意识。
这部电影有三点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其一是这部电影的打斗场景,节奏快、打斗给力,加上赛德克人独特的体质,让他们在战斗时非常有观赏性,非常给力。
其二就是这部电影的配音,个人是相当的喜欢,特有的民族风味音乐,轻快、节奏感强。
他们族人在庆祝跳舞时的音乐可称得上是经典。
其三就是这部电影的画面感,很多场景导演都运用了淡黄色的场景,给人史诗,大气的感觉。
看完这部电影,让我感觉台湾的电影真的上了很大一个台阶,比内地的很多所谓的大导演拍的电影好看,给力。
10 ) 野蛮英雄的傲骨,落后受罪的战争悲剧
「名词解释」*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当地话语体系中是指人,巴莱是真正的意思,所以直译是真正的人。
但是我个人在看完影片后觉得赛德克是雾社部族总称,而巴莱更像是英雄的意思。
*出草:部族间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与其他部族发生的暴力斗争均可称为“出草”。
也指代猎动物首级,猎人头等。
「个人观感」上下两部加起来长达四个半小时,分了几个时段才看完。
一部野蛮英雄主义悲歌在4个小时根本说不完,所以电影显得紧凑又紧张,一张张面孔都让人难忘,一句句台词都引人思考,一次次出草都使人提心吊胆。
更别说野蛮与文明的冲突,落后对先进的抗争,部族与部族的撕斗,民族与民族的战争。
内容丰富到需要配合史料和论坛多刷几遍才能理解,但是内容又悲怆到不忍再看一遍。
上部《太阳旗》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影片结尾,配合着歌声,莫那鲁道背着枪一路狂奔,镜头带到一朵盛开的樱花,血一样红的花儿孤零零的盛开着。
跟着莫那的视线,一路走过,异族的无论男女老少都死在路上,不禁悲从中来:这场争斗中莫那他们赢了吗?
真的算赢了吗?。
导演也借欧宾之口问出:“你们为何要出草?
”的问题。
在日军立场来看:我们善待你们带来文明引导进步,你们却反过来杀我全家。
而在雾社反抗部族立场看来:你们这些入侵的异族,奴役我们身体占领我们土地甚至蔑视我们的灵魂,必须驱除。
没有对错也说不上输赢,然后我知道邪恶的一定是战争。
下部《彩虹桥》小岛所在的屯巴拉社,阴暗的天空飘起了雪。
所谓好人小岛不仅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也与当地人相处融洽,最主要的懂得个部族之间的明争暗斗,所以利用部族间的不和为日军谋得战争中喘息和进攻的机会。
小岛在妻女死后表现出来积极性以及最后煽动道泽屠杀莫那鲁道老弱遗族的报复性也得到印证。
相对上部来说,下部更加精彩紧凑,有诸多令人动容的名场面。
比如女人们为了能让参战男人们有更多粮食纷纷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文明受益者一郎二郎不得不杀死孩子送走女人,最后在纠结中自我了解。
,谁的灵魂赢了?
谁的肉体又输了呢?
影片最后的结局也让人唏嘘,莫那鲁道选择走入深山自杀是就出于本不想受辱的本意。
但造化弄人,死后四年多遗骸被一个猎人偶然发现,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公开被陈列于日本役所的凌辱。
「樱之寓意」全片重要片段都出现了樱花,不仅推动故事发展,也寓意非常。
第一幕樱——满开与希望:日本军队第一次来到雾社,看到满山盛开的火红樱花。
赛德克族人杀死了这批入侵日军,给了他们第一记耳光。
落樱与侵略者鲜血交织,我们还没感受到彼此实力的差距,还有希望满怀。
莫那鲁道第二幕樱——孤朵与傲骨:画面一边是背着枪不断往前冲的莫那鲁道一面是安静在枝头盛开的孤樱,战斗的紧张与安然盛开的樱花形成强烈的对比。
此时的孤樱预示反抗族群的傲骨与抗争道路的艰难。
第三幕樱——谎言与不屈:天空中飞来红樱般的劝降单,莫那鲁道深知投降报名是个谎言。
然而继续战斗下去也是死路一条,只得着手安排剩余部众后路。
自己则拿着枪向深山初走去。
第四幕樱——早樱与不甘:日军清扫战场时又恰逢樱花满开。
司令官折服于三百名反抗战士的英勇精神,感叹此处樱花甚是鲜红。
而小岛却说此时并非樱花季节,是开早了。
这也预示着小岛从内心对目前战果的不甘和不满,印证后面他的煽动打击报复行为。
「动人台词」莫那鲁道「如果你所谓的文明要叫我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可以输身体,但会赢得灵魂」另一个部落首领问莫那鲁道:「你明明知道这一战一定会输,为什么还要打?
」莫那鲁道「为了快被遗忘的图腾」他又问「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轻的生命」莫那鲁道「骄傲」只求一战的巴万对莫那鲁道请求道:「让我也参加吧,我有图腾刻纹我可以战斗。
我们好累 真的好累 我想睡个好觉」在战火中直接冲向日本军想起歌声「战死吧 赛德克巴莱」莫那鲁道问道「达多如何能躲过这些大炮」「让我这个灵魂来带路吧」司令官「区区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
为何我会在遥远的台湾深山见到我们民族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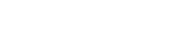




















确实有点长了。。。而且有好几段剪辑的很乱我都没看明白
三星半。
大片
启示弱化版
三星半吧,情节挺紧凑
with u
①既然导演内心已有观念成见,所以史实什么的,能帮助自己自圆其说的就拿来用,不符合的就不用或者改动,因此活脱脱拍成抗日神剧也就在所难免了。还原历史?不存在的;②维族人藏人的历史能拍吗?③过于拖沓,无时无刻都是原住民在歌唱,听到烦躁。
如果你們的文明是卑躬屈膝, 我要讓你看到野蠻的驕傲!!!
上半部一共2小时20分钟,气氛渲染了整整两个小时,结尾最后20分钟才大开杀戒。打着反抗侵略的旗子,杀戮就杀戮呗,非打着祭祖的旗号干什么。也许这部电影在台湾人和日方人看起来更舒服, 我是很不习惯这种媚日的影片的。艺术片就艺术片,没事唱你麻痹歌。上半部电影完全可以压缩到一个半小时时间
三星半
总觉得跟我那根弦儿对不上,这部片子绝对不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抗日电影。我一度认为,日本这个敌人可以替换成任意一个对象,归根结底,对这些原住民来说都是外族,即便不是外族,也只不过是部落之间的斗争。后面则上升到了文明与野蛮的高度,我认为这时电影才终于慢慢进入状态。第700部电影~
再见了,魏导!
不是我爱的类型呢
你说,你是要进我们的祖灵之家还是日本神社?To be or not to be...
每个逻辑上进行不下去的电影,都得一边设置个丧心病狂的疯子去无赖挑观众仇恨,另一边加一个毫无廉耻的爱族(国)者去无奈挑同情,本电影又加一没讨论清楚的历史讨论(不过水和安藤政信真的很清澈~)。跟我一样喜欢土著的还是建议去看看Apocalypto启示净化一下心情
如果你们的文明是卑躬屈膝,我要让你们看到野蛮的骄傲。
如果文明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看野蛮的骄傲:这骄傲被魏德圣演绎的淋漓尽致
一般
开头就高潮迭起,可惜太过宏大的叙事构架以及导演想表现的内涵太多,导致叙事越来越混乱。第一部更精彩。
拖沓,直到大屠杀才觉得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