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第三季》剧情介绍
《双峰第三季》长篇影评
1 ) 双峰时空观的观察
Black/white lodge不只是抽象的善恶本源,而且近似于高维空间,它的时间处于静止/折叠(准确说是根本不存在时间)。
这里的“头目”(fireman/judy)可以操控现实世界 (类似于《星际穿越》里,三维空间的一个观测成了五维空间里的一个切片),甚至将世界改造成一个不同的时间线。
我们看到woodsman的淡入/淡出,正是高维生物的运动在三维空间里观测到的样子。
现实世界的人物出入高维空间要经过特定的通道。
可能是在现实中特定时间+地点坐标形成的开口,也可能是black lodge->紫色铁屋->插电孔这种奇特路径。
现实不存在“平行世界”,但是它否定了时空状态的唯一性(即对任一个三维空间+时间的坐标,世界的状态不是唯一确定的),因为它时刻处在高维空间的干涉中。
当它被替换为新的时间线,之前的时间线从物理上就不存在了。
如果没有恶之源,现实世界也没有与高维空间发生关系,它或许原本是线性的。
当现实世界被替换为新的时间线,人们会持有其他时间线中的记忆。
同样地在Black/white lodge影响下,人们不同程度地持有他们去过lodge(尽管发生在“将来”)的记忆,或者关于“将来”的其他预见。
但是这些记忆通常体现为潜意识,在某些时刻(如梦中)被唤起。
特定的人可通过lodge在同一时间线中时空旅行 (一个观测空间的物理身体来到另一个观测空间,能够保有全部记忆)。
因此并没有真正的“轮回”,但是人们好像在没经历一件事之前已经经历过它了,或者说经历了各种时间线和各种时间点的“全集”,时间在高维空间作用下弯曲折叠,过去/现在/将来的区分失去了意义。
摄影机像一个角色一样具有一个“观测空间”。
现实不再是线性时间的,但我们的观测是线性时间的。
当某一时间点的世界状态受到外力扰动,这个扰动可能会波及它“之后”的世界状态。
因此我们的观测空间常常处于不稳定的“裂变”中(一个特殊的镜头效果,甚至一个平常的镜头剪切,可能已经在传递裂变的感觉,get到这种状态或许是体验这部电影的关键),有时则是时间线替换产生的巨变(包括观测到突然“断电”)。
现实中与高维空间干涉越多的时-空区域,越容易观测到裂变,这也解释了紫色铁房间里的混乱情况。
关于梦与现实的探讨,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有唯一的灵魂,却不再有唯一的身体,他所处的时空会受到扰动,甚至时间线被终结,进入“另一具身体”中。
于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dream of time and space”,但是“Who's dreamer?”如有新发现会继续更新或修正~
2 )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看了一个礼拜,每集都写,零零碎碎记录了几千字,系统性的符号对比研究了一大堆,比如三个酒吧。
gunbar,还有类似于中美洲吹箭的那个戴安常去的那个bar,还有劳拉妈妈会去的那个麋鹿bar(挺像北美三国的)。
我就不发上来了,太乱。
研究这个东西对人的精神损耗太大了,我就概括性的说一下林奇在说什么,其实就是有两股力量在博弈,善与恶。
举一个例子(此类例子其实还很多),戴安给黑库珀的坐标是17位,实际看图片(死了的秘书手臂上写的那个),非常清晰的是16位,她想电死黑库珀,老实说,在前一个时空,其实成功了。
但是恶的力量改变了时空,让奥黛丽的儿子撞死了那个小男孩,进一步推动他走向狂躁,然后遇到了黑库珀,黑库珀利用他先探测了那个地点,然后那个家伙被电死了,黑库珀立马就知道这是个陷阱。
恶在这一步,实际是胜利了,但最终还是输了,即便他拿着对的坐标,找到了善的代表——fireman的总部,还是被早就在站岗的上校(大头)给抓住了,然后被传送到了警察局,在善恶的对擂中,还是被消灭了。
这是一个微观事件,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善恶对擂。
在结局中,改变了时空的库珀,最终还是没能彻底消灭恶,他出现在了lodge里,劳拉也在旁边。
在最终,虽然他没能如16集苏醒时那样英雄临世,天降猛男,大获全胜。
但也肯定不是屈服于恶(那样只会被悲伤和恐惧浸透,成为bob这样的恶灵的养料)。
甚至不是善恶对半分,给予恶充分的空间,相信彼此只能平起平坐。
而是一种知道了恶是永远无法被根除的,强大的。
永远是阴魂不散的,游荡于世的,无孔不入的,但是,也知道,善,永远压恶一头。
所以,请大家不要搞错,林奇大爷是个乐观的人,库珀最后的表情也是了解了这一切之后的一种释然和动容的表情,因为他知道——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3 ) 用诺斯替主义解读双峰之五:异乡人菲利普·杰弗里斯的形态变化
菲利普·杰弗里斯的形态变化(从人类到混沌般的超维存在,再到最终以“茶壶”形态示人)在《双峰》第三季中显得极其神秘,但如果我们从诺斯替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理解为“异乡人”(Stranger)在灵性进程中的必然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解释为他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都对应着诺斯替传统中的不同灵魂状态。
1. 初始形态:人类身份的破碎——离开物质世界杰弗里斯原本是FBI探员,属于物质世界的常规存在,但在《双峰:与火同行》(Fire Walk With Me)中,他在FBI总部的短暂现身已经表现出极端的不稳定性:他的语言破碎,无法正常沟通;他的时间感混乱,似乎同时处于多个时间点;他的物理存在无法持久,在房间里短暂闪现后便消失。
这种状态与诺斯替异乡人的命运一致——当他们开始获得超验知识(gnosis)时,他们就会被物质世界排斥,因为他们的存在已不再完全符合这个现实的规则。
杰弗里斯的身体和语言都开始崩溃,这暗示他正在经历从物质存在向更高维度存在的转变。
2. 过渡形态:超维放逐者——意识的碎片化在第三季中,杰弗里斯已经不再以人类形态存在,而是变成了一种超越常规空间的存在:他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似乎受到了干扰;他似乎能够以某种方式操控时间,并帮助库珀穿越现实;他似乎也受到某种限制,无法直接干涉现实世界。
这种状态与诺斯替主义中“灵魂被困在中介世界”相似。
在诺斯替教义中,灵魂一旦获得gnosis,就可能会被Demiurge(假神)及其统治者(Archons)封锁在某个介于物质世界与完满之境(Pleroma)之间的状态。
杰弗里斯的状态暗示着:他已经突破了物质世界的规则;但他仍然受限于某种存在规则,无法彻底自由;他可能正在某种层面上与Archons抗争,试图给予库珀启示。
3. 终极形态:茶壶——灵魂的降临与再构造最令人困惑的部分是杰弗里斯最终以一只茶壶的形态出现。
这一形态既像某种古老的炼金术象征,也可能是一种对诺斯替主义灵魂困境的隐喻。
A. 茶壶象征“能量容器”在神秘学和诺斯替思想中,器皿(Vessel)常常象征着灵魂的容器,而物理世界的身体只是一种临时的壳。
茶壶的形象可能代表了“他不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肉体,但仍然承载某种意识”。
这与诺斯替传统中的“光之火花”(divine spark)相似——灵魂被困在物质世界之中,但仍然保持一丝与神圣世界的联系。
B. 茶壶象征“困囚于系统之中”在诺斯替主义中,灵魂可能会被Demiurge囚禁在某种机制中,使其无法完全解脱。
这也可能意味着,杰弗里斯的超维存在依然被某种更高的秩序所束缚,他的形态已经被某种超自然力量(例如Judy)改变。
C. 茶壶象征“炼金术转化”在某些神秘学传统中,茶壶或坩埚象征着炼金术的转化过程。
这意味着杰弗里斯的形态变化可能并非单纯的囚禁,而是一种最终通向更高境界的蜕变。
4. 为什么他必须经历这样的形态变化?
从诺斯替视角来看,杰弗里斯的形态变化可能具有以下原因:A. 他的意识已经超越了人类形态在诺斯替主义中,灵魂在达到一定的启示阶段后,会与物质世界产生根本的不兼容性。
因此,传统的人类形态已经不足以承载他的意识。
他必须进入另一种形式,以便继续存在并与世界互动。
B. 他是Demiurge的敌人,遭到了形而上学的封锁杰弗里斯在故事中的角色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他试图让库珀理解Judy的存在,并提供时间旅行的能力。
这意味着他已经威胁到了Demiurge或Archons的统治。
在诺斯替主义中,这类觉醒者(gnostic revealer)通常会遭到Demiurge的封锁,他们的形态可能会被扭曲,以限制他们的影响力。
C. 他的形态变化是通向最终解脱的一个阶段杰弗里斯的形态变化可能并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必须经历的进化:他从物质世界消失(从人类形态消失);他变成了超维存在,但仍受限制(他在第三季中仍然无法自由行动);他的最终形态是茶壶——某种完全异化的存在(既能存活于不同的时间线,又能提供知识)。
在诺斯替主义中,灵魂从物质界解脱的过程往往是非线性的,它必须经历不同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以形态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结论:杰弗里斯的形态变化是诺斯替“异乡人”旅程的象征在《双峰》宇宙中,菲利普·杰弗里斯的形态变化象征着一个典型的诺斯替旅程:他最初是普通人,被卷入超自然现实(类似于灵魂堕落到物质世界)。
他获得了某种启示,但因此被逐出物质世界(获得gnosis后,异乡人不再属于尘世)。
他的形态开始变化,无法再以普通方式存在(灵魂挣脱肉体束缚)。
他最终变成茶壶——象征着某种炼金术式的转化,成为某种超维信息存在(可能是通向最终解脱的中间形态)。
这一变化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怪诞,而是符合诺斯替教义的深层隐喻:当一个人获得了绝对的知识,他的存在方式就不可能再与普通世界兼容。
4 ) 关于《双峰:回归》的28个碎片
/“注意听声音”/“LISTEN TO THE SOUNDS”“注意听声音。
” 在我们听到这句台词后,戴尔·库珀的视线看向那个声音,最初静止对准留声机的摄影机也意识到了,也往前做出推进运动。
此时,留声机巨大的喇叭如同一个黑洞,里头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是的,不仅要听声音,还要“看”声音,这便是Fireman提示的意义。
拿这句话用来开启《双峰》的回归,既是给库珀的一条线索,更是给我们观众的提示。
库珀与Fireman的这一开场戏在剧集开播后便争议不断,关于其发生位置、时间线、以及对库珀这个人物的意义已经有了大量的猜测和讨论。
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标准答案。
我个人的猜测在这里并不重要,但在阅读了一些文章后,我能暂且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这场戏在剧集的时间线中是发生在第十八集,也就是库珀义无反顾地走上那条黑暗之路的之前或之后,Fireman的线索对于观众的意义,都要大于其对库珀的意义。
/气象预报员/WEATHER REPORT虽然我们都了解成就《双峰》的并不都在于它的故事情节,但那些关于它的种种感官体验:梦幻般的小镇气氛、极佳的音乐、魅力十足又古怪的演员们等等,或许暂不应被文字化,因此我还是从叙事开始。
首先,需要指出一些反常的地方。
在回归季中,包括Fireman与库珀揭幕的第一场戏在内,总是有着大量如下的情节——线索被角色全盘托出,摄影机静静地看着,有时反打拍摄其他人的反应,总之,一段段长段的解释。
这时人们会怀疑:这还是我们熟悉的“视听艺术家”林奇吗?
为何突然一反常态地开始解释各种元素,这是一种惰性还是对电影语言的背离?
但重点在于,那些应该知道的,作者诚实地告诉我们。
面对这部续作我们更必须了解到,在2017年,《双峰》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度饱和的秘密盒子,经过了自1990年首播以来长久的催化,粉丝对剧中的每个元素都疯狂地着迷,十几年来的各种文字、批评、理论和猜测堆积如山。
因此,为了其自己的生存,林奇和弗罗斯特在这回归季中,必须时不时地必须分享给观众一些东西,这是其保持生命力的必需品,也是获得与观众平等关系的一次机会,更重要的是因此来从秘密中解放自己,来生成更多的秘密——成为林奇理想中的那个“生金蛋的鹅”。
催发着林奇的视听魔力的前提在于好奇心,而这便是所有的“提示”和“线索”所起到的作用,这些线索是足够清晰的指路灯,它并不夸张到能抵消所有的奥秘,而是恰如其分地站在了直线叙事与碎片化断裂之间的平衡点,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好奇心是无尽的:我们不仅有线索的武装,更拥有想象的空间。
《双峰》中的那些表达,其状态介于纯粹的信息传输和神秘兮兮的悄悄话之间。
不如用一个林奇式的爱好来做一个对比——气象预报。
从《内陆帝国》的年代开始的几年间,以及在这个新冠疫情时代的近期,林奇开始在自己的付费网站(这个网站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则是YouTube)上发布每日更新的气象报告:在每天一成不变的机位下,林奇用他标志性的口音开始播报当天洛杉矶的天气情况。
他的工作台背后是一扇刚好处于镜头外的窗户,也是林奇观察天气的窗口,于是他转向窗户,观察云层和天空的颜色。
我们看不到窗户外具体的景象,但是林奇的讲述让我们相信:晴朗的天空令他愉悦,他的咬字变得充满狂喜(“美-丽-的-蓝-天!
”),而就算阴雨时期,从他的语气中,你也能听到对于阳光的渴望。
如戈达尔语:“电影制造记忆,电视制造遗忘。
” 这不只是信息传递,这是电影(cinema)。
《双峰》里也有自己的气象预报员:在第二季的第一集中,神秘的天象观察员加兰少校向自己叛逆的儿子鲍比讲述自己的梦境,在梦中自己的儿子在未来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
这或许是第二季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而我们只是坐在RR餐厅那个再简单不过的小隔间中,用朴素的分镜头看着这两位风格迥异,完全不像父子的演员叙述着这个故事。
唐·戴维斯扮演的少校语气镇定,即便描述如此奇景时也是一股军人的严肃模样,但他的语气又不像是在做刻板的报告,而是真诚地分享;而扮演鲍比的达纳·艾什布鲁克,仍然保有着他情景剧化的夸张表情,如他在首播集中令人捧腹的咆哮——不像对面的戴维斯,这不是一位能把情感藏在内心的演员,他的任何触动与震惊全部写在脸上。
《双峰》中这样的交代情节,不也正是来自于这种气象预报的精神吗?
它充满爱地讲述着,分享着,剩下的则交由我们想象。
而那些我们不应该知道的,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弗兰克,你永远不会想知道那是什么” “我们不要提朱迪”)。
这听上去虽然没有这么“视觉”,但正因如此,当我们在真正接收到那些突如其来的影像时刻时,情感的能量才被放大到最强:如果第八集中爆炸性的实验影像仅仅是一系列的诡异画面,它并不会掌握其现在拥有的情感力量;如果米彻姆兄弟不就那个盒子里的樱桃派而鬼鬼祟祟地讨论一番,属于“道奇·琼斯”的伟大时刻也不会如此令人畅快;回到最初,假如Fireman在没有给出库珀这些看似随机的提示,那么当我们看到最后一集时也不会如此不安。
25年后,少校的预言成真,已经成为警员的鲍比对着劳拉经典画像而哭红了脸(第四集),将所有关于《双峰》的记忆唤起——这也是安哲罗·巴达拉曼提所作的劳拉·帕尔默主题音乐首次在回归季中响起。
注意听声音(和沉默)。
华丽归来的FBI探员库珀在第十七集中对一脸疑惑的弗兰克·杜鲁门(罗伯特·福斯特)警长说:“少校告诉我,(北方大饭店315房间的钥匙)会在杜鲁门警长手上。
” 演员戴维斯在2008年便去世,他在本季的回归也形式诡异,尸首分离但又无形地存在着,剧中也没有材料去佐证其种种预言;然而当库珀对警长说出此话时,没错,我们无条件地相信他,这位伟大的预报员。
/电影学院/FILM SCHOOL距离《双峰》回归荧屏已经三年了,我进入电影学院也三年了。
于我而言,它便是21世纪的电影学院,长达18个小时的宝藏。
不仅仅是那些实验的、神鬼的、所谓“林奇主义”的时刻(刻意模仿那些时刻虽屡试不爽,但反而被证明是有害的),而是教给我们什么时候该拍什么,展示/不展示什么,也是关于节奏的大师课;它教你如何利用时间,教你如何催发好奇心(“2”的秘密),如何利用电影最简单的三种景别(换言之,什么是正反打?
),教你如何制造声音的能动,情感的能量,音乐的能量,教你如何活在当下并同时顾及过去与未来…… 同时,它也是一部喜剧杰作。
/电视或电影/TV OR CINEMA“当我们选择把两部电视剧集排在我们十年十佳的最高位时,我们所做的,是在分辨那些还讲着电影的言语(懂得场面调度、剪辑、镜头、现实主义、表演等等……)的影片和剧集,和另外一批影视,那些只是给观众和’用户’提供‘内容’、‘宇宙’和‘信息”的叙事节目之间的关系。
” (斯蒂芬·德罗尔姆,《电影手册》第761期)/火车/TRAIN第二集某处,夜晚,固定不动的摄影机描写了一列火车穿过马路的场景。
火车让我们想到电影的起源,想到卢米埃尔,想到悬念。
路杆放下的那一刻,悬念便生成,我们等待火车到来。
很快画外传来了火车的声音,我们期待着,声音越来越响,随后火车飞驰而过,悬念解除。
但接下来呢?
而对于刚刚开始进入剧集的我们,正在等待的则是库珀,或是奥黛丽·霍恩、雪莉·强森、杜鲁门警长、以及所有那些熟悉的脸庞和地点们,我们期待这列火车能将他们带到荧屏面前。
或许是我过度解读,但这一镜似乎早已默默道出所有这些等待背后的真谛。
/空房子/EMPTY HOUSE据《电影手册》2017年底对林奇的采访,拉斯维加斯是马克·弗罗斯特的主意,他设想在原剧集25年后,戴尔·库珀会突然出现在这座赌城的某栋未经装修的空房子中(这一设想最终出现在第三集),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不少“空城”楼盘出现在这座扁平的沙漠之城中——一个诡异又讽刺的景象,道奇·琼斯的出现则额外加入了幽默感。
为什么是它?
这看似随机,但其实也是缘分。
如果说1990年的《双峰》是源于林奇和弗罗斯特两人对玛丽莲·梦露式神秘的女性悲剧的兴趣,那么弗罗斯特的这个新想法则又一次足够与林奇的频率相共振。
空房子的想法也足够有电影上的空间想象力,也足够令人充满好奇,正如第一集中如弗朗西斯·培根画作般的纽约玻璃箱,显然像是林奇的产物:两个看似空空如也的空间,像两块白色的画板一样,等待着画笔落下。
正是这种罕见的灵感共振,催生了《双峰》的回归,而作为一部从一开始就是两者合作产物的剧集,这种默契更是必需品。
那么在2010年代,《双峰》对于两位作者而言,契合点在哪里呢?
/反怀旧/ANTI-NOSTALGIA如不少观众在回归季的开头两集便意识到的一样,这部新《双峰》似乎并不追求着把“故事”集中在双峰镇上展开,也不急着引进那些观众熟悉的人物,因此也被一些意见人士看作是一次借“双峰”之名而作的随意作品。
但正如这部剧集长达25年的“冬歇”一样,在如此长时间的停滞后,这部回归季也是关于回归这件事本身。
有人说回归季是一次对怀旧式的翻拍作品的抵抗,但我们或许根本不必上升到抵抗层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真的离《双峰》这么近吗?
最起码我们的作者不是,在看过《回归》后,我们很难再想象一种所谓“正常”的回归轨迹:双峰镇又发生一起命案,又出现一个杀手,FBI探员又一次到访。
在第一季的伟大开局和第二季初期激烈的超自然演进后,我们已经在原版剧集第二季的后半程,以及电影《双峰:与火同行》见过这样的“翻拍”戏码。
前者被证明是一次无用功的自我模仿,最终沉沦于无节制的廉价幽默,并活生生地让一众经典角色沦为跳梁小丑;而在后者中,独当一面的林奇则有意识地在第一幕将剧集的前传故事:特蕾莎·班克斯的谋杀案和鹿草镇(Deer Meadow)设计成为一个反《双峰》的实验,用极端反面的形象解构着定义着“双峰”魅力的各种元素:小餐馆,咖啡,FBI探员,被谋杀的神秘女孩,等等。
《双峰:回归》则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一部试图回归的剧集,在其故事的演进和重复,人物的出现和消失中,寻找着真正回归的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开始,一切元素都被分裂到了整个美国的各个角落。
/纽约/NEW YORK CITY回归季的第一集中最吸引人的戏码莫过于纽约市的玻璃箱情节——如此神秘费解,又特别不“双峰”。
相信不少人都能清晰回忆到首播那天,在荧屏中看到纽约市三个大字随着曼哈顿的夜色突然出现时的震撼,这是绝无仅有的反应。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镜头本身甚至只是一个网上的库存素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魔力?
先让我们回看第一集的开场段落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首先林奇展示给我们熟悉的东西。
他在开场字幕前回顾了剧集试播集和第二季最终集中的段落:劳拉·帕尔默告诉库珀“25年后我会再见到你”;劳拉的死讯传遍双峰高中时的空镜头——那个一闪而过的在窗外尖叫着的女孩,只是这次林奇选择了慢放,像回放一段记忆——我们对剧集的记忆;开场的“TWIN PEAKS”字样伴着劳拉的经典画像出现,提醒我们这部剧集的核心自始至终都来自她。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是熟悉的。
然后,在全新的开场片段后(此时我们一睹红房间的新质感),在黑白影像中,一个优雅又有些许不稳定的镜头抬升,我们看到Fireman,对面坐着库珀。
虽然影像风格上,这个段落显然已和原版剧集划开了界限,此时此刻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熟悉的,毕竟谁不会想看到如此经典角色的回归呢?
紧接着这一段落的,是森林中的杰科比医生的回归。
为什么是他?
我们问自己。
况且,这不是你所熟悉的介绍回归人物的方式,镜头设计完全是疏离的,没有任何特写,没有标志性的音乐,我们甚至也不太明白他订购这些铲子的目的是如何。
整个段落在真实时间中以写实的美学展开,在远处静悄悄地观察着这个人物,结尾处摄影机在树根后面的注视更略有一种监控视角的意味。
不过就算如此,我们在双峰镇,我们在熟悉的森林里看到了熟悉的人物,即便没有故事展开,一切还是安抚人心的,于是我们放下了警惕。
然而……
连接着杰科比医生的出场和纽约玻璃箱情节的,是淡入淡出的一段短暂的黑场,这种剪辑技巧在本季中被林奇和其剪辑师Duwayne Dunham反复利用,但又不同于原版剧集中被广告时间强制分离的黑屏。
黑场在此有一种仪式感,如剧场中的红幕帘,当幕布降下,我们陷入神秘中,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它再次升起时,舞台会被什么所覆盖。
也如林奇电影中常见的缓慢推镜头(以本作中的原子弹爆炸镜头为代表),摄影机聚焦在某处,随之缓慢地进入那个黑暗的角落,伴随着微风的声响。
此时观众问自己:摄影机穿过去之后,对岸的世界有什么?
有时迎接我们的是一整幅异境画卷(《橡皮头》),而有时,对岸看上去什么也没有,但一切却早已随之改变(《穆赫兰道》)。
这自然也是对连贯性的分镜和延续性思维的挑战,它确保我们时刻保持高度的思维集中——这不是一条笔直的路,它不断地跳跃,穿梭在非线性的时空中,它们是林奇作品中的虫洞(在本季《双峰》中还真的出现了“虫洞”),既是捷径,也是幽暗的小路。
/红房间/THE RED ROOM红房间或许是最象征性的林奇舞台,它是由所有上述灵感凝结而成的综合体:一个有限的空间,但有着无限的可能。
25年前,库珀穿行于此,观众与他是同步的,没人知道下一个房间里会出现什么,因为每个房间的外观看上去一模一样。
这次重新见到它,带来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它实在太令人熟悉,但又远称不上亲切。
我们进入了一种介于知与不知的混沌状态:我们明显感受到其材质的变化,不再是通透的亮红色,而是厚重不透光的暗红色丝绒,数字摄影极强的锐度打碎了胶片的梦幻感,每个细节都变得清晰而实体,甚至16:9的高清电视画幅也令观感变得更加不安,似乎这个房间会按照画幅而发生空间变化(事实上这一点在《与火同行》中已经有显现)。
在《双峰》彻底打开其世界观之后,这早已不只是一个做梦的地方。
红房间的命名又有不少争议:跳舞的小人在第二季称它为“等候室”;大多数时候,我们称它为“守夜门/黑屋”(Black Lodge);但此时的我们,是不是只看到了地板上的深褐色条纹,而忽略了那浅黄色的另一半呢?
在《与火同行》的最后,正是在红房间中,劳拉和库珀笑中带泪地沐浴着天使的阳光(在《回归》之前这一直是“双峰”世界的终极影像),此时的它难道不又是“守日门/白屋”(White Lodge)?
同时,我们又不能咬定便利店上方的房间又是一个完全邪恶的地方,库珀的邪恶双生能在此囚禁戴安(化身为Naido);而当劳拉在《与火同行》中穿行于此时,她认识了自我,洞穿了未来;当真正归来的库珀和MIKE来到这里时,它又在执行着不同的使命,消失的探员菲利普·杰弗里斯(大卫·鲍伊)似乎也是一个中立者,只是时空中的指路人。
我也不认为Fireman在紫色海洋上的房子就是那所谓的“白屋”,Fireman能在这里生成神圣的劳拉灵魂,但当库珀在第三集坠落于某地,看到被囚的戴安时,他也看到了阳台上的那片海洋。
这两个地点是相互连接的吗?
或许命名和定义本身便是没有出路的,存在的变化莫测,正如霍克意味深长地解释的一样:“火的属性的变化,取决于使用者。
”/观众/AUDIENCE没有什么剧集或者电影的评论中,有如此多的像《双峰》的这样涉及到“观众”这两个字。
归根结底,还是要返回它最初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属性。
作为一部公共台剧集,随拍随播的特点几乎让它不可能不被大众的需求所劫持,“谁杀了劳拉·帕尔默?
” 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阴霾,也揭露了电视骨子里只是无尽的信息交换的真相,而《双峰》正是电影派去征服这个“信息堡垒”的特派员。
这也是当时的结局:时任ABC电视网总裁的鲍勃·艾格迫使林奇和弗罗斯特揭露真凶的面目,如林奇所言:“这是宰杀一只下金蛋的鹅。
” 虽然事后证明,这场关于创作权力的争夺还是结下了意外果实:林奇揭露凶手的第14集(第二季第7集)成为了《双峰》中最经典单集之一,在其惊人的结尾段落中,林奇在写实恐怖的凶杀场面和朱莉·克鲁斯忧伤的致幻歌曲之间剪辑,创造了整个第二季的情感高潮;《与火同行》则让林奇在摆脱了解密的压力后重返劳拉这一核心人物,上映时的恶评不妨碍后人认清这是他最具人情味的电影,甚至开启了林奇电影风格的一个新阶段;当然,没有这一系列变故,也不可能有25年后《回归》的出现…… 但观众作为一个核心元素,时时刻刻让《双峰》充满了一层来自戏外的悬念,是一场每周更新的解密游戏。
《双峰:回归》没有选择重走原版剧集的路子,而是一部一气呵成,由林奇和弗罗斯特两位作者全权主使的作品,但它在首播时依旧完美复刻了25年中这种戏外的,来自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悬念。
在每一集播出后,观众们便开始猜测各种元素的意味,而除了不少无理取闹的理论以外,大多数时候观众们的细心观察会获得来自作者的回报。
一个绝佳的例子是当剧集首播时,人们纷纷议论到第四集中坏库珀在监狱里疑似说漏嘴的倒转词语“yrev”(“very”)是何意图,意外的是,林奇竟然在三周之后亲自以戈登的身份解密。
这也是为什么Showtime的周播模式更适合本剧,而不是像网飞的剧集一样一次性放送。
《回归》必须选择一条更具险境的路,并邀请观众一起上路,与两位作者一起踏上这“试图”回归双峰镇的路。
/空间/SPACE在双峰镇外,林奇和弗罗斯特绽放着灵感之花:拉斯维加斯、南达科塔州、蒙大拿州、费城、纽约、新墨西哥、甚至还有阿根廷、巴黎、五角大楼…… 一连串的故事与幻想在这里发生,FBI探员们乘坐私人飞机在各地打探,“坏库珀”驾着他大男子气的黑色卡车随电流奔波,寻找着“坐标”,作为导演的林奇则借助剪辑之手穿行于各处,拼接起线索…… 而在双峰镇内,我们看到的一切似乎都进入了停滞状态:人物长时间被困在自己的空间里(本·霍恩、奥黛丽、无法理解手机的露西、永远呆在RR餐厅的诺玛),或者迷路在某地(杰瑞),或者经历各种痛苦的怪象(鲍比目睹枪支暴力,紧接着,伴着刺耳的鸣声,他看到一个呕吐的女孩;坏警察查德与酒鬼;无处不在的家暴和性侵犯;毒品继续统治着小镇地下经济;理查德·霍恩的恶行)。
/帕尔默的家/PALMER’S HOME启动于2012年,林奇和弗罗斯特在这之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构建《回归》前两集的剧本,而在这两集的末尾,当从红房间坠落的库珀在与第一集的玻璃箱会合后,一个莫比乌斯环俨然形成。
似乎这也是整个剧集结构的缩影,一个不断叠加的循环,而这将在最后两集中完全达成。
这些循环的终点甚至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帕尔默家的房子,臭名昭著的708号。
在《与火同行》中,我们目睹了劳拉一家的痛与苦,25年后的今天,唯一还留守在这屋子里的,只剩下萨拉·帕尔默。
这奇妙的一场戏几乎是从未在林奇以往作品中出现过的情景——一个完全的私人时刻。
与此同时,静止的中景镜头,以及那些沉默的日常图景,这是林奇的“让娜·迪尔曼”式时刻,同样也是母亲的故事。
萨拉也曾是一位母亲,格蕾丝·扎布里斯基沉默的注视与她的尖叫一样令人不安。
我们这次见到萨拉时的这个画面,和《与火同行》中劳拉最后一次和萨拉道晚安时的构图几乎一模一样,唯独这次,我们看不到刚好被放在画框左侧外劳拉的经典肖像(这幅肖像在这一季依旧重要)。
她还没走出这个阴影,恐怕再也走不出了,一切都在这沉默,和这野兽的嘶吼中呈现。
但你可能会问,为何突然选择剪到这里?
我们前一秒看到的,是库珀飘落在太空中,不断加速,不知要去往何方;下一秒,是萨拉坐在幽暗的客厅里看野兽残杀。
林奇在本季中看似僵硬的转场有时看上去毫无逻辑,乍一眼确实令人费解,但联系一下剧集的发展:1. 萨拉显然已经被超自然力量占领(第十四集);2. 玻璃箱被证实是坏库珀的创造(第十集);3. 当坏库珀找到他想要的坐标后,Fireman一开始要将其传送至帕尔默宅(第十七集)。
于是,不妨这么假设林奇的思路:库珀被红房间设套后进入坏库珀设下的陷阱(玻璃箱),本该被传送到帕尔默家,直面最为邪恶的“朱迪”(此时她还需要暴力的电视节目获得“Garmonbozia”——《双峰》世界观中恶灵的能量,以奶油玉米作为视觉符号,象征着人世间的痛与苦)。
自然,林奇不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下子将所有人剧透,但这个小伏笔,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电影/CINEMA面对本作中变化多端的空间,观众或许更多会去纠结于一个力图模仿物理世界的时空逻辑,但终究我们正在观看的,是完全由电影意识创作出来的作品:如果失去叠化、倒放与蒙太奇,我们便不可能看到库珀如何进入红房间,并实时感受到其关于有限和无限之间交错的魅力。
在《回归》中,不少时间被花在角色单纯地在夜晚驾车,或是走过一个门廊,或是站立在某处等待,或是在闪烁的跳接中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中。
当库珀巨大的面孔叠印在皆大欢喜的警局团圆时,他那放慢的低沉声音说到:“我们活在梦里” (“We live inside a dream”),那么这个梦便只可能是电影,一个用纯粹来自电影的想法来承载的梦,这也超脱了《穆赫兰道》中,那个需要用冲向枕头的主观镜头来暗示梦的状态的林奇。
在《回归》中,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析将被纯粹电影的言语取代:Fireman的剧场里挂着一块电影银幕,而正是在这之中他接收到了关于世间黑暗的影像,而正是如此,他才得以向银幕的方向投放金色的灵魂(第八集),并操控角色在场景之间转换(第十七集);这解释了影片中的部分角色为何在叠影中消失/出现,或是有时直接从银幕中被抹去;第三集开场不断倒放/正放、快放/慢放中混乱的电影时间告知着我们危险的到来;在同一集中,从一个房间上升打开天窗,我们忽然发现自己身处在宇宙之中(正如玛雅·黛伦的作品《在陆地上》中,她利用对应动作的剪辑在无限多个空间中爬行奔跑);当剧集试图调和一些演员的离世时,林奇则从过往影片中直接抓取他们的影像,让他们以幽灵的方式继续存活下去…… 当戈登在2017年打开酒店的房门,劳拉在1992年向唐娜呼救的影像忽然叠印在门前(第十集),戈登的脸上写着不解;而在之后,他则在梦的重述中直接看到过去影片中被留存下来的自己(第十四集),于是才想起来杰弗里斯探员当年给他的提示。
这两个影像均取自《与火同行》——一个看似突兀的举动。
而当库珀抵达他自己的使命时,他正是降临在这部前传的结尾——新拍的影像和这部25年前拍摄的电影(转换为黑白)互相剪辑在一起,这部电影的存在允许他去做出改变历史的危险举动。
在本季最美的一组镜头中,坏库珀和一个“伐木人”缓缓步上通往便利店上方的楼梯,他们在电流声中闪烁地“消失”在叠影中,随即林奇选择叠化到一个幽暗森林中的推进镜头——一个完全印象派的动作,是这个镜头在精致的声音中缓缓前进,才将我们送到彼岸的超自然房间中;而当坏库珀走到房间的尽头打开门,音效突然变得自然化,他开门所见的看上去只是一个汽车酒店而已…… 因此,什么才是超自然?
或许它正隐藏在看似平常的空间里。
/路屋酒吧/THE ROADHOUSE于是,路屋酒吧(Roadhouse)或许成为了本季中所有双峰镇内地点里最诡异的一个——一个早已被幽灵化的场所,它看似是停滞在90年代,是一个能拥抱“双峰”世界所有美好景象的地方。
这里是观众聚集的中转站,他们在舞池中伴随着当集的乐队摇摆,如电视机前的我们,不论我们如何接受或拒绝剧集中碎片般的情节,但永远有那么一个自我愿意无条件地把自己抛洒在这里,因为这是那个经典《双峰》的象征。
不论这里放的是朱莉·克鲁斯的梦幻歌谣,还是九寸钉的重金属,人们都想来到这里(整个回归季中最令人“气愤”的奥黛丽情节,完全围绕着“去路屋酒吧”这个引子展开),而在本季一半的单集中,我们也是在此和所有的故事短暂作别。
但与此同时,酒吧又时常拒绝简单的音乐诱惑,上演着最令人匪夷所思的随机戏码。
第二集结尾来自Chromatics令人无比畅快的《Shadow》开启了“双峰”世界这个新的传统:我们看到熟悉的角色,熟悉的音乐,但一切都以现代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部出色续作的象征。
随后放送的两集中也以同样的方式结尾,选用的歌曲也都比较轻松。
从此以后,我们在每一集中都会期待酒吧的出现,而有时它也带来伤感,因为经常这也意味着单集即将结束。
林奇和弗罗斯特一直以来都是培养观众这些小习惯的大师,但不必多说,他们也是最擅长去打破这些习惯的人,这也是本剧的慷慨和秘密,我们总是有所期待,而作者常常能满足这些期待,但一切并不总按照我们的期待而展开。
不过,在欣赏音乐和品味这些美好时刻的同时,或许不应该忘记路屋酒吧在剧中的拥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雷诺家族。
为了专门强调这点,两位作者甚至不惜请回了原版剧集中被杀的雅克·雷诺,让原演员Walter Olkewicz扮演一位雷诺家族的新成员来管理酒吧。
作为劳拉谋杀案中关键的涉案人之一,你一定记得弗罗斯特是如何在他导演的第一季第八集中对准他的嘴唇,拍摄他下流的言行。
在《回归》中,他的言行也没有好到哪去(参见第七集“臭名昭著”的扫地长镜头),是借他之口我们意识到,双峰的地下色情业仍然泛滥,林奇带回这个角色,他的秘密提醒我们,当年的劳拉是如何陷入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面中,并最终导致她的死亡。
因此路屋酒吧中的舒适注定也是短暂的,它也随着音乐风格的变化而无限地发生着变异。
因此可以非常大胆地说,在《回归》中,红房间的关于“有限/无限”的能动关系已经被延伸到了“双峰”世界的每个角落,甚至在库珀的视线中,它更能够被“随时”激活(红房间中,独臂人MIKE时常闪现在半透明的图层中,甚至能隔空传物)。
而路屋酒吧自从原版剧集以来便是超自然力量的光顾之处,当杀害劳拉的真凶被揭露时,也是路屋酒吧中的人们首先感应到悲剧的“再次发生”(It is happening again)。
这种离奇的现象在《回归》中以一种更为磨人的方式呈现,它体现在那些坐在小包厢里的随机人物,和一种疑似平行时空的存在中。
以第八集作为分割线,从第九集开始,这些随机的人物开始出现在路屋中,她们(她们几乎全部是女性)只会出现一次,随后便再也不被提及。
正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拉开红房间的帷幕时会遇到什么,路屋酒吧的这些随机人物,以及她们的故事——肥皂剧式的剧情、时不时的危险侵入、暴力无处不在、以及偶尔闪现的关于“主要”情节人物的线索等等,同样被给予一种这样的不安感。
就如第一次观看林奇回归执导的第二季季终集时的难以适应一样,面对这些和“主要”剧情毫无干系的人物,观众的第一反应是疑惑,甚至愤怒,抗议为何不把这珍贵的时间送给更“重要”的人物,这种疑惑情绪在第十二集开播,盼天盼地终于盼来奥黛丽,得到的却是如此冗长诡异的对话情节后达到顶峰。
但林奇和弗罗斯特在本季中对双峰镇这个空间的描绘,是没有任何所谓的“重要”或“不重要”可言的:除了双峰警局和路屋酒吧这两大常驻元素外,任何其它的场景或多或少都以看似随机的方式被抛出。
这种思路确实令人困惑,但另一方面,更可以说是一种平等。
在《回归》的世界中,即便其情节再令人感到随意,一旦一场戏被抛出,一种对节奏、语言、步伐、声音、分镜头严丝合缝的控制便体现出来,即便当它们只是两个看似无关人物的谈天说地,或是对一根电线杆、一只脚的注视,连一只咖啡杯的特写也充满光泽,每一场戏似乎都是一部独立成章的短片,被放置在《双峰》这个拥抱无限的容器里。
/“你叫什么名字?
”/“WHAT IS YOUR NAME?”每一集的最后,凯尔·麦克拉克伦的名字的出现揭示单集的结束,但库珀,不论是哪个形态,并没有大量出现在每个单集中,在某几集中,他的出场时间甚至不足一分钟!
只有最疯狂的电影人才敢作出如此的决定。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谈论库珀。
毕竟,这是一个无限的容器,因此不妨来窥测这些无限。
路屋酒吧的人物真的如此“随意”吗?
第十二集中奥黛丽和查理报菜名式的人名游戏令人头疼,是不是?
事实上林奇和弗罗斯特早有暗示,也是通向本剧最后终极时刻——第十八集的预防针。
再者,这种危险而暖昧的暗示还通向了另一条路,通向现实世界的路,这些“随机”的暗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故事将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你永远猜不到门后站着的会是什么。
倒回到第一集,此时的我们对《回归》的格局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但纽约市的玻璃箱,以及萨姆和崔西,不正是两个最经典的“随机”角色吗(同酒吧里的角色,这对年轻情侣在被“Experiment Model”残忍杀害后也很快从故事中消失)?
更明显地,就在某一个关键时刻之前,林奇和弗罗斯特选择加入这么一场令人好奇的滑稽情节。
是的,那个时候的我们才只是好奇,还未能通向困惑:一个叫Majorie Green的女人(Melissa Bailey曾在《穆赫兰道》里饰演了被倒霉枪手误伤的邻居,显然她又租错房了)带着吉娃娃狗(想及第二季里戈登·科尔的笑话)走在公寓过道上。
女人手臂上挂着的钥匙丁零当啷地发出着各种响声,而钥匙正是本场戏的关键。
滑稽的是,我们却花了接下来的五分钟时间和至少四个角色来找到它。
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恶作剧,在短短几分钟内,我们听到了一连串的名字:Barney、Ruth、Hank、Harvey、Chip…… 除了Hank,其他人都只在对话中出现(以及一个失去身体的死者),Chip还没有电话,而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将消失在之后的情节中。
虽然在之后的十几个小时中我们虽然不怎么再听到上述名字,但是一连串新名字陆陆续续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Red、Billy、Bing(Riley Lynch的角色,在双R餐厅门口问“谁见过Billy”)、Trick、Chuck、Clark、Angela、Tina、Carrie Page、Alice Tremond……;甚至还包括我们以为自己熟悉的,也以扭曲的面貌出现:萨拉·帕尔默、“朱迪”、杰弗里斯、理查德、琳达、甚至库珀自己…… 或许有一种关于名字的身份政治,这既是一种毒药又是一种幸事。
或许只有在《双峰》的世界中,几个简单的人名能产生如此效应,正是因为《双峰》作为一个成体系的世界拥有如此多的标志,但其作者又如此偏执地希望能偏离所有人的想象。
林奇和弗罗斯特完全可以不给这些角色赋予名字,将他们彻底随机化而帮观众消除这些疑惑,但她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名字,正也是她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证明。
林奇和弗罗斯特在整个十八集的旅程中一共安排了多达280个大大小小的角色,一共39位原版剧集的演员回归出演,两位作者从没有选择偏袒任何一方。
再拿第一集举例,纽约的萨姆和崔西两位新角色,以及鹿角镇的比尔·海思汀的情节占据了第一集几乎全部的时间,林奇最高度集中地呈现了这两条故事线,而流畅地穿插于其中的老角色——本、杰瑞、露西、圆木女士、杰科比医生……,虽然看上去戏份精简,但短短几分钟内,作者还给观众他们所熟悉的。
正如《手册》在评论中赞誉到:短短一瞥即可,只需要明白,他们还在这里。
对经典角色轻盈的处理,与新人物之间游刃有余地跳跃,似乎令人感觉剧集从未离开过,因此也无需盛大的迎接派对(只有库珀、戴安和劳拉们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这种礼遇,但这几个角色是无可置疑的中心,也和怀旧/反怀旧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相关),我们只需要直接进入他们生活的世界中。
因此,剧集的这种高度平等的关系确保了当我们进入到其最关键的最后阶段时,观众得以做好准备迎接任何可能性的到来,在将《双峰》的世界逐步扩展到它的最无限边缘的同时,并部分满足观众对于延续性和结局的渴望。
在《回归》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场戏中,库珀(或是“理查德”?
)问出了两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和“现在是几几年?
” 这是剧集中“我是谁我在哪?
”式的存在主义时刻。
完全不巧合地,这也是我们在整部剧的过程中常常问自己的问题。
除了那些四处抛洒的人名之外,全剧中发生的年份时间也是一个谜团——除了第八集中明确表示的1945和1956年(一方面越是清晰的科普和诠释,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更强大的未知),我们也无从得知剧集发生的年份,这种谜团则在最后一集达到顶峰。
关于时间的问题还会回来。
当库珀在第三集降临到紫色的屋子里,跳接生成的电流断裂感令我们头昏脑胀,此时库珀问:“这是哪里?
我们在哪里?
” 此时,观众与主角一起共享这些神秘,每个人都是侦探,林奇和弗罗斯特的慷慨之处在于对问题的不回避,因为一切观众在问的,作品也在问。
/弗雷迪/FREDDIE让我们聚焦在某一个,可能看上去是整部《回归》中最“随机”的角色上面——弗雷迪,戴着绿色超能力手套的英国小伙。
弗雷迪这个角色的灵感来自林奇,而选角方面,在YouTube上专门发布多国口音模仿秀视频(最早发布于2010年,目前点击量超过3200万次)的Jake Wardle被林奇选中。
这个在第二集结尾操着“异国口音”短暂出场的神秘角色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在回归季所有这些新角色中,林奇对他似乎也是特别偏袒,甚至在剧终时期给予了他最“神圣”的使命之一。
/弗雷迪与安迪/FREDDIE & ANDY正如林奇因其语言天赋而选中他一样,在剧中,处于“上帝视角”的Fireman也邀请了他——一个外人,这个故事在第十四集中由他向“老一辈”的詹姆士·赫利讲述(在这一集中,讲故事这个元素几乎被单独拎出来的作为结构上的骨架,还有戈登讲述他的“莫妮卡·贝鲁奇”之梦,阿尔伯特给塔米探员讲述“蓝玫瑰”之起源,鲍比与父亲的故事,露西关于Bora Bora的故事则令戈登困惑)。
在同一集的前半部分中,Fireman还意外选中了另一个角色——警员安迪,并给他和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影像(和弗雷迪的纯讲述恰好相反)。
就如弗雷迪问Fireman:“为什么是我?
” Fireman回答到:“为什么不是你?
” 弗雷迪的讲述紧接着警局四人在少校的“Jack Rabbit’s Palace”的冒险,不仅在电影形式上是一次优雅的形变,更也能被称为是对安迪的胜利作出的注解。
作为一名老角色,安迪在原版剧集中的“地位”显然在库珀、李兰·帕尔默、杜鲁门警长、本·霍恩、艾尔伯特这些“高级”角色面前显然是“不太高”的,因为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男子气概”。
在第二季的大多数时候,他被编剧们囚禁在自己、迪克和露西之间那条三角恋情景剧中,上演着荒唐的喜剧戏码,一直到最后真正的作者归来,他才勉强脱身,还给库珀指出了通往“黑屋”的关键线索。
但林奇与弗罗斯特一直对他钟爱有加,还在试播集的一开始就给予他难忘而滑稽的一幕:在劳拉的尸体面前,他突然痛哭起来,即便他与劳拉之间毫无交集——这是属于安迪的本真。
我们的两位作者从不怀疑这位看上去天真傻气的警员内在的智慧,这也就有了他在第十四集中的超越。
安迪的故事是一条直线(a straight story),但依旧通向伟大。
回过头来看安迪穿越的这一场戏,初看时确实倍感意外,但从林奇的调度中,答案已然明显:在看到了Naido之后,给予其他三位警员的都是简单的站立动作,而只有安迪蹲下身来紧紧握住Naido的手,眼睛望着天空中的漩涡。
腐败的警察查德在第十七集讽刺道:“这不是那个好警察安迪吗?
” 是的,犬儒的讥讽很快受到了来自弗雷迪的打击,查德从此消失。
弗雷迪和安迪的意外胜利是一种反“男子气概”的必然,正如在剧中“代表”了男子气概的坏库珀(第一集他首次亮相时,小屋里的欧蒂斯像称呼一个皮条客一样亲切地称呼他为“C先生”——贩卖职业杀手的皮条客),不偏不倚地拿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证明了自己男子气概的荒唐可笑。
/弗雷迪与“鲍勃”(喜剧)/FREDDIE & BOB (COMEDY)正如弗雷迪的手套中Fireman给予他的超人类力量,寄生于C先生体内的“鲍勃”也给予了他这样的能力,因此在第十三集前半部分令人捧腹的农场“大战”中,悬念几乎从一开始便不复存在,变为了一场严肃的闹剧。
我们看到一群灰头土脸的高大男人吹嘘到,自己的老大之所以是老大,是因为没人能在扳手腕上胜过他。
当这句话被说出时,想必观众们都已经了解到了事情的结局。
当然,最搞笑的是,正是因为如此,林奇才得以津津有味地拍摄这群男人,如观看一场早已分出胜负的拳击比赛一样,所有热火朝天的吼叫和长牙咧嘴的舞动都变成了纯粹的场面调度,伦佐面对C先生时绷紧肌肉面红耳赤的表情,也成了出色的喜剧表演,被消解的是暴力的竞技运动表面上自发的激情。
也难怪C先生最终的命运看上去是如此的反讽,先是被露西开了历史性的一枪(林奇和弗罗斯特一定等了一辈子这个时刻),随后“鲍勃”的黑色球体则被弗雷迪“呼呼”几下打碎。
一个对漫画式角色的漫画式处理。
弗雷迪与“鲍勃”的大战是被碎片化地剪辑起来的,林奇则亲自持单反相机拍摄那些晃动的镜头,四分五裂的调度,闪烁重叠的影像,一场“肉搏”变为了抽象艺术品。
这也是一次走钢丝式的危险尝试,配合起前一集中(好似从昆汀的《八恶人》片场过来的)詹妮弗·杰森·李和蒂姆·罗斯两位杀手的反高潮结局——被波兰会计(又一个突然冒出的角色)用半自动武器扫射身亡。
载着他们尸体的货车乌龟似地从目睹了此景的两位FBI探员身旁有气无力地爬过,懒懒地踏上了路旁的草地上。
杀手之死,“鲍勃”的结局,与弗雷迪的设计,如同第十六和十七集本身突然加速的节奏和爆炸性的剧情进展一样,对于剧集整体的基调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刻意破坏,但更像是林奇的一次警告。
观众事实上也有知晓,我们下意识地感觉到“鲍勃”的结局是错误的,这个原版剧集和《与火同行》中劳拉·帕尔默面前最恐怖的恶魔不应该如此,在“低劣”的数字特效底下草率收场,不是吗?
但此时,每一个人都是弗雷迪,对美好结局和“终极使命”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因而发生了短暂的失忆,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接受林奇慷慨给予的美好幻想(如同《穆赫兰道》,但这次远没有做一个梦这么简单),唯独不知道还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意外转折将会发生。
/“朱迪”/JUDY但或许“鲍勃”和C先生正应该这么“草草收尾”,因为他们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关键。
“鲍勃”导致了劳拉之死?
是也不是,《双峰》的骨子里是一个原生家庭中家庭创伤和不伦关系的故事,即便剧集再想把李兰·帕尔默和“鲍勃”划清界限,林奇在《与火同行》中也相当明确地展示了李兰作为父亲内心的缺口,他的紧绷与懦弱,最终演化为暴力。
“鲍勃”导致了库珀的分裂的堕落?
同样,是也不是,“C先生”或许只是库珀内心整体的一部分,那个热爱咖啡和树木清香的库珀也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在第二季结尾,也是那个“完整”的库珀主动接受了与恶魔的交易,而这样的错误他还会再犯一次。
戈登/林奇在第十七集开场滔滔不绝地开始解释“朱迪”,看似诱人,这事实上又是一次警告。
是什么驱使神秘的FBI总管突然开始暴露那些25年来他都不愿提及的秘密?
秘密背后更有秘密,戈登告诉我们“朱迪”是某种极端负面的力量(force),于是我们立刻开始在脑海的影像库中寻找某种实体(entity):是被黑暗物寄生的萨拉?
是那个杀死了纽约情侣的幻影?
是德克萨斯州奥德赛(Odessa, Texas)的“朱迪”餐馆?
它们或许都是“朱迪”,但也许又都不是,如果说第十八集证明了什么,它证明的正是对实体,对符号的误解:当你因为库珀在前作中被困在红房间里是最可怕的事情时,或许事情还没这么简单,毕竟红房间即便再如同一个深渊,它终究只是个“房间”,库珀还是能够在某一天“离开”;当库珀被四分五裂成三个形态时,不着急,他总有与自己面对面的一天;但如果他进入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既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呢?
如果这个领域正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呢?
林奇的频谱最终证明的是,任何的超现实场域,最终仍敌不过现实本身的讽刺:在无尽的夜路中驾驶,24小时营业的小餐馆灯光黑暗,或只是华盛顿州的某座平凡的房子。
正如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看了《蓝丝绒》后所定义的“林奇主义”:来自日常与平凡中背后的毛骨悚然。
当然,还是要有来自超现实的辩证来催发出这些秘密,正如库珀化身为“道奇·琼斯”时在案件报告里那些孩童般的画作所揭示的一样。
/道奇·琼斯/DOUGIE JONES道奇·琼斯,一个多么平凡的名字:“道奇”像是那种人们用来称呼家养小狗的昵称,而“琼斯”则是大卫·鲍伊(本名大卫·罗伯特·琼斯)出道时选择抛弃的那个毫无特点的姓氏。
显然,他不拥有库珀所拥有的一切气质:衣品极差(即便林奇拍出了怪异的美感),头上显然戴着假发,大腹便便地躺在空房子简陋的床垫上。
这是库珀能成为的最差的样子,甚至更不济于坏库珀,后者最起码还有些大反派的魅力飘荡在其中,而道奇只能懒散地从脸上挤出几点笑容来,比任何的超现实效果都更加荒唐。
但就在我们还在好奇此君究竟为何物时,他便消失了(第三集),被真正的库珀取代,后者陷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就当我们觉得事情无法更糟时,我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曾经威武的《双峰》男一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还被困在了一个更糟的身份中:幸运7号(Lucky 7 Insurance)保险公司职位摇摇欲坠的推销员,被犯罪团伙追杀,被要挟在赌债中,还因为出轨被妻子嫌弃。
是的,我们得谈谈道奇,不是那个穿着丑陋的黄色西装的赌徒道奇,而是那个让库珀梦游了十三个小时的“道奇”。
《双峰:回归》无疑是一次全新的灵感碰撞,如果说这部作品是一个奇迹的话,“道奇·琼斯”的出现无疑象征着这奇迹所带来的无限狂喜,林奇说:“想要赶走黑暗,你要做的只是把灯打开。
” 特别探员戴尔·库珀化身“道奇”,成为一股闪烁的力量,作者用一种原始却激进的方式让我们重温让这位经典主角如何“特别”的独特美德。
这个沉默的孩童携带超自然场域的引力驱散着一切的虚伪与恶,他一眼一触便识破骗局,他浓缩并简化人们的语言;他恢复原生家庭的和睦,净化竞争对手的心灵,恶势力如磁铁的同极相斥般被道奇反弹回去。
然而这也是林奇最悲情的讽刺。
“道奇”是一个“不自然”的人工产物,被困在库珀的身体中,但依旧是个朱巴(tulpa),一个不现实的极善者形象,像一个无意中在考试里考满分的“笨学生”,他孤独地站在西部牛仔的雕像下(第五集末尾),他的运气和美好结局只属于电影——这注定是一个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是最纯粹的狂想曲。
如此热爱“道奇”,并不是要没有理由地热衷于孩童形象与乐观主义,而是因为林奇的调度从来不缺乏悬念,以至于林奇放慢一切的速度让你关心他:你感受到他新生的身躯慢吞吞地行走着,偶尔撞上一面玻璃墙;他触发赌场里的疯狂,一眼洞穿老虎机的假象,警铃声(模糊的所指:逮捕我还是奖励我?
)伴着硬币的叮当作响,与“HellooOoOOoOOooo!”形成了音乐;他几乎是雅克·塔蒂喜剧中的于洛先生,还把他自己身体中丧失的感官体验扩散到了一切与他交集的人当中,他笨拙的肢体运动竟神奇地让对方感受到情感,你从未能够如此细细观看凯尔·麦克拉克伦这位林奇老朋友的脸,他的沉默和僵硬中反射的迷失与记忆。
他看到腐败的保险员工安东尼脑门星空一般洒在西装上的头皮屑,后者泪眼婆娑地决定改邪归正(戈登在第四集中高喊“Fix Your Hearts or Die”);纳奥米·沃茨饰演的Janey-E再一次感受到了快乐,并喷发出内心对金钱与官僚世界的愤怒(第六集中一人单挑两个赌本的她不能更加强悍,弗罗斯特的政治宣言时刻,正如杰科比化身“扩音医生”(Dr.Amp));看上去像是刻板的黑帮老大角色米彻姆兄弟们一遇上他,则陷入了狂欢之中,排起队跳起舞;他的老板布什纳尔——一位前拳击手则发现了超验的魅力。
在第六集中,当他看到“道奇”的信手涂鸦,困惑并怒斥道:“你要如何指望我怎么去理解它?
”而“道奇”呢,则只是默默重复着:“去…… 理解它。
”(“Make… sense of it.”)于是,他便立刻看得一清二楚。
当第十一集中,赌场的流浪老太(琳达·波特)穿着一身华丽的服饰和儿子伴着巴达拉曼提的新曲子突然从背景里现身,对着她眼中的“头奖先生”(Mr. Jackpot)无尽道谢时,我们内心猛然一震。
观众也中了头奖:这是本作中最出乎意料的情感时刻,堪比任何弗兰克·卡普拉电影的结尾。
三千万美元的支票和一块樱桃派才让道奇逃脱了杀生之祸,而价值两万八美元的两个老虎机头奖,却让这个看似不值一提的龙套蜕变为了整个《回归》里最令人感动的角色——实话实说,没人指望,也不会有人在乎她是否归来。
但林奇和弗罗斯特让她回来了,并不只为了让我们看一个贫穷的老太是如何一夜暴富,她中的钱远远少于“道奇”,但对她而言这都足够,两位作者要我们看她如何从第三集中厌世贫瘠的赌徒形象中摆脱,绽放出惊人的尊严、慷慨和饱满的人格魅力:她看着这位失语的“特别”探员,如看着自己亲生的骨肉一般。
她的华服和房子、她的狗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名下的肆意消费,林奇只为了证明这一点点小小的推动,即便残存在拉斯维加斯本质的荒诞与虚伪中,仍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在之后不会再见到她(该演员在剧集播出后也去世),但是这影像、音乐和表演,足够让我们相信。
/相信道奇/BELIEVE IN DOUGIE梦醒时分,库珀告诉MIKE让他用“种子”重造一个新的道奇,后者在第十八集开场实现了库珀给Janey-E和Sonny Jim的诺言,敲响了那个红色大门,这个新的家庭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一集中唯一的幸福时刻,从此之后事情将朝着一往无前的黑暗驾驶,脱离前两集中架设的怀旧美景与理想主义,返回到我们被困的现实中。
林奇和弗罗斯特在这里提醒我们“道奇”本质的假象,但最起码,“道奇”的伟大还能在这部作品里被反复重温,作为一种理想他并非一无是处。
是的,在库珀慢慢陷入到“理查德”这个混沌状态中,绝望地试图改变过去而进入新的深渊时,我们反而开始怀念“道奇”,那个令人烦躁的,笨拙的,“浪费”观众时间的“道奇”。
/寄语/THE MESSAGE“霍克,电流声鸣响着。
你在山间与河流中听见它。
你看到它在大海与星空中舞蹈,在月亮四周闪光,但在如今,这闪光渐渐淡没。
在那黑暗中还能残存什么?
杜鲁门兄弟两人都是真正的人。
他们是你的兄弟。
而其他人,那些优秀的也与你站在一起。
如今,这个循环即将化为一个圆。
仔细听,仔细看,那时间与空间的梦。
像一条河流,一切都涌动出来了。
那些存在与不存在。
霍克,劳拉就是那唯一。
” (圆木女士,第十集)
/便携录音机/TAPE RECORDER第二集,在南达科他州,预料到事情异常的“坏库珀”在汽车旅店包围了毫无防备的Darya,我们立刻感知到,她完全暴露在危险甚至死亡当中。
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在林奇作品中持续被审视,从《蓝丝绒》里的丹尼斯·霍珀与伊萨贝拉·罗西里尼,到《我心狂野》里的威廉·达福和劳拉·邓恩;而《双峰》更是其中的代表。
而这一场长达8分钟的审问剩下的,仅有Darya绝望的无用功和坏库珀绝对的冷漠,而观众都已知道结局。
与此同时,林奇通过动作和台词的叠加强化了这种残忍——Darya反复试图逃脱,多达4次,而每一次她都被坏库珀拉回,毫无招架之力。
巨大的人物特写让观看这场戏更加充满不适,形成一种视点中立的可怕的理性。
麦克拉克伦在这一段中的演绎堪称极致,我们无法把这个人物和“真正”的库珀联系起来;然而触发两人冲突的,却是一段库珀通过便携录音机监听到的电话,而没有什么,能比库珀在此时掏出一个黑色的便携录音机更为恐怖的事情了。
任何一位看过《双峰》的观众都会明白便携录音机对于库珀这个人物的意义——尚未登场的戴安。
曾经,我们总是看着库珀通过一支录音机向戴安报告情况,或在前往双峰镇的车上、或在双峰镇警局、或在北方大饭店的315房间,等等。
这个在当年从没真正亮相的角色,可谓是库珀的最佳拍档。
现在,坏库珀携带一支类似的便携录音机登场,虽然并没有喊出标志性的“戴安……”开场白,但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暗示:如果他将这位最亲密无间的搭档也转变成了被邪恶附身的傀儡,会发生什么?
作为观众的一员,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戴安……” “DIANE……”尽管直到最后,我们才意识到戴安在《回归》的第三集便已某种形式出场,但当劳拉·邓恩饰演的她在第六集中的现身,仍然是一次又惊喜又令人警惕的举动。
库珀在整个《双峰》世界中的第一句台词,喊的便是她的名字,因此从一开始,即便作为一个无形的角色,戴安便与劳拉·帕尔默一样令人熟知。
跟布满全剧的超自然力量一样,无论是死去的劳拉,还是始终只出现在库珀台词中的戴安,这些无形的角色或者力量一直如此笼罩着剧集中的世界,更作为被动的客体而被代表着。
因而当戴安的真身出现时,被代表的客体忽然间成为自主的整体,正如我们直到《与火同行》才亲眼目睹真正的劳拉,强烈反差所带来的未知气息反而加剧了角色的神秘,她全部的真相更是一个混乱的迷宫。
果然,最终(第十六集)我们发现,这个银发的戴安并非是真正的戴安,而是如原装的道奇一样,被坏库珀控制的傀儡,正如他的黑色录音机所暗示的,只不过坏库珀并不像我们心爱的探员一样对着自己的录音机持之以恒,这个恶灵附身的杀手只是将戴安当作随手激活的工具,正如他那些用后即焚的一次性手机一样。
/戴安/DIANE林奇和弗罗斯特以极具挑拨性的方式逐渐揭开这个版本的戴安的面纱。
她粗俗的语言首先打破我们对这个秘书形象的刻板认知(“去你*的,戈登”),随后在第七集与坏库珀在监狱里关键的对话中,我们意识到,有一件糟糕的往事彻底地异化了这对搭档之间的关系,猜测是容易的,但我们却更愿意不把它当作是真相,即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那唯一的可能性——在这消失的25年间,坏库珀如曾经的李兰/“鲍勃”一样性侵了戴安(这个故事在第十六集终于以最为痛苦的方式述出,邓恩最好的表演之一)。
这一《双峰》骨子里的黑暗历史如1990年底的揭露一样令人恐惧,令人无法直视。
在劳拉的谋杀案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的当年,人们纷纷对“谁是真凶”这个问题下起赌注,但丝毫不出意料的是,李兰·帕尔默排在这个榜单的末位——没人会相信,或者愿意相信这个悲痛的父亲正是这个家庭恐怖的源泉,就如扮演他的雷·怀斯也不愿意相信,即便他在剧中已经动手谋杀了雅克·雷诺(习惯了影视剧复仇戏码的我们会说这情有可原),头发也一夜之间变成了“鲍勃”的银色,并像红房间的小人一样跳起了舞。
“今年是几几年?
” 答案:2017年(《回归》播出的年份),川普登台美国的第一年,#MeToo运动的第一年。
人之本性决定了我们不愿意听到最坏的消息,正如当在路屋酒吧里突然侵犯邻座年轻女性的男子被发现名为理查德·霍恩时,我们即便猜到他必然是坏库珀在25年前在医院强奸昏迷的奥黛丽导致的恶种,我们也宁可不去相信,并在脑内试图延迟真相揭露的时间。
讽刺的是,我们又是如此热衷于知道真相,热衷于让事情画上句号,这样我们便能忘却并继续前进。
戴安的例子则更为复杂,因为我们意识到她或许除了是坏库珀的受害者以外,还是他计划中的帮凶。
第九集时,当戴安第一次收到来自坏库珀的神秘短信时,“戴安是反派”这一可能性便被慢慢建立起来,但我并不愿意相信,在潜意识中拒绝接受:“戴安不可能这么做!
” 遗憾的是,在《双峰》世界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于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现出来:她目睹了比尔被爆了头,偷窥阿尔伯特得到的坐标,并给坏库珀泄露情报。
但正如剧集结尾的“真”戴安,这个“假”戴安看上去也是如此真实,因为她即便作为一个人工复制品,她与原装道奇的性质完全不同,这也归功于林奇与弗罗斯特出色的模糊化处理,和邓恩立体的表演。
在许多时刻,她展现出来的极度压抑的情感,怎能让我们相信她背后受控的程序?
这个戴安虽然是“假”,但又是一种异于一切的人格分裂,她的冷漠不代表她就不能时不时召唤出那个远在天边的“真”戴安。
“库……”,当在第十六集中收到来自坏库珀的终极使命时,银发戴安在震惊之余对着控制自己的手机轻轻呼唤到。
这显然是真正的戴安,用她自己的声音在呼唤真正的库珀(刚刚从“道奇”的梦中醒来),而不是那个“去你*的”戴安。
劳拉·邓恩在最终的讲述中奋力与恶魔般的往事抵抗,在这无形的较量中,是那个真正的戴安在揭发坏库珀的恶行,也是那个真正的戴安在给困在酒店里的FBI探员里指明方向(他们已经有连续五集之间呆在这个酒店里),也是她在用力呼喊着:“我不是我!
我不是我!
”(“I am not me!”)她必须选择拔枪射向自己的老朋友,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坏库珀的控制中摆脱出来。
这与《与火同行》最后劳拉面对恶魔时必须做的牺牲显然是异曲同工的,于是在被销毁之前,她才得以非常自豪地,端坐在红房间里对着它(以及她的施暴者)爆最后一次粗口。
这便是银发戴安伟大的矛盾。
/时间/TIME露西如是说:“这得看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是说,有时候我甚至都没时间去想任何事情。
有一次安迪甚至觉得时钟都停了,结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完全忘了时间,感觉像是无限。
”这句话发生在第十集,而当我们纵观整部剧集的节奏,我们会发现从第八集的疯狂之后,林奇和弗罗斯特在接下来的五集(即第九到第十三集)中,似乎把频率放慢了不少,与此同时带来的,便是露西所说的时间上的混乱和运动的停滞了,尤其是在双峰镇内的情节中尤为明显。
在第九集中,鲍比、霍克和警长一行来到鲍比母亲的家中,后者给了他们少校留下的最后秘密,提示他们要在两天后去“Jack Rabbit’s Palace”,然而这一行动却一直要等到(首播时现实时间的五周后的)第十四集才发生,而在这之后剧集也将开始快速地前行,往终结而去。
连时间顺序甚至也出现了断层:鲍比在第十三集时前往RR餐厅吃饭碰上了艾德·赫利,此时他却说是在今天“发现了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
时间漩涡的可能性不断地被暗示:萨拉的电视上播着一段反复循环的拳击比赛录像(第十三集),路屋酒吧之前的客座乐队再次出现(Au Revoir Simone和Chromatics),杰科比医生的广播被完整重复,甚至还有像是被刻意设计的穿帮和不连贯(关于这个可以写一整篇文章,但由于实在无法区分出故意作为的不连贯和制作疏忽导致的错误,还是暂不深究)。
更巧合的是,如果仔细观看影片中给出的线索,我们正是在第九集才第一次知道剧集本身发生的时间:9月29日!
而在之前的八集中,除了闪回中给出的两个年份和库珀离开红房间的“253”,时间和日期都是被刻意地模糊的。
回想原作中清晰的时间:《与火同行》把时间线限定在劳拉被害前的一周时间内;前两季剧集则严格按照一集一天的速率前进,连库珀出场时的第一句台词就是播报时间和空间——“11点30分,2月24日,开车进入双峰镇……”,FBI探员把自己经过的地点一个个地细数了出来。
从一个本来能清晰地知道自己所处时空的世界中,我们是如何一直来到现在这个处境中?
在《回归》中,这种流畅的运行是被禁止的,似乎是剧集在以电影的线性运作时,把物理的时间抛在了脑后一样。
而这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因为在数不胜数的时刻中,时间固执地以平缓匀速的方式度过着,在那段时间中,好似我们被永远困在现实的速度中,作品让我们感受到每分每秒。
此时,这表面现实的速度好似也是某种超现实:杰科比医生慢条自理地对着他的铲子喷绘(第三集),林奇拍摄下这平凡的工作,如同他自己在工作室里完成一件家具或画作;第七集我们看着一个人扫地整整两分钟;下一集,一个同样两分钟长的镜头往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缓缓冲去;邪恶的爬行生物缓缓从一颗蛋中孵出;女孩睡着在床上,静止的镜头看着她悄悄被寄生;戈登、塔米和戴安在警局门口静静地站着抽烟(第九集);法国女人滑稽地起身离开,戈登看得津津有味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了疲惫的阿尔伯特颇为无奈地看着他们的游戏(第十二集);“道奇”和Janey-E在第六集开场长近15分钟的对峙,最终他默默地在桌上作画。
这种时间上的变奏也恰如其分代表了了库珀、坏库珀与“道奇”这三个“分身”的时空观。
当我们反复被MIKE提醒“这是未来?
还是过去?
”时,我们以“完整”库珀的视角思考,而这时,几个库珀的时空观之间存在分裂:谨守于其英雄使命的“特别探员库珀”执迷于过去,一头扎进那笼罩着他25年人生的囚禁,那些他无法拯救的人,那唯一一个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坏库珀的眼中只有未来,一个他已经预见的毁灭结局,因此他制定重重计划和阻碍来阻止结局的发生,永远行驶在慢慢长夜中,沿途中都是暴力和痛苦,这是他的悲剧;而无须多言,“道奇”是一个完全处在当下的人,他不知道过去也不会想未来,他是库珀内心中那个能每天享受咖啡和樱桃派的人格,是那个在原剧集中说出“每天给自己一件礼物”的库珀。
混乱源自什么?
在《双峰:回归》中,时间混乱的到来正是源自对过去和未来的执迷,这一对本身在“现实”时间中本就“不存在”的矛盾体是两个诡怪的极端,正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不可调和造就了我们体验的种种困惑和恐惧。
/急救行动/EMERGENCY RESCUE《双峰:回归》面对的,终究还有它自己的时间,它必须回归于2015-2017年,正如劳拉在曾经预言的一样。
前所未有地,一部重启的续集选择在当下,在现实中演员的衰老中寻找那些迷失的时间。
我们总是对原版剧集中的俊男靓女津津乐道——演员之爱是强大的。
在《回归》开始拍摄的2015年,林奇69岁,弗罗斯特61岁,凯尔·麦克拉克伦56岁。
属于劳拉·帕尔默——雪莉·李的时间也没有冻结在1989年的那张老照片,或是她冰冷尸体的面孔中,林奇选择让她以如今的年龄出现在红房间里,在数字摄影机的高清注视下,每位回归的演员上岁月的皱纹清晰可见——劳拉、MIKE和库珀脸上来自岁月的痕迹无不让我们记住,这25年过得有多长,即便是在如红房间这样看上去无视时空法则的超验领域里,也是如此。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衰老和死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双峰》的主题之一。
“你认得出我吗?
”,劳拉瞪大着眼睛提醒库珀,似乎同时也在质问观众,我们也将信将疑,像库珀一样回答道:“你是劳拉·帕尔默?
” 对于林奇而言,这之间包含的隐秘思绪似乎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依旧选择采取对话式正反打的剪辑,但我们能看到的仅有两张诧异的脸紧紧地互相打量着对方。
与此同时在双峰镇,疾病困扰着人们:贝弗利的丈夫忍受着癌症的痛苦、史蒂文的精神在毒品和经济的压力中逐渐崩溃、住在房车里的平凡修理工卖血养活自己、路屋酒吧里颓废的女性身上出现诡怪抓痕、奥黛丽似乎住在精神病院……
在《回归》开拍的同一年,凯瑟琳·科尔森(圆木女士)和大卫·鲍伊(FBI探员菲利普·杰弗里斯)也都在艰难地抵抗着癌症,后者没有选择回归,但他的印记显然不可磨灭,而我们怎么可能让《双峰》失去圆木女士?
于是制作组远程在西雅图召集了一只小团队,由林奇在洛杉矶透过视频通话远程执导(这个故事在如今的新冠时代尤其令人唏嘘),用两个简单的机位拍下了这位老朋友最后的几段独白。
圆木女士在四天后逝世,《双峰:回归》则悄然变成了一场伟大又令人怜惜的“急救行动”。
在剧中戏份仅有几秒的Marv Rosand——双R餐厅的厨师,在拍完他的部分四天后去世;马克·弗罗斯特的父亲沃伦在剧中饰演唐娜的父亲海沃德医生,在本季短暂客串后也离开人世;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饰演阿尔伯特的米盖尔·弗尔,他在剧集开播前离世,于是林奇与他在剧中的每一段对话都变得不一样,他们幽默的化学反应中渗入的不安气氛变得无法掩饰;而在剧集播完后,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又送走了哈利·戴恩·斯坦通——卡尔·罗德,本季中人道主义的光芒;布兰特·布里斯科——鹿角镇那位风趣的侦探,也曾出演《穆赫兰道》;饰演赌场老太的琳达·波特,和在剧中激励自己重病的弟弟哈利的弗兰克·杜鲁门警长——罗伯特·福斯特,也都于2019年去世。
好在,格蕾丝·扎布里斯基(79岁)还在,雷·怀斯还在(今年72岁,即便在他少得可怜的戏份中,那脸庞里的复杂依旧惊人!
),迈克尔·霍斯(霍克,68岁)还在,理查德·贝梅尔(本·霍恩,82岁,在这次拍摄中他依旧贡献了幕后花絮)还在,拉斯·坦布林(杰科比医生,85岁)也还在,等等,如果《双峰》还会以某种方式延续,林奇必然还会再次邀请这群老朋友们,他们的火种定会继续放光。
而对于诺玛——佩吉·利普顿的离世,更是让我们惋惜和感激《回归》中最美妙的时刻。
2014年,就在林奇宣布《双峰》回归的几个月前,他在推特上公开向网友询问一个电话号码——属于“大艾德”埃沃雷特·麦克吉尔的电话。
一个林奇式的故事在现实中展开,据麦克吉尔本人回忆,他当时已经退休多年,基本处于隐居状态,而林奇最终得到的电话号码事实上连到的是一个他已经不再居住的旧房子里,而当林奇打通那个电话时,麦克吉尔竟恰好正在那察看。
于是如缘分一样,我们得以看到诺玛/艾迪/奈丁这个横跨四分之一世纪的三角恋故事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谁又能想到,本季中双峰镇内的第一幕——杰科比医生的出场,会一直通向这个“唯一”的美好结局?
第十五集——本季最棒的一集之一就是以它开始,也是一切的终结的开始。
奈丁手里背着杰科比闪亮的金铲子,大步走向艾德,最终拥抱他,给予他自由,这是前所未有地坚定的一场戏。
而后在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于67年蒙特利尔音乐节现场版的《我已爱你太久》的激情旋律中,林奇和弗罗斯特给了艾德和诺玛这对久违的恋人他们的圆满谢幕,一切无须多言;而在诺玛与商人沃尔特的对峙中(这一迂回给了这场戏额外的悬念),林奇和弗罗斯特借着诺玛温柔的决心,高调宣布着独立万岁,影像万岁——奥蒂斯的歌断断续续,欲言又止地播放着,正如《双峰》的火光在它的历史中也是如此的忽暗忽明,但在这一时刻,弗罗斯特、林奇、诺玛、“大艾德”,他们在双R餐厅——这个美好的地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场急救行动将记载于电影史,这个林奇主义影像的博物馆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最有责任与爱的礼物。
/帕尔默的房子/THE PALMER HOUSE随后,夜幕降临,就连双R餐厅也灯火熄灭。
每当面临第十八集,我总是感到深深的词穷,我的眼睛的一部分永远被封印于2017年9月3日。
能说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男人,即便被时间抛弃,身份被剥夺,仍然坚信自己是“FBI”:在“朱迪”餐厅他这么宣布到;在Carrie Page的家门口他再次这么宣布;当被怀疑时,他掏出那枚徽章;最终,在曾属于帕尔默的房子前,他最后一次说出:“联邦调查局,我是特别探员戴尔·库珀。
” 但此时,面对门对面的陌生人(该栋房子的真实屋主),就连他也开始怀疑——凯尔用一个微妙的提问语气说出这句台词。
但我们又能指望他做什么别的呢?
凯尔·麦克拉克伦和雪莉·李,这两位《双峰》绝对的灵魂,在此时站在这个房子面前,一切注定如此,又不应如此:这个夜晚,在这空无一人的小路中央——三年后的我们将在现实中看到如此的景象。
在双峰警局难忘的重逢后,如果库珀选择和这群宝贵的人们在一起,而没有与戴安和戈登一起被那黑暗吞噬的话,又会发生什么?
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
但请让我现在给大家留下这些:
在2017年底与《电影手册》的采访中,林奇沉默片刻,然后说道:“世界风云变幻。
我不清楚您是否听说过Kali Yuga这个说法?
在印度教中,世界分为四个世纪:黄金世纪、白银世纪、青铜世纪、以及钢铁世纪。
我们正处于钢铁纪,这是四纪中最短的,持续四十三万两千年,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所有活在这个世纪的人都是理所应当的。
但这给了每个人精力去寻求启示,以此来破除灾祸,达到更高的境界…… 人类并非为痛苦而活,人的本性还是善的。
我们应当快乐,快乐的人们互相友好,解决问题也很容易。
但这是一场战斗,因为不少人,有时甚至不需要神,在反对这个理念。
”当《手册》问到为什么《双峰:回归》只暗示“黄金世纪”而不实际去抵达它,而是停留在帕尔默的房子前时,林奇会笑着说道:“如果我们如今活在’黄金世纪’,那我们就会看到《双峰》的终结…… 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到达,我们站在帕尔默家的房门前。
”
5 ) 恶灵拦截失败
黑cooper为了阻止真cooper回到人间,制作了一个胖cooper。
胖cooper完全是个赝品,没有cooper的灵魂。
从他热爱嫖娼就可以看出来。
但即便这样仍不保险,因为传送一旦开始黑cooper 和胖cooper各有50%概率被替换,主要就看谁能忍住不吐。。。。
所以黑cooper想出了第二套方案:用恶灵拦截真cooper!
黑cooper在南达科他州制造了一起凶杀案,把一个男人的身体和女人的头颅接在一起。
用来释放出一个恶灵,在真cooper离开black lodge并未到太空舱时进行拦截。
一旦拦截成功,真cooper到达到达太空舱前就被恶灵杀死,自然就不会有后面的替换了。
但由于某种原因,拦截失败。
某个科学家借富翁的钱架设了一个玻璃箱,想研究异次元空间。
结果歪打正着捕获了往来black lodge的东西。
根据影片,玻璃箱有两个作用,首先让真cooper和恶灵错开了,避免了被拦截。
但后到的恶灵把玻璃箱外的情侣杀死了。
注意玻璃箱内的恶灵形象同时具备男性和女性的特征。
和床上的女头男身尸体对应。
其次,玻璃箱延迟了真cooper到达太空舱的时间,以致真cooper到达时,传送门的编号是15,这是不对的,cooper该走的传送门编号是3(时间253的最后一位),15>3,说明cooper迟到了。
无眼女房间的时间明显是错的,不停倒带又倒不回去的感觉,暗示cooper已经错过了传送时间。
无眼女无奈只能爬上屋顶,拉下电闸重置了时间,自己也消失于太空。
cooper再次进入房间回到了正确时间,pulaski正在等他,当时针指向2点53分,传送开始。
此时黑cooper和胖cooper各有一半的概率被替换,黑cooper的拦截计划失败,只能赌了。
谁先吐谁就输了。
6 ) 关于《双峰:回归》的28块碎片
“注意听声音” “LISTEN TO THE SOUNDS”“注意听声音。
” 在我们听到这句台词后,戴尔·库珀的视线看向那个声音,最初静止对准留声机的摄影机也意识到了,也往前做出推进运动。
此时,留声机巨大的喇叭如同一个黑洞,里头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是的,不仅要听声音,还要“看”声音,这便是Fireman提示的意义。
拿这句话用来开启《双峰》的回归,既是给库珀的一条线索,更是给我们观众的提示。
库珀与Fireman的这一开场戏在剧集开播后便争议不断,关于其发生位置、时间线、以及对库珀这个人物的意义已经有了大量的猜测和讨论。
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标准答案。
我个人的猜测在这里并不重要,但在阅读了一些文章后,我能暂且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这场戏在剧集的时间线中是发生在第十八集,也就是库珀义无反顾地走上那条黑暗之路的之前或之后,Fireman的线索对于观众的意义,都要大于其对库珀的意义。
气象预报员 WEATHER REPORT虽然我们都了解成就《双峰》的并不都在于它的故事情节,但那些关于它的种种感官体验:梦幻般的小镇气氛、极佳的音乐、魅力十足又古怪的演员们等等,或许暂不应被文字化,因此我还是从叙事开始。
首先,需要指出一些反常的地方。
在回归季中,包括Fireman与库珀揭幕的第一场戏在内,总是有着大量如下的情节——线索被角色全盘托出,摄影机静静地看着,有时反打拍摄其他人的反应,总之,一段段长段的解释。
这时人们会怀疑:这还是我们熟悉的“视听艺术家”林奇吗?
为何突然一反常态地开始解释各种元素,这是一种惰性还是对电影语言的背离?
但重点在于,那些应该知道的,作者诚实地告诉我们。
面对这部续作我们更必须了解到,在2017年,《双峰》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度饱和的秘密盒子,经过了自1990年首播以来长久的催化,粉丝对剧中的每个元素都疯狂地着迷,十几年来的各种文字、批评、理论和猜测堆积如山。
因此,为了其自己的生存,林奇和弗罗斯特在这回归季中,必须时不时地必须分享给观众一些东西,这是其保持生命力的必需品,也是获得与观众平等关系的一次机会,更重要的是因此来从秘密中解放自己,来生成更多的秘密——成为林奇理想中的那个“生金蛋的鹅”。
催发着林奇的视听魔力的前提在于好奇心,而这便是所有的“提示”和“线索”所起到的作用,这些线索是足够清晰的指路灯,它并不夸张到能抵消所有的奥秘,而是恰如其分地站在了直线叙事与碎片化断裂之间的平衡点,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好奇心是无尽的:我们不仅有线索的武装,更拥有想象的空间。
《双峰》中的那些表达,其状态介于纯粹的信息传输和神秘兮兮的悄悄话之间。
不如用一个林奇式的爱好来做一个对比——气象预报。
从《内陆帝国》的年代开始的几年间,以及在这个新冠疫情时代的近期,林奇开始在自己的付费网站(这个网站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则是YouTube)上发布每日更新的气象报告:在每天一成不变的机位下,林奇用他标志性的口音开始播报当天洛杉矶的天气情况。
他的工作台背后是一扇刚好处于镜头外的窗户,也是林奇观察天气的窗口,于是他转向窗户,观察云层和天空的颜色。
我们看不到窗户外具体的景象,但是林奇的讲述让我们相信:晴朗的天空令他愉悦,他的咬字变得充满狂喜(“美-丽-的-蓝-天!
”),而就算阴雨时期,从他的语气中,你也能听到对于阳光的渴望。
如戈达尔语:“电影制造记忆,电视制造遗忘。
” 这不只是信息传递,这是电影(cinema)。
《双峰》里也有自己的气象预报员:在第二季的第一集中,神秘的天象观察员加兰少校向自己叛逆的儿子鲍比讲述自己的梦境,在梦中自己的儿子在未来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
这或许是第二季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而我们只是坐在RR餐厅那个再简单不过的小隔间中,用朴素的分镜头看着这两位风格迥异,完全不像父子的演员叙述着这个故事。
唐·戴维斯扮演的少校语气镇定,即便描述如此奇景时也是一股军人的严肃模样,但他的语气又不像是在做刻板的报告,而是真诚地分享;而扮演鲍比的达纳·艾什布鲁克,仍然保有着他情景剧化的夸张表情,如他在首播集中令人捧腹的咆哮——不像对面的戴维斯,这不是一位能把情感藏在内心的演员,他的任何触动与震惊全部写在脸上。
《双峰》中这样的交代情节,不也正是来自于这种气象预报的精神吗?
它充满爱地讲述着,分享着,剩下的则交由我们想象。
而那些我们不应该知道的,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弗兰克,你永远不会想知道那是什么” “我们不要提朱迪”)。
这听上去虽然没有这么“视觉”,但正因如此,当我们在真正接收到那些突如其来的影像时刻时,情感的能量才被放大到最强:如果第八集中爆炸性的实验影像仅仅是一系列的诡异画面,它并不会掌握其现在拥有的情感力量;如果米彻姆兄弟不就那个盒子里的樱桃派而鬼鬼祟祟地讨论一番,属于“道奇·琼斯”的伟大时刻也不会如此令人畅快;回到最初,假如Fireman在没有给出库珀这些看似随机的提示,那么当我们看到最后一集时也不会如此不安。
25年后,少校的预言成真,已经成为警员的鲍比对着劳拉经典画像而哭红了脸(第四集),将所有关于《双峰》的记忆唤起——这也是安哲罗·巴达拉曼提所作的劳拉·帕尔默主题音乐首次在回归季中响起。
注意听声音(和沉默)。
华丽归来的FBI探员库珀在第十七集中对一脸疑惑的弗兰克·杜鲁门(罗伯特·福斯特)警长说:“少校告诉我,(北方大饭店315房间的钥匙)会在杜鲁门警长手上。
” 演员戴维斯在2008年便去世,他在本季的回归也形式诡异,尸首分离但又无形地存在着,剧中也没有材料去佐证其种种预言;然而当库珀对警长说出此话时,没错,我们无条件地相信他,这位伟大的预报员。
电影学院 FILM SCHOOL距离《双峰》回归荧屏已经三年了,我进入电影学院也三年了。
于我而言,它便是21世纪的电影学院,长达18个小时的宝藏。
不仅仅是那些实验的、神鬼的、所谓“林奇主义”的时刻(刻意模仿那些时刻虽屡试不爽,但反而被证明是有害的),而是教给我们什么时候该拍什么,展示/不展示什么,也是关于节奏的大师课;它教你如何利用时间,教你如何催发好奇心(“2”的秘密),如何利用电影最简单的三种景别(换言之,什么是正反打?
),教你如何制造声音的能动,情感的能量,音乐的能量,教你如何活在当下并同时顾及过去与未来…… 同时,它也是一部喜剧杰作。
电视或电影 TV OR CINEMA“当我们选择把两部电视剧集排在我们十年十佳的最高位时,我们所做的,是在分辨那些还讲着电影的言语(懂得场面调度、剪辑、镜头、现实主义、表演等等……)的影片和剧集,和另外一批影视,那些只是给观众和’用户’提供‘内容’、‘宇宙’和‘信息”的叙事节目之间的关系。
” (斯蒂芬·德罗尔姆,《电影手册》第761期)火车 TRAIN第二集某处,夜晚,固定不动的摄影机描写了一列火车穿过马路的场景。
火车让我们想到电影的起源,想到卢米埃尔,想到悬念。
路杆放下的那一刻,悬念便生成,我们等待火车到来。
很快画外传来了火车的声音,我们期待着,声音越来越响,随后火车飞驰而过,悬念解除。
但接下来呢?
而对于刚刚开始进入剧集的我们,正在等待的则是库珀,或是奥黛丽·霍恩、雪莉·强森、杜鲁门警长、以及所有那些熟悉的脸庞和地点们,我们期待这列火车能将他们带到荧屏面前。
或许是我过度解读,但这一镜似乎早已默默道出所有这些等待背后的真谛。
空房子 EMPTY HOUSE据《电影手册》2017年底对林奇的采访,拉斯维加斯是马克·弗罗斯特的主意,他设想在原剧集25年后,戴尔·库珀会突然出现在这座赌城的某栋未经装修的空房子中(这一设想最终出现在第三集),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不少“空城”楼盘出现在这座扁平的沙漠之城中——一个诡异又讽刺的景象,道奇·琼斯的出现则额外加入了幽默感。
为什么是它?
这看似随机,但其实也是缘分。
如果说1990年的《双峰》是源于林奇和弗罗斯特两人对玛丽莲·梦露式神秘的女性悲剧的兴趣,那么弗罗斯特的这个新想法则又一次足够与林奇的频率相共振。
空房子的想法也足够有电影上的空间想象力,也足够令人充满好奇,正如第一集中如弗朗西斯·培根画作般的纽约玻璃箱,显然像是林奇的产物:两个看似空空如也的空间,像两块白色的画板一样,等待着画笔落下。
正是这种罕见的灵感共振,催生了《双峰》的回归,而作为一部从一开始就是两者合作产物的剧集,这种默契更是必需品。
那么在2010年代,《双峰》对于两位作者而言,契合点在哪里呢?
反怀旧 ANTI-NOSTALGIA如不少观众在回归季的开头两集便意识到的一样,这部新《双峰》似乎并不追求着把“故事”集中在双峰镇上展开,也不急着引进那些观众熟悉的人物,因此也被一些意见人士看作是一次借“双峰”之名而作的随意作品。
但正如这部剧集长达25年的“冬歇”一样,在如此长时间的停滞后,这部回归季也是关于回归这件事本身。
有人说回归季是一次对怀旧式的翻拍作品的抵抗,但我们或许根本不必上升到抵抗层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真的离《双峰》这么近吗?
最起码我们的作者不是,在看过《回归》后,我们很难再想象一种所谓“正常”的回归轨迹:双峰镇又发生一起命案,又出现一个杀手,FBI探员又一次到访。
在第一季的伟大开局和第二季初期激烈的超自然演进后,我们已经在原版剧集第二季的后半程,以及电影《双峰:与火同行》见过这样的“翻拍”戏码。
前者被证明是一次无用功的自我模仿,最终沉沦于无节制的廉价幽默,并活生生地让一众经典角色沦为跳梁小丑;而在后者中,独当一面的林奇则有意识地在第一幕将剧集的前传故事:特蕾莎·班克斯的谋杀案和鹿草镇(Deer Meadow)设计成为一个反《双峰》的实验,用极端反面的形象解构着定义着“双峰”魅力的各种元素:小餐馆,咖啡,FBI探员,被谋杀的神秘女孩,等等。
《双峰:回归》则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一部试图回归的剧集,在其故事的演进和重复,人物的出现和消失中,寻找着真正回归的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开始,一切元素都被分裂到了整个美国的各个角落。
纽约 NEW YORK CITY回归季的第一集中最吸引人的戏码莫过于纽约市的玻璃箱情节——如此神秘费解,又特别不“双峰”。
相信不少人都能清晰回忆到首播那天,在荧屏中看到纽约市三个大字随着曼哈顿的夜色突然出现时的震撼,这是绝无仅有的反应。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镜头本身甚至只是一个网上的库存素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魔力?
先让我们回看第一集的开场段落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首先林奇展示给我们熟悉的东西。
他在开场字幕前回顾了剧集试播集和第二季最终集中的段落:劳拉·帕尔默告诉库珀“25年后我会再见到你”;劳拉的死讯传遍双峰高中时的空镜头——那个一闪而过的在窗外尖叫着的女孩,只是这次林奇选择了慢放,像回放一段记忆——我们对剧集的记忆;开场的“TWIN PEAKS”字样伴着劳拉的经典画像出现,提醒我们这部剧集的核心自始至终都来自她。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是熟悉的。
然后,在全新的开场片段后(此时我们一睹红房间的新质感),在黑白影像中,一个优雅又有些许不稳定的镜头抬升,我们看到Fireman,对面坐着库珀。
虽然影像风格上,这个段落显然已和原版剧集划开了界限,此时此刻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熟悉的,毕竟谁不会想看到如此经典角色的回归呢?
紧接着这一段落的,是森林中的杰科比医生的回归。
为什么是他?
我们问自己。
况且,这不是你所熟悉的介绍回归人物的方式,镜头设计完全是疏离的,没有任何特写,没有标志性的音乐,我们甚至也不太明白他订购这些铲子的目的是如何。
整个段落在真实时间中以写实的美学展开,在远处静悄悄地观察着这个人物,结尾处摄影机在树根后面的注视更略有一种监控视角的意味。
不过就算如此,我们在双峰镇,我们在熟悉的森林里看到了熟悉的人物,即便没有故事展开,一切还是安抚人心的,于是我们放下了警惕。
然而……连接着杰科比医生的出场和纽约玻璃箱情节的,是淡入淡出的一段短暂的黑场,这种剪辑技巧在本季中被林奇和其剪辑师Duwayne Dunham反复利用,但又不同于原版剧集中被广告时间强制分离的黑屏。
黑场在此有一种仪式感,如剧场中的红幕帘,当幕布降下,我们陷入神秘中,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它再次升起时,舞台会被什么所覆盖。
也如林奇电影中常见的缓慢推镜头(以本作中的原子弹爆炸镜头为代表),摄影机聚焦在某处,随之缓慢地进入那个黑暗的角落,伴随着微风的声响。
此时观众问自己:摄影机穿过去之后,对岸的世界有什么?
有时迎接我们的是一整幅异境画卷(《橡皮头》),而有时,对岸看上去什么也没有,但一切却早已随之改变(《穆赫兰道》)。
这自然也是对连贯性的分镜和延续性思维的挑战,它确保我们时刻保持高度的思维集中——这不是一条笔直的路,它不断地跳跃,穿梭在非线性的时空中,它们是林奇作品中的虫洞(在本季《双峰》中还真的出现了“虫洞”),既是捷径,也是幽暗的小路。
红房间 THE RED ROOM红房间或许是最象征性的林奇舞台,它是由所有上述灵感凝结而成的综合体:一个有限的空间,但有着无限的可能。
25年前,库珀穿行于此,观众与他是同步的,没人知道下一个房间里会出现什么,因为每个房间的外观看上去一模一样。
这次重新见到它,带来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它实在太令人熟悉,但又远称不上亲切。
我们进入了一种介于知与不知的混沌状态:我们明显感受到其材质的变化,不再是通透的亮红色,而是厚重不透光的暗红色丝绒,数字摄影极强的锐度打碎了胶片的梦幻感,每个细节都变得清晰而实体,甚至16:9的高清电视画幅也令观感变得更加不安,似乎这个房间会按照画幅而发生空间变化(事实上这一点在《与火同行》中已经有显现)。
在《双峰》彻底打开其世界观之后,这早已不只是一个做梦的地方。
红房间的命名又有不少争议:跳舞的小人在第二季称它为“等候室”;大多数时候,我们称它为“守夜门/黑屋”(Black Lodge);但此时的我们,是不是只看到了地板上的深褐色条纹,而忽略了那浅黄色的另一半呢?
在《与火同行》的最后,正是在红房间中,劳拉和库珀笑中带泪地沐浴着天使的阳光(在《回归》之前这一直是“双峰”世界的终极影像),此时的它难道不又是“守日门/白屋”(White Lodge)?
同时,我们又不能咬定便利店上方的房间又是一个完全邪恶的地方,库珀的邪恶双生能在此囚禁戴安(化身为Naido);而当劳拉在《与火同行》中穿行于此时,她认识了自我,洞穿了未来;当真正归来的库珀和MIKE来到这里时,它又在执行着不同的使命,消失的探员菲利普·杰弗里斯(大卫·鲍伊)似乎也是一个中立者,只是时空中的指路人。
我也不认为Fireman在紫色海洋上的房子就是那所谓的“白屋”,Fireman能在这里生成神圣的劳拉灵魂,但当库珀在第三集坠落于某地,看到被囚的戴安时,他也看到了阳台上的那片海洋。
这两个地点是相互连接的吗?
或许命名和定义本身便是没有出路的,存在的变化莫测,正如霍克意味深长地解释的一样:“火的属性的变化,取决于使用者。
”观众 AUDIENCE没有什么剧集或者电影的评论中,有如此多的像《双峰》的这样涉及到“观众”这两个字。
归根结底,还是要返回它最初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属性。
作为一部公共台剧集,随拍随播的特点几乎让它不可能不被大众的需求所劫持,“谁杀了劳拉·帕尔默?
” 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阴霾,也揭露了电视骨子里只是无尽的信息交换的真相,而《双峰》正是电影派去征服这个“信息堡垒”的特派员。
这也是当时的结局:时任ABC电视网总裁的鲍勃·艾格迫使林奇和弗罗斯特揭露真凶的面目,如林奇所言:“这是宰杀一只下金蛋的鹅。
” 虽然事后证明,这场关于创作权力的争夺还是结下了意外果实:林奇揭露凶手的第14集(第二季第7集)成为了《双峰》中最经典单集之一,在其惊人的结尾段落中,林奇在写实恐怖的凶杀场面和朱莉·克鲁斯忧伤的致幻歌曲之间剪辑,创造了整个第二季的情感高潮;《与火同行》则让林奇在摆脱了解密的压力后重返劳拉这一核心人物,上映时的恶评不妨碍后人认清这是他最具人情味的电影,甚至开启了林奇电影风格的一个新阶段;当然,没有这一系列变故,也不可能有25年后《回归》的出现…… 但观众作为一个核心元素,时时刻刻让《双峰》充满了一层来自戏外的悬念,是一场每周更新的解密游戏。
《双峰:回归》没有选择重走原版剧集的路子,而是一部一气呵成,由林奇和弗罗斯特两位作者全权主使的作品,但它在首播时依旧完美复刻了25年中这种戏外的,来自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悬念。
在每一集播出后,观众们便开始猜测各种元素的意味,而除了不少无理取闹的理论以外,大多数时候观众们的细心观察会获得来自作者的回报。
一个绝佳的例子是当剧集首播时,人们纷纷议论到第四集中坏库珀在监狱里疑似说漏嘴的倒转词语“yrev”(“very”)是何意图,意外的是,林奇竟然在三周之后亲自以戈登的身份解密。
这也是为什么Showtime的周播模式更适合本剧,而不是像网飞的剧集一样一次性放送。
《回归》必须选择一条更具险境的路,并邀请观众一起上路,与两位作者一起踏上这“试图”回归双峰镇的路。
空间 SPACE在双峰镇外,林奇和弗罗斯特绽放着灵感之花:拉斯维加斯、南达科塔州、蒙大拿州、费城、纽约、新墨西哥、甚至还有阿根廷、巴黎、五角大楼…… 一连串的故事与幻想在这里发生,FBI探员们乘坐私人飞机在各地打探,“坏库珀”驾着他大男子气的黑色卡车随电流奔波,寻找着“坐标”,作为导演的林奇则借助剪辑之手穿行于各处,拼接起线索…… 而在双峰镇内,我们看到的一切似乎都进入了停滞状态:人物长时间被困在自己的空间里(本·霍恩、奥黛丽、无法理解手机的露西、永远呆在RR餐厅的诺玛),或者迷路在某地(杰瑞),或者经历各种痛苦的怪象(鲍比目睹枪支暴力,紧接着,伴着刺耳的鸣声,他看到一个呕吐的女孩;坏警察查德与酒鬼;无处不在的家暴和性侵犯;毒品继续统治着小镇地下经济;理查德·霍恩的恶行)。
帕尔默的家 PALMER’S HOME启动于2012年,林奇和弗罗斯特在这之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构建《回归》前两集的剧本,而在这两集的末尾,当从红房间坠落的库珀在与第一集的玻璃箱会合后,一个莫比乌斯环俨然形成。
似乎这也是整个剧集结构的缩影,一个不断叠加的循环,而这将在最后两集中完全达成。
这些循环的终点甚至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帕尔默家的房子,臭名昭著的708号。
在《与火同行》中,我们目睹了劳拉一家的痛与苦,25年后的今天,唯一还留守在这屋子里的,只剩下萨拉·帕尔默。
这奇妙的一场戏几乎是从未在林奇以往作品中出现过的情景——一个完全的私人时刻。
与此同时,静止的中景镜头,以及那些沉默的日常图景,这是林奇的“让娜·迪尔曼”式时刻,同样也是母亲的故事。
萨拉也曾是一位母亲,格蕾丝·扎布里斯基沉默的注视与她的尖叫一样令人不安。
我们这次见到萨拉时的这个画面,和《与火同行》中劳拉最后一次和萨拉道晚安时的构图几乎一模一样,唯独这次,我们看不到刚好被放在画框左侧外劳拉的经典肖像(这幅肖像在这一季依旧重要)。
她还没走出这个阴影,恐怕再也走不出了,一切都在这沉默,和这野兽的嘶吼中呈现。
但你可能会问,为何突然选择剪到这里?
我们前一秒看到的,是库珀飘落在太空中,不断加速,不知要去往何方;下一秒,是萨拉坐在幽暗的客厅里看野兽残杀。
林奇在本季中看似僵硬的转场有时看上去毫无逻辑,乍一眼确实令人费解,但联系一下剧集的发展:1. 萨拉显然已经被超自然力量占领(第十四集);2. 玻璃箱被证实是坏库珀的创造(第十集);3. 当坏库珀找到他想要的坐标后,Fireman一开始要将其传送至帕尔默宅(第十七集)。
于是,不妨这么假设林奇的思路:库珀被红房间设套后进入坏库珀设下的陷阱(玻璃箱),本该被传送到帕尔默家,直面最为邪恶的“朱迪”(此时她还需要暴力的电视节目获得“Garmonbozia”——《双峰》世界观中恶灵的能量,以奶油玉米作为视觉符号,象征着人世间的痛与苦)。
自然,林奇不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下子将所有人剧透,但这个小伏笔,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电影 CINEMA面对本作中变化多端的空间,观众或许更多会去纠结于一个力图模仿物理世界的时空逻辑,但终究我们正在观看的,是完全由电影意识创作出来的作品:如果失去叠化、倒放与蒙太奇,我们便不可能看到库珀如何进入红房间,并实时感受到其关于有限和无限之间交错的魅力。
在《回归》中,不少时间被花在角色单纯地在夜晚驾车,或是走过一个门廊,或是站立在某处等待,或是在闪烁的跳接中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中。
当库珀巨大的面孔叠印在皆大欢喜的警局团圆时,他那放慢的低沉声音说到:“我们活在梦里” (“We live inside a dream”),那么这个梦便只可能是电影,一个用纯粹来自电影的想法来承载的梦,这也超脱了《穆赫兰道》中,那个需要用冲向枕头的主观镜头来暗示梦的状态的林奇。
在《回归》中,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析将被纯粹电影的言语取代:Fireman的剧场里挂着一块电影银幕,而正是在这之中他接收到了关于世间黑暗的影像,而正是如此,他才得以向银幕的方向投放金色的灵魂(第八集),并操控角色在场景之间转换(第十七集);这解释了影片中的部分角色为何在叠影中消失/出现,或是有时直接从银幕中被抹去;第三集开场不断倒放/正放、快放/慢放中混乱的电影时间告知着我们危险的到来;在同一集中,从一个房间上升打开天窗,我们忽然发现自己身处在宇宙之中(正如玛雅·黛伦的作品《在陆地上》中,她利用对应动作的剪辑在无限多个空间中爬行奔跑);当剧集试图调和一些演员的离世时,林奇则从过往影片中直接抓取他们的影像,让他们以幽灵的方式继续存活下去…… 当戈登在2017年打开酒店的房门,劳拉在1992年向唐娜呼救的影像忽然叠印在门前(第十集),戈登的脸上写着不解;而在之后,他则在梦的重述中直接看到过去影片中被留存下来的自己(第十四集),于是才想起来杰弗里斯探员当年给他的提示。
这两个影像均取自《与火同行》——一个看似突兀的举动。
而当库珀抵达他自己的使命时,他正是降临在这部前传的结尾——新拍的影像和这部25年前拍摄的电影(转换为黑白)互相剪辑在一起,这部电影的存在允许他去做出改变历史的危险举动。
在本季最美的一组镜头中,坏库珀和一个“伐木人”缓缓步上通往便利店上方的楼梯,他们在电流声中闪烁地“消失”在叠影中,随即林奇选择叠化到一个幽暗森林中的推进镜头——一个完全印象派的动作,是这个镜头在精致的声音中缓缓前进,才将我们送到彼岸的超自然房间中;而当坏库珀走到房间的尽头打开门,音效突然变得自然化,他开门所见的看上去只是一个汽车酒店而已…… 因此,什么才是超自然?
或许它正隐藏在看似平常的空间里。
路屋酒吧 THE ROADHOUSE于是,路屋酒吧(Roadhouse)或许成为了本季中所有双峰镇内地点里最诡异的一个——一个早已被幽灵化的场所,它看似是停滞在90年代,是一个能拥抱“双峰”世界所有美好景象的地方。
这里是观众聚集的中转站,他们在舞池中伴随着当集的乐队摇摆,如电视机前的我们,不论我们如何接受或拒绝剧集中碎片般的情节,但永远有那么一个自我愿意无条件地把自己抛洒在这里,因为这是那个经典《双峰》的象征。
不论这里放的是朱莉·克鲁斯的梦幻歌谣,还是九寸钉的重金属,人们都想来到这里(整个回归季中最令人“气愤”的奥黛丽情节,完全围绕着“去路屋酒吧”这个引子展开),而在本季一半的单集中,我们也是在此和所有的故事短暂作别。
但与此同时,酒吧又时常拒绝简单的音乐诱惑,上演着最令人匪夷所思的随机戏码。
第二集结尾来自Chromatics令人无比畅快的《Shadow》开启了“双峰”世界这个新的传统:我们看到熟悉的角色,熟悉的音乐,但一切都以现代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部出色续作的象征。
随后放送的两集中也以同样的方式结尾,选用的歌曲也都比较轻松。
从此以后,我们在每一集中都会期待酒吧的出现,而有时它也带来伤感,因为经常这也意味着单集即将结束。
林奇和弗罗斯特一直以来都是培养观众这些小习惯的大师,但不必多说,他们也是最擅长去打破这些习惯的人,这也是本剧的慷慨和秘密,我们总是有所期待,而作者常常能满足这些期待,但一切并不总按照我们的期待而展开。
不过,在欣赏音乐和品味这些美好时刻的同时,或许不应该忘记路屋酒吧在剧中的拥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雷诺家族。
为了专门强调这点,两位作者甚至不惜请回了原版剧集中被杀的雅克·雷诺,让原演员Walter Olkewicz扮演一位雷诺家族的新成员来管理酒吧。
作为劳拉谋杀案中关键的涉案人之一,你一定记得弗罗斯特是如何在他导演的第一季第八集中对准他的嘴唇,拍摄他下流的言行。
在《回归》中,他的言行也没有好到哪去(参见第七集“臭名昭著”的扫地长镜头),是借他之口我们意识到,双峰的地下色情业仍然泛滥,林奇带回这个角色,他的秘密提醒我们,当年的劳拉是如何陷入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面中,并最终导致她的死亡。
因此路屋酒吧中的舒适注定也是短暂的,它也随着音乐风格的变化而无限地发生着变异。
因此可以非常大胆地说,在《回归》中,红房间的关于“有限/无限”的能动关系已经被延伸到了“双峰”世界的每个角落,甚至在库珀的视线中,它更能够被“随时”激活(红房间中,独臂人MIKE时常闪现在半透明的图层中,甚至能隔空传物)。
而路屋酒吧自从原版剧集以来便是超自然力量的光顾之处,当杀害劳拉的真凶被揭露时,也是路屋酒吧中的人们首先感应到悲剧的“再次发生”(It is happening again)。
这些离奇的现象在《回归》中以一种更为磨人的方式呈现,它体现在那些坐在小包厢里的随机人物,和一种疑似平行时空的存在中。
以第八集作为分割线,从第九集开始,这些随机的人物开始出现在路屋中,她们(她们几乎全部是女性)只会出现一次,随后便再也不被提及。
正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拉开红房间的帷幕时会遇到什么,路屋酒吧的这些随机人物,以及她们的故事——肥皂剧式的剧情、时不时的危险侵入、暴力无处不在、以及偶尔闪现的关于“主要”情节人物的线索等等,同样被给予一种这样的不安感。
就如第一次观看林奇回归执导的第二季季终集时的难以适应一样,面对这些和“主要”剧情毫无干系的人物,观众的第一反应是疑惑,甚至愤怒,抗议为何不把这珍贵的时间送给更“重要”的人物,这种疑惑情绪在第十二集开播,盼天盼地终于盼来奥黛丽,得到的却是如此冗长诡异的对话情节后达到顶峰。
但林奇和弗罗斯特在本季中对双峰镇这个空间的描绘,是没有任何所谓的“重要”或“不重要”可言的:除了双峰警局和路屋酒吧这两大常驻元素外,任何其它的场景或多或少都以看似随机的方式被抛出。
这种思路确实令人困惑,但另一方面,更可以说是一种平等。
在《回归》的世界中,即便其情节再令人感到随意,一旦一场戏被抛出,一种对节奏、语言、步伐、声音、分镜头严丝合缝的控制便体现出来,即便当它们只是两个看似无关人物的谈天说地,或是对一根电线杆、一只脚的注视,连一只咖啡杯的特写也充满光泽,每一场戏似乎都是一部独立成章的短片,被放置在《双峰》这个拥抱无限的容器里。
“你叫什么名字?
” “WHAT IS YOUR NAME?”每一集的最后,凯尔·麦克拉克伦的名字的出现揭示单集的结束,但库珀,不论是哪个形态,并没有大量出现在每个单集中,在某几集中,他的出场时间甚至不足一分钟!
只有最疯狂的电影人才敢作出如此的决定。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谈论库珀。
毕竟,这是一个无限的容器,因此不妨来窥测这些无限。
路屋酒吧的人物真的如此“随意”吗?
第十二集中奥黛丽和查理报菜名式的人名游戏令人头疼,是不是?
事实上林奇和弗罗斯特早有暗示,也是通向本剧最后终极时刻——第十八集的预防针。
再者,这种危险而暖昧的暗示还通向了另一条路,通向现实世界的路,这些“随机”的暗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故事将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你永远猜不到门后站着的会是什么。
倒回到第一集,此时的我们对《回归》的格局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但纽约市的玻璃箱,以及萨姆和崔西,不正是两个最经典的“随机”角色吗(同酒吧里的角色,这对年轻情侣在被“Experiment Model”残忍杀害后也很快从故事中消失)?
更明显地,就在某一个关键时刻之前,林奇和弗罗斯特选择加入这么一场令人好奇的滑稽情节。
是的,那个时候的我们才只是好奇,还未能通向困惑:一个叫Majorie Green的女人(Melissa Bailey曾在《穆赫兰道》里饰演了被倒霉枪手误伤的邻居,显然她又租错房了)带着吉娃娃狗(想及第二季里戈登·科尔的笑话)走在公寓过道上。
女人手臂上挂着的钥匙丁零当啷地发出着各种响声,而钥匙正是本场戏的关键。
滑稽的是,我们却花了接下来的五分钟时间和至少四个角色来找到它。
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恶作剧,在短短几分钟内,我们听到了一连串的名字:Barney、Ruth、Hank、Harvey、Chip…… 除了Hank,其他人都只在对话中出现(以及一个失去身体的死者),Chip还没有电话,而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将消失在之后的情节中。
虽然在之后的十几个小时中我们虽然不怎么再听到上述名字,但是一连串新名字陆陆续续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Red、Billy、Bing(Riley Lynch的角色,在双R餐厅门口问“谁见过Billy”)、Trick、Chuck、Clark、Angela、Tina、Carrie Page、Alice Tremond……;甚至还包括我们以为自己熟悉的,也以扭曲的面貌出现:萨拉·帕尔默、“朱迪”、杰弗里斯、理查德、琳达、甚至库珀自己…… 或许有一种关于名字的身份政治,这既是一种毒药又是一种幸事。
或许只有在《双峰》的世界中,几个简单的人名能产生如此效应,正是因为《双峰》作为一个成体系的世界拥有如此多的标志,但其作者又如此偏执地希望能偏离所有人的想象。
林奇和弗罗斯特完全可以不给这些角色赋予名字,将他们彻底随机化而帮观众消除这些疑惑,但她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名字,正也是她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证明。
林奇和弗罗斯特在整个十八集的旅程中一共安排了多达280个大大小小的角色,一共39位原版剧集的演员回归出演,两位作者从没有选择偏袒任何一方。
再拿第一集举例,纽约的萨姆和崔西两位新角色,以及鹿角镇的比尔·海思汀的情节占据了第一集几乎全部的时间,林奇最高度集中地呈现了这两条故事线,而流畅地穿插于其中的老角色——本、杰瑞、露西、圆木女士、杰科比医生……,虽然看上去戏份精简,但短短几分钟内,作者还给观众他们所熟悉的。
正如《手册》在评论中赞誉到:短短一瞥即可,只需要明白,他们还在这里。
对经典角色轻盈的处理,与新人物之间游刃有余地跳跃,似乎令人感觉剧集从未离开过,因此也无需盛大的迎接派对(只有库珀、戴安和劳拉们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这种礼遇,但这几个角色是无可置疑的中心,也和怀旧/反怀旧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相关),我们只需要直接进入他们生活的世界中。
因此,剧集的这种高度平等的关系确保了当我们进入到其最关键的最后阶段时,观众得以做好准备迎接任何可能性的到来,在将《双峰》的世界逐步扩展到它的最无限边缘的同时,并部分满足观众对于延续性和结局的渴望。
在《回归》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场戏中,库珀(或是“理查德”?
)问出了两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和“现在是几几年?
” 这是剧集中“我是谁我在哪?
”式的存在主义时刻。
完全不巧合地,这也是我们在整部剧的过程中常常问自己的问题。
除了那些四处抛洒的人名之外,全剧中发生的年份时间也是一个谜团——除了第八集中明确表示的1945和1956年(一方面越是清晰的科普和诠释,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更强大的未知),我们也无从得知剧集发生的年份,这种谜团则在最后一集达到顶峰。
关于时间的问题还会回来。
当库珀在第三集降临到紫色的屋子里,跳接生成的电流断裂感令我们头昏脑胀,此时库珀问:“这是哪里?
我们在哪里?
” 此时,观众与主角一起共享这些神秘,每个人都是侦探,林奇和弗罗斯特的慷慨之处在于对问题的不回避,因为一切观众在问的,作品也在问。
弗雷迪 FREDDIE让我们聚焦在某一个,可能看上去是整部《回归》中最“随机”的角色上面——弗雷迪,戴着绿色超能力手套的英国小伙。
弗雷迪这个角色的灵感来自林奇,而选角方面,在YouTube上专门发布多国口音模仿秀视频(最早发布于2010年,目前点击量超过3200万次)的Jake Wardle被林奇选中。
这个在第二集结尾操着“异国口音”短暂出场的神秘角色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在回归季所有这些新角色中,林奇对他似乎也是特别偏袒,甚至在剧终时期给予了他最“神圣”的使命之一。
弗雷迪与安迪 FREDDIE & ANDY正如林奇因其语言天赋而选中他一样,在剧中,处于“上帝视角”的Fireman也邀请了他——一个外人,这个故事在第十四集中由他向“老一辈”的詹姆士·赫利讲述(在这一集中,讲故事这个元素几乎被单独拎出来作为结构上的骨架,还有戈登讲述他的“莫妮卡·贝鲁奇”之梦,阿尔伯特给塔米探员讲述“蓝玫瑰”之起源,鲍比与父亲的故事,露西关于Bora Bora的故事则令戈登困惑)。
在同一集的前半部分中,Fireman还意外选中了另一个角色——警员安迪,并给他和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影像(和弗雷迪的纯讲述恰好相反)。
就如弗雷迪问Fireman:“为什么是我?
” Fireman回答到:“为什么不能是你?
” 弗雷迪的讲述紧接着警局四人在少校的“Jack Rabbit’s Palace”的冒险,不仅在电影形式上是一次优雅的形变,更也能被称为是对安迪的胜利作出的注解。
作为一名老角色,安迪在原版剧集中的“地位”显然在库珀、李兰·帕尔默、杜鲁门警长、本·霍恩、艾尔伯特这些“高级”角色面前显然是“不太高”的,因为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男子气概”。
在第二季的大多数时候,他被编剧们囚禁在自己、迪克和露西之间那条三角恋情景剧中,上演着荒唐的喜剧戏码,一直到最后真正的作者归来,他才勉强脱身,还给库珀指出了通往“黑屋”的关键线索。
但林奇与弗罗斯特一直对他钟爱有加,还在试播集的一开始就给予他难忘而滑稽的一幕:在劳拉的尸体面前,他突然痛哭起来,即便他与劳拉之间毫无交集——这是属于安迪的本真。
我们的两位作者从不怀疑这位看上去天真傻气的警员内在的智慧,这也就有了他在第十四集中的超越。
安迪的故事是一条直线(a straight story),但依旧通向伟大。
回过头来看安迪穿越的这一场戏,初看时确实倍感意外,但从林奇的调度中,答案已然明显:在看到了Naido之后,给予其他三位警员的都是简单的站立动作,而只有安迪蹲下身来紧紧握住Naido的手,眼睛望着天空中的漩涡。
腐败的警察查德在第十七集讽刺道:“这不是那个好警察安迪吗?
” 是的,犬儒的讥讽很快受到了来自弗雷迪的打击,查德从此消失。
弗雷迪和安迪的意外胜利是一种反“男子气概”的必然,正如在剧中“代表”了男子气概的坏库珀(第一集他首次亮相时,小屋里的欧蒂斯像称呼一个皮条客一样亲切地称呼他为“C先生”——贩卖职业杀手的皮条客),不偏不倚地拿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证明了自己男子气概的荒唐可笑。
弗雷迪与“鲍勃”(喜剧) FREDDIE & BOB (COMEDY)正如弗雷迪的手套中Fireman给予他的超人类力量,寄生于C先生体内的“鲍勃”也给予了他这样的能力,因此在第十三集前半部分令人捧腹的农场“大战”中,悬念几乎从一开始便不复存在,变为了一场严肃的闹剧。
我们看到一群灰头土脸的高大男人吹嘘到,自己的老大之所以是老大,是因为没人能在扳手腕上胜过他。
当这句话被说出时,想必观众们都已经了解到了事情的结局。
当然,最搞笑的是,正是因为如此,林奇才得以津津有味地拍摄这群男人,如观看一场早已分出胜负的拳击比赛一样,所有热火朝天的吼叫和长牙咧嘴的舞动都变成了纯粹的场面调度,伦佐面对C先生时绷紧肌肉面红耳赤的表情,也成了出色的喜剧表演,被消解的是暴力的竞技运动表面上自发的激情。
也难怪C先生最终的命运看上去是如此的反讽,先是被露西开了历史性的一枪(林奇和弗罗斯特一定等了一辈子这个时刻),随后“鲍勃”的黑色球体则被弗雷迪“呼呼”几下打碎。
一个对漫画式角色的漫画式处理。
弗雷迪与“鲍勃”的大战是被碎片化地剪辑起来的,林奇则亲自持单反相机拍摄那些晃动的镜头,四分五裂的调度,闪烁重叠的影像,一场“肉搏”变为了抽象艺术品。
这也是一次走钢丝式的危险尝试,配合起前一集中(好似从昆汀的《八恶人》片场过来的)詹妮弗·杰森·李和蒂姆·罗斯两位杀手的反高潮结局——被波兰会计(又一个突然冒出的角色)用半自动武器扫射身亡。
载着他们尸体的货车乌龟似地从目睹了此景的两位FBI探员身旁有气无力地爬过,懒懒地踏上了路旁的草地上。
杀手之死,“鲍勃”的结局,与弗雷迪的设计,如同第十六和十七集本身突然加速的节奏和爆炸性的剧情进展一样,对于剧集整体的基调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刻意破坏,但更像是林奇的一次警告。
观众事实上也有知晓,我们下意识地感觉到“鲍勃”的结局是错误的,这个原版剧集和《与火同行》中劳拉·帕尔默面前最恐怖的恶魔不应该如此,在“低劣”的数字特效底下草率收场,不是吗?
但此时,每一个人都是弗雷迪,对美好结局和“终极使命”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因而发生了短暂的失忆,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接受林奇慷慨给予的美好幻想(如同《穆赫兰道》,但这次远没有做一个梦这么简单),唯独不知道还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意外转折将会发生。
“朱迪” JUDY但或许“鲍勃”和C先生正应该这么“草草收尾”,因为他们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关键。
“鲍勃”导致了劳拉之死?
是也不是,《双峰》的骨子里是一个原生家庭中家庭创伤和不伦关系的故事,即便剧集再想把李兰·帕尔默和“鲍勃”划清界限,林奇在《与火同行》中也相当明确地展示了李兰作为父亲内心的缺口,他的紧绷与懦弱,最终演化为暴力。
“鲍勃”导致了库珀的分裂的堕落?
同样,是也不是,“C先生”或许只是库珀内心整体的一部分,那个热爱咖啡和树木清香的库珀也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在第二季结尾,也是那个“完整”的库珀主动接受了与恶魔的交易,而这样的错误他还会再犯一次。
戈登/林奇在第十七集开场滔滔不绝地开始解释“朱迪”,看似诱人,这事实上又是一次警告。
是什么驱使神秘的FBI总管突然开始暴露那些25年来他都不愿提及的秘密?
秘密背后更有秘密,戈登告诉我们“朱迪”是某种极端负面的力量(force),于是我们立刻开始在脑海的影像库中寻找某种实体(entity):是被黑暗物寄生的萨拉?
是那个杀死了纽约情侣的幻影?
是坏库珀的扑克牌和霍克地图上的诡异标志?
还是德克萨斯州奥德赛(Odessa, Texas)的“朱迪”餐馆?
它们或许都是“朱迪”,但也许又都不是,如果说第十八集证明了什么,它证明的正是对实体,对符号的误解:当你因为库珀在前作中被困在红房间里是最可怕的事情时,或许事情还没这么简单,毕竟红房间即便再如同一个深渊,它终究只是个“房间”,库珀还是能够在某一天“离开”;当库珀被四分五裂成三个形态时,不着急,他总有与自己面对面的一天;但如果他进入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既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呢?
如果这个领域正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呢?
林奇的频谱最终证明的是,任何的超现实场域,最终仍敌不过现实本身的讽刺:在无尽的夜路中驾驶,24小时营业的小餐馆灯光黑暗,或只是华盛顿州的某座平凡的房子。
正如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看了《蓝丝绒》后所定义的“林奇主义”:来自日常与平凡中背后的毛骨悚然。
当然,还是要有来自超现实的辩证来催发出这些秘密,正如库珀化身为“道奇·琼斯”时在案件报告里那些孩童般的画作所揭示的一样。
道奇·琼斯 DOUGIE JONES道奇·琼斯,一个多么平凡的名字:“道奇”像是那种人们用来称呼家养小狗的昵称,而“琼斯”则是大卫·鲍伊(本名大卫·罗伯特·琼斯)出道时选择抛弃的那个毫无特点的姓氏。
显然,他不拥有库珀所拥有的一切气质:衣品极差(即便林奇拍出了怪异的美感),头上显然戴着假发,大腹便便地躺在空房子简陋的床垫上。
这是库珀能成为的最差的样子,甚至更不济于坏库珀,后者最起码还有些大反派的魅力飘荡在其中,而道奇只能懒散地从脸上挤出几点笑容来,比任何的超现实效果都更加荒唐。
但就在我们还在好奇此君究竟为何物时,他便消失了(第三集),被真正的库珀取代,后者陷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就当我们觉得事情无法更糟时,我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曾经威武的《双峰》男一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还被困在了一个更糟的身份中:幸运7号(Lucky 7 Insurance)保险公司职位摇摇欲坠的推销员,被犯罪团伙追杀,被要挟在赌债中,还因为出轨被妻子嫌弃。
是的,我们得谈谈道奇,不是那个穿着丑陋的黄色西装的赌徒道奇,而是那个让库珀梦游了十三个小时的“道奇”。
《双峰:回归》无疑是一次全新的灵感碰撞,如果说这部作品是一个奇迹的话,“道奇·琼斯”的出现无疑象征着这奇迹所带来的无限狂喜,林奇说:“想要赶走黑暗,你要做的只是把灯打开。
” 特别探员戴尔·库珀化身“道奇”,成为一股闪烁的力量,作者用一种原始却激进的方式让我们重温让这位经典主角如何“特别”的独特美德。
这个沉默的孩童携带超自然场域的引力驱散着一切的虚伪与恶,他一眼一触便识破骗局,他浓缩并简化人们的语言;他恢复原生家庭的和睦,净化竞争对手的心灵,恶势力如磁铁的同极相斥般被道奇反弹回去。
然而这也是林奇最悲情的讽刺。
“道奇”是一个“不自然”的人工产物,被困在库珀的身体中,但依旧是个朱巴(tulpa),一个不现实的极善者形象,像一个无意中在考试里考满分的“笨学生”,他孤独地站在西部牛仔的雕像下(第五集末尾),他的运气和美好结局只属于电影——这注定是一个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是最纯粹的狂想曲。
如此热爱“道奇”,并不是要没有理由地热衷于孩童形象与乐观主义,而是因为林奇的调度从来不缺乏悬念,以至于林奇放慢一切的速度让你关心他:你感受到他新生的身躯慢吞吞地行走着,偶尔撞上一面玻璃墙;他触发赌场里的疯狂,一眼洞穿老虎机的假象,警铃声(模糊的所指:逮捕我还是奖励我?
)伴着硬币的叮当作响,与“HellooOoOOoOOooo!”形成了音乐;他几乎是雅克·塔蒂喜剧中的于洛先生,还把他自己身体中丧失的感官体验扩散到了一切与他交集的人当中,他笨拙的肢体运动竟神奇地让对方感受到情感,你从未能够如此细细观看凯尔·麦克拉克伦这位林奇老朋友的脸,他的沉默和僵硬中反射的迷失与记忆。
他看到腐败的保险员工安东尼脑门星空一般洒在西装上的头皮屑,后者泪眼婆娑地决定改邪归正(戈登在第四集中高喊 “Fix Your Hearts or Die”);纳奥米·沃茨饰演的Janey-E再一次感受到了快乐,并喷发出内心对金钱与官僚世界的愤怒(第六集中一人单挑两个赌本的她不能更加强悍,弗罗斯特的政治宣言时刻,正如杰科比化身“扩音医生”(Dr.Amp));看上去像是刻板的黑帮老大角色米彻姆兄弟们一遇上他,则陷入了狂欢之中,排起队跳起舞;他的老板布什纳尔——一位前拳击手则发现了超验的魅力。
在第六集中,当他看到“道奇”的信手涂鸦,困惑并怒斥道:“你要如何指望我怎么去理解它?
”而“道奇”呢,则只是默默重复着:“去…… 理解它。
”(“Make… sense of it.”)于是,他便立刻看得一清二楚。
当第十一集中,赌场的流浪老太(琳达·波特)穿着一身华丽的服饰和儿子伴着巴达拉曼提的新曲子突然从背景里现身,对着她眼中的“头奖先生”(Mr. Jackpot)无尽道谢时,我们内心猛然一震。
观众也中了头奖:这是本作中最出乎意料的情感时刻,堪比任何弗兰克·卡普拉电影的结尾。
三千万美元的支票和一块樱桃派才让道奇逃脱了杀生之祸,而价值两万八美元的两个老虎机头奖,却让这个看似不值一提的龙套蜕变为了整个《回归》里最令人感动的角色——实话实说,没人指望,也不会有人在乎她是否归来。
但林奇和弗罗斯特让她回来了,并不只为了让我们看一个贫穷的老太是如何一夜暴富,她中的钱远远少于“道奇”,但对她而言这都足够,两位作者要我们看她如何从第三集中厌世贫瘠的赌徒形象中摆脱,绽放出惊人的尊严、慷慨和饱满的人格魅力:她看着这位失语的“特别”探员,如看着自己亲生的骨肉一般。
她的华服和房子、她的狗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名下的肆意消费,林奇只为了证明这一点点小小的推动,即便残存在拉斯维加斯本质的荒诞与虚伪中,仍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在之后不会再见到她(该演员在剧集播出后也去世),但是这影像、音乐和表演,足够让我们相信。
相信道奇 BELIEVE IN DOUGIE梦醒时分,库珀告诉MIKE让他用“种子”重造一个新的道奇,后者在第十八集开场实现了库珀给Janey-E和Sonny Jim的诺言,敲响了那个红色大门,这个新的家庭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一集中唯一的幸福时刻,从此之后事情将朝着一往无前的黑暗驾驶,脱离前两集中架设的怀旧美景与理想主义,返回到我们被困的现实中。
林奇和弗罗斯特在这里提醒我们“道奇”本质的假象,但最起码,“道奇”的伟大还能在这部作品里被反复重温,作为一种理想他并非一无是处。
是的,在库珀慢慢陷入到“理查德”这个混沌状态中,绝望地试图改变过去而进入新的深渊时,我们反而开始怀念“道奇”,那个令人烦躁的,笨拙的,“浪费”观众时间的“道奇”。
寄语 THE MESSAGE“霍克,电流声鸣响着。
你在山间与河流中听见它。
你看到它在大海与星空中舞蹈,在月亮四周闪光,但在如今,这闪光渐渐淡没。
在那黑暗中还能残存什么?
杜鲁门兄弟两人都是真正的人。
他们是你的兄弟。
而其他人,那些优秀的也与你站在一起。
如今,这个循环即将化为一个圆。
仔细听,仔细看,那时间与空间的梦。
像一条河流,一切都涌动出来了。
那些存在与不存在。
霍克,劳拉就是那唯一。
” (圆木女士,第十集)便携录音机 TAPE RECORDER第二集,在南达科他州,预料到事情异常的“坏库珀”在汽车旅店包围了毫无防备的Darya,我们立刻感知到,她完全暴露在危险甚至死亡当中。
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在林奇作品中持续被审视,从《蓝丝绒》里的丹尼斯·霍珀与伊萨贝拉·罗西里尼,到《我心狂野》里的威廉·达福和劳拉·邓恩;而《双峰》更是其中的代表。
而这一场长达8分钟的审问剩下的,仅有Darya绝望的无用功和坏库珀绝对的冷漠,而观众都已知道结局。
与此同时,林奇通过动作和台词的叠加强化了这种残忍——Darya反复试图逃脱,多达4次,而每一次她都被坏库珀拉回,毫无招架之力。
巨大的人物特写让观看这场戏更加充满不适,形成一种视点中立的可怕的理性。
麦克拉克伦在这一段中的演绎堪称极致,我们无法把这个人物和“真正”的库珀联系起来;然而触发两人冲突的,却是一段库珀通过便携录音机监听到的电话,而没有什么,能比库珀在此时掏出一个黑色的便携录音机更为恐怖的事情了。
任何一位看过《双峰》的观众都会明白便携录音机对于库珀这个人物的意义——尚未登场的戴安。
曾经,我们总是看着库珀通过一支录音机向戴安报告情况,或在前往双峰镇的车上、或在双峰镇警局、或在北方大饭店的315房间,等等。
这个在当年从没真正亮相的角色,可谓是库珀的最佳拍档。
现在,坏库珀携带一支类似的便携录音机登场,虽然并没有喊出标志性的“戴安……”开场白,但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暗示:如果他将这位最亲密无间的搭档也转变成了被邪恶附身的傀儡,会发生什么?
作为观众的一员,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戴安……” “DIANE……”尽管直到最后,我们才意识到戴安在《回归》的第三集便已某种形式出场,但当劳拉·邓恩饰演的她在第六集中的现身,仍然是一次又惊喜又令人警惕的举动。
库珀在整个《双峰》世界中的第一句台词,喊的便是她的名字,因此从一开始,即便作为一个无形的角色,戴安便与劳拉·帕尔默一样令人熟知。
跟布满全剧的超自然力量一样,无论是死去的劳拉,还是始终只出现在库珀台词中的戴安,这些无形的角色或者力量一直如此笼罩着剧集中的世界,更作为被动的客体而被代表着。
因而当戴安的真身出现时,被代表的客体忽然间成为自主的整体,正如我们直到《与火同行》才亲眼目睹真正的劳拉,强烈反差所带来的未知气息反而加剧了角色的神秘,她全部的真相更是一个混乱的迷宫。
果然,最终(第十六集)我们发现,这个银发的戴安并非是真正的戴安,而是如原装的道奇一样,被坏库珀控制的傀儡,正如他的黑色录音机所暗示的,只不过坏库珀并不像我们心爱的探员一样对着自己的录音机持之以恒,这个恶灵附身的杀手只是将戴安当作随手激活的工具,正如他那些用后即焚的一次性手机一样。
戴安 DIANE林奇和弗罗斯特以极具挑拨性的方式逐渐揭开这个版本的戴安的面纱。
她粗俗的语言首先打破我们对这个秘书形象的刻板认知(“去你*的,戈登”),随后在第七集与坏库珀在监狱里关键的对话中,我们意识到,有一件糟糕的往事彻底地异化了这对搭档之间的关系,猜测是容易的,但我们却更愿意不把它当作是真相,即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那唯一的可能性——在这消失的25年间,坏库珀如曾经的李兰/“鲍勃”一样性侵了戴安(这个故事在第十六集终于以最为痛苦的方式述出,邓恩最好的表演之一)。
这一《双峰》骨子里的黑暗历史如1990年底的揭露一样令人恐惧,令人无法直视。
在劳拉的谋杀案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的当年,人们纷纷对“谁是真凶”这个问题下起赌注,但丝毫不出意料的是,李兰·帕尔默排在这个榜单的末位——没人会相信,或者愿意相信这个悲痛的父亲正是这个家庭恐怖的源泉,就如扮演他的雷·怀斯也不愿意相信,即便他在剧中已经动手谋杀了雅克·雷诺(习惯了影视剧复仇戏码的我们会说这情有可原),头发也一夜之间变成了“鲍勃”的银色,并像红房间的小人一样跳起了舞。
“今年是几几年?
” 答案:2017年(《回归》播出的年份),川普登台美国的第一年,#MeToo运动的第一年。
人之本性决定了我们不愿意听到最坏的消息,正如当在路屋酒吧里突然侵犯邻座年轻女性的男子被发现名为理查德·霍恩时,我们即便猜到他必然是坏库珀在25年前在医院强奸昏迷的奥黛丽导致的恶种,我们也宁可不去相信,并在脑内试图延迟真相揭露的时间。
讽刺的是,我们又是如此热衷于知道真相,热衷于让事情画上句号,这样我们便能忘却并继续前进。
戴安的例子则更为复杂,因为我们意识到她或许除了是坏库珀的受害者以外,还是他计划中的帮凶。
第九集时,当戴安第一次收到来自坏库珀的神秘短信时,“戴安是反派”这一可能性便被慢慢建立起来,但我并不愿意相信,在潜意识中拒绝接受:“戴安不可能这么做!
” 遗憾的是,在《双峰》世界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于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现出来:她目睹了比尔被爆了头,偷窥阿尔伯特得到的坐标,并给坏库珀泄露情报。
但正如剧集结尾的“真”戴安,这个“假”戴安看上去也是如此真实,因为她即便作为一个人工复制品,她与原装道奇的性质完全不同,这也归功于林奇与弗罗斯特出色的模糊化处理,和邓恩立体的表演。
在许多时刻,她展现出来的极度压抑的情感,怎能让我们相信她背后受控的程序?
这个戴安虽然是“假”,但又是一种异于一切的人格分裂,她的冷漠不代表她就不能时不时召唤出那个远在天边的“真”戴安。
“库……”,当在第十六集中收到来自坏库珀的终极使命时,银发戴安在震惊之余对着控制自己的手机轻轻呼唤到。
这显然是真正的戴安,用她自己的声音在呼唤真正的库珀(刚刚从“道奇”的梦中醒来),而不是那个“去你*的”戴安。
劳拉·邓恩在最终的讲述中奋力与恶魔般的往事抵抗,在这无形的较量中,是那个真正的戴安在揭发坏库珀的恶行,也是那个真正的戴安在给困在酒店里的FBI探员里指明方向(他们已经有连续五集之间呆在这个酒店里),也是她在用力呼喊着:“我不是我!
我不是我!
”(“I am not me! I am not me!”)她必须选择拔枪射向自己的老朋友,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坏库珀的控制中摆脱出来。
这与《与火同行》最后劳拉面对恶魔时必须做的牺牲显然是异曲同工的,于是在被销毁之前,她才得以非常自豪地,端坐在红房间里对着它(以及她的施暴者)爆最后一次粗口。
这便是银发戴安伟大的矛盾。
时间 TIME露西如是说:“这得看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是说,有时候我甚至都没时间去想任何事情。
有一次安迪甚至觉得时钟都停了,结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完全忘了时间,感觉像是无限。
”这句话发生在第十集,而当我们纵观整部剧集的节奏,我们会发现从第八集的疯狂之后,林奇和弗罗斯特在接下来的五集(即第九到第十三集)中,似乎把频率放慢了不少,与此同时带来的,便是露西所说的时间上的混乱和运动的停滞了,尤其是在双峰镇内的情节中尤为明显。
在第九集中,鲍比、霍克和警长一行来到鲍比母亲的家中,后者给了他们少校留下的最后秘密,提示他们要在两天后去“Jack Rabbit’s Palace”,然而这一行动却一直要等到(首播时现实时间的五周后的)第十四集才发生,而在这之后剧集也将开始快速地前行,往终结而去。
连时间顺序甚至也出现了断层:鲍比在第十三集时前往RR餐厅吃饭碰上了艾德·赫利,此时他却说是在今天“发现了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
时间漩涡的可能性不断地被暗示:萨拉的电视上播着一段反复循环的拳击比赛录像(第十三集),路屋酒吧之前的客座乐队再次出现(Au Revoir Simone和Chromatics),杰科比医生的广播被完整重复,甚至还有像是被刻意设计的穿帮和不连贯(关于这个可以写一整篇文章,但由于实在无法区分出故意作为的不连贯和制作疏忽导致的错误,还是暂不深究)。
更巧合的是,如果仔细观看影片中给出的线索,我们正是在第九集才第一次知道剧集本身发生的时间:9月29日!
而在之前的八集中,除了闪回中给出的两个年份和库珀离开红房间的“253”,时间和日期都是被刻意地模糊的。
回想原作中清晰的时间:《与火同行》把时间线限定在劳拉被害前的一周时间内;前两季剧集则严格按照一集一天的速率前进,连库珀出场时的第一句台词就是播报时间和空间——“11点30分,2月24日,开车进入双峰镇……”,FBI探员把自己经过的地点一个个地细数了出来。
从一个本来能清晰地知道自己所处时空的世界中,我们是如何一直来到现在这个处境中?
在《回归》中,这种流畅的运行是被禁止的,似乎是剧集在以电影的线性运作时,把物理的时间抛在了脑后一样。
而这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因为在数不胜数的时刻中,时间固执地以平缓匀速的方式度过着,在那段时间中,好似我们被永远困在现实的速度中,作品让我们感受到每分每秒。
此时,这表面现实的速度好似也是某种超现实:杰科比医生慢条自理地对着他的铲子喷绘(第三集),林奇拍摄下这平凡的工作,如同他自己在工作室里完成一件家具或画作;第七集我们看着一个人扫地整整两分钟;下一集,一个同样两分钟长的镜头往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缓缓冲去;邪恶的爬行生物缓缓从一颗蛋中孵出;女孩睡着在床上,静止的镜头看着她悄悄被寄生;戈登、塔米和戴安在警局门口静静地站着抽烟(第九集);法国女人滑稽地起身离开,戈登看得津津有味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了疲惫的阿尔伯特颇为无奈地看着他们的游戏(第十二集);“道奇”和Janey-E在第六集开场长近15分钟的对峙,最终他默默地在桌上作画。
这种时间上的变奏也恰如其分代表了了库珀、坏库珀与“道奇”这三个“分身”的时空观。
当我们反复被MIKE提醒“这是未来?
还是过去?
”时,我们以“完整”库珀的视角思考,而这时,几个库珀的时空观之间存在分裂:谨守于其英雄使命的“特别探员库珀”执迷于过去,一头扎进那笼罩着他25年人生的囚禁,那些他无法拯救的人,那唯一一个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坏库珀的眼中只有未来,一个他已经预见的毁灭结局,因此他制定重重计划和阻碍来阻止结局的发生,永远行驶在慢慢长夜中,沿途中都是暴力和痛苦,这是他的悲剧;而无须多言,“道奇”是一个完全处在当下的人,他不知道过去也不会想未来,他是库珀内心中那个能每天享受咖啡和樱桃派的人格,是那个在原剧集中说出“每天给自己一件礼物”的库珀。
混乱源自什么?
在《双峰:回归》中,时间混乱的到来正是源自对过去和未来的执迷,这一对本身在“现实”时间中本就“不存在”的矛盾体是两个诡怪的极端,正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不可调和造就了我们体验的种种困惑和恐惧。
急救行动 EMERGENCY RESCUE《双峰:回归》面对的,终究还有它自己的时间,它必须回归于2015-2017年,正如劳拉在曾经预言的一样。
前所未有地,一部重启的续集选择在当下,在现实中演员的衰老中寻找那些迷失的时间。
我们总是对原版剧集中的俊男靓女津津乐道——演员之爱是强大的。
在《回归》开始拍摄的2015年,林奇69岁,弗罗斯特61岁,凯尔·麦克拉克伦56岁。
属于劳拉·帕尔默——雪莉·李的时间也没有冻结在1989年的那张老照片,或是她冰冷尸体的面孔中,林奇选择让她以如今的年龄出现在红房间里,在数字摄影机的高清注视下,每位回归的演员上岁月的皱纹清晰可见——劳拉、MIKE和库珀脸上来自岁月的痕迹无不让我们记住,这25年过得有多长,即便是在如红房间这样看上去无视时空法则的超验领域里,也是如此。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衰老和死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双峰》的主题之一。
“你认得出我吗?
”,劳拉瞪大着眼睛提醒库珀,似乎同时也在质问观众,我们也将信将疑,像库珀一样回答道:“你是劳拉·帕尔默?
” 对于林奇而言,这之间包含的隐秘思绪似乎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依旧选择采取对话式正反打的剪辑,但我们能看到的仅有两张诧异的脸紧紧地互相打量着对方。
与此同时在双峰镇,疾病困扰着人们:贝弗利的丈夫忍受着癌症的痛苦、史蒂文的精神在毒品和经济的压力中逐渐崩溃、住在房车里的平凡修理工卖血养活自己、路屋酒吧里颓废的女性身上出现诡怪抓痕、奥黛丽似乎住在精神病院…… 在《回归》开拍的同一年,凯瑟琳·科尔森(圆木女士)和大卫·鲍伊(FBI探员菲利普·杰弗里斯)也都在艰难地抵抗着癌症,后者没有选择回归,但他的印记显然不可磨灭,而我们怎么可能让《双峰》失去圆木女士?
于是制作组远程在西雅图召集了一只小团队,由林奇在洛杉矶透过视频通话远程执导(这个故事在如今的新冠时代尤其令人唏嘘),用两个简单的机位拍下了这位老朋友最后的几段独白。
圆木女士在四天后逝世,《双峰:回归》则悄然变成了一场伟大又令人怜惜的“急救行动”。
在剧中戏份仅有几秒的Marv Rosand——双R餐厅的厨师,在拍完他的部分四天后去世;马克·弗罗斯特的父亲沃伦在剧中饰演唐娜的父亲海沃德医生,在本季短暂客串后也离开人世;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饰演阿尔伯特的米盖尔·弗尔,他在剧集开播前离世,于是林奇与他在剧中的每一段对话都变得不一样,他们幽默的化学反应中渗入的不安气氛变得无法掩饰;而在剧集播完后,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又送走了哈利·戴恩·斯坦通——卡尔·罗德,本季中人道主义的光芒;布兰特·布里斯科——鹿角镇那位风趣的侦探,也曾出演《穆赫兰道》;饰演赌场老太的琳达·波特,和在剧中激励自己重病的弟弟哈利的弗兰克·杜鲁门警长——罗伯特·福斯特,也都于2019年去世。
好在,格蕾丝·扎布里斯基(79岁)还在,雷·怀斯还在(今年72岁,即便在他少得可怜的戏份中,那脸庞里的复杂依旧惊人!
),迈克尔·霍斯(霍克,68岁)还在,理查德·贝梅尔(本·霍恩,82岁,在这次拍摄中他依旧贡献了幕后花絮)还在,拉斯·坦布林(杰科比医生,85岁)也还在,等等,如果《双峰》还会以某种方式延续,林奇必然还会再次邀请这群老朋友们,他们的火种定会继续放光。
而对于诺玛——佩吉·利普顿的离世,更是让我们惋惜和感激《回归》中最美妙的时刻。
2014年,就在林奇宣布《双峰》回归的几个月前,他在推特上公开向网友询问一个电话号码——属于“大艾德”埃沃雷特·麦克吉尔的电话。
一个林奇式的故事在现实中展开,据麦克吉尔本人回忆,他当时已经退休多年,基本处于隐居状态,而林奇最终得到的电话号码事实上连到的是一个他已经不再居住的旧房子里,而当林奇打通那个电话时,麦克吉尔竟恰好正在那察看。
于是如缘分一样,我们得以看到诺玛/艾迪/奈丁这个横跨四分之一世纪的三角恋故事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谁又能想到,本季中双峰镇内的第一幕——杰科比医生的出场,会一直通向这个“唯一”的美好结局?
第十五集——本季最棒的一集之一就是以它开始,也是一切的终结的开始。
奈丁手里背着杰科比闪亮的金铲子,大步走向艾德,最终拥抱他,给予他自由,这是前所未有地坚定的一场戏。
而后在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于67年蒙特利尔音乐节现场版的《我已爱你太久》的激情旋律中,林奇和弗罗斯特给了艾德和诺玛这对久违的恋人他们的圆满谢幕,一切无须多言;而在诺玛与商人沃尔特的对峙中(这一迂回给了这场戏额外的悬念),林奇和弗罗斯特借着诺玛温柔的决心,高调宣布着独立万岁,影像万岁——奥蒂斯的歌断断续续,欲言又止地播放着,正如《双峰》的火光在它的历史中也是如此的忽暗忽明,但在这一时刻,弗罗斯特、林奇、诺玛、“大艾德”,他们在双R餐厅——这个美好的地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场急救行动将记载于电影史,这个林奇主义影像的博物馆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最有责任与爱的礼物。
帕尔默的房子 THE PALMER HOUSE随后,夜幕降临,就连双R餐厅也灯火熄灭。
每当面临第十八集,我总是感到深深的词穷,我的眼睛的一部分永远被封印于2017年9月3日。
能说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男人,即便被时间抛弃,身份被剥夺,仍然坚信自己是“FBI”:在“朱迪”餐厅他这么宣布到;在Carrie Page的家门口他再次这么宣布;当被怀疑时,他掏出那枚徽章;最终,在曾属于帕尔默的房子前,他最后一次说出:“联邦调查局,我是特别探员戴尔·库珀。
” 但此时,面对门对面的陌生人(该栋房子的真实屋主),就连他也开始怀疑——凯尔用一个微妙的提问语气说出这句台词。
但我们又能指望他做什么别的呢?
凯尔·麦克拉克伦和雪莉·李,这两位《双峰》绝对的灵魂,在此时站在这个房子面前,一切注定如此,又不应如此:这个夜晚,在这空无一人的小路中央——三年后的我们将在现实中看到如此的景象。
在双峰警局难忘的重逢后,如果库珀选择和这群宝贵的人们在一起,而没有与戴安和戈登一起被那黑暗吞噬的话,又会发生什么?
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
但请让我现在给大家留下这些:在2017年底与《电影手册》的采访中,林奇沉默片刻,然后说道:“世界风云变幻。
我不清楚您是否听说过Kali Yuga这个说法?
在印度教中,世界分为四个世纪:黄金世纪、白银世纪、青铜世纪、以及钢铁世纪。
我们正处于钢铁纪,这是四纪中最短的,持续四十三万两千年,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所有活在这个世纪的人都是理所应当的。
但这给了每个人精力去寻求启示,以此来破除灾祸,达到更高的境界…… 人类并非为痛苦而活,人的本性还是善的。
我们应当快乐,快乐的人们互相友好,解决问题也很容易。
但这是一场战斗,因为不少人,有时甚至不需要神,在反对这个理念。
”当《手册》问到为什么《双峰:回归》只暗示“黄金世纪”而不实际去抵达它,而是停留在帕尔默的房子前时,林奇会笑着说道:“如果我们如今活在’黄金世纪’,那我们就会看到《双峰》的终结…… 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到达,我们站在帕尔默家的房门前。
”FIN+ 他者之梦 DREAMS OF THE OTHER在重看这集《双峰》时,德勒兹的话突然回荡在耳边:“他者的梦是非常危险的。
梦有种可怖的意志,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他者之梦的受害者…… 要小心他者的梦,因为当你一旦深陷他人的梦,你的一切将无可挽回!
” 当然,在《双峰》中,我们有莫妮卡·贝鲁奇说:“谁是梦者?
” 这不是在说这部剧集完全依靠梦的解析,或者整部剧都是一个角色的梦境之类的异端邪说。
倒不如说“梦”在此象征了一种分离的状态,它将诸角色的生命体验所分离,并最终导致这些生命的体验以最为暴力和刺耳的方式冲撞在一起。
请看《双峰:回归》的第十一集,一上来就是这种冲撞:孩子们遭遇了草丛中匍匐爬行,满脸是血的女人。
正如《蓝丝绒》中杰弗里遭遇那只耳朵——镜头伸展进去,进入秘密之中,这便是他人的梦的入侵。
我们不会再一次看到这些孩子,但另一些孩子取代了他们:雪莉(上一代《双峰》中的年轻人们虽已老去,但观众不会这么想,最起码会极力阻止这种想法的渗透)、雪莉的女儿贝琪。
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地发生着,林奇在这里用的居然是第三集中那个惊人的逃逸片段的音乐,两者之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但入侵正是这样发生的,剧烈又不自然。
像一个十足的特技演员,雪莉紧紧抓住自己的车,无力地试图阻止女儿的复仇计划。
贝琪朝着空空如也的公寓里开枪,镜头如疾风般飞行着,揪出了躲在角落的史蒂文(贝琪年轻的瘾君子丈夫)和格斯滕(唯一回归的海华德姊妹,曾经的钢琴手)。
“就算是最美好的女孩,也有着惊人的吞没力…” (德勒兹)就这样,那些他人的梦开始四处蔓延,记忆和影像开始疯狂入侵我们的大脑。
为什么是格斯滕?
为什么是她出现了?
唐娜呢?
为什么她现在是这样了?
为什么是她跟史蒂文?
十万个为什么。
在这一季中,林奇和弗罗斯特近乎过分地强调了角色之间的分离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的相遇都变得如一道闪电,在那些不得体的剪辑中爆发。
紧接着,一连串的入侵。
夜晚的双R餐厅里,布里吉斯一家三口:鲍比、雪莉和贝琪,在剧中唯一一次团聚,但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眼中他者的梦。
不然该如何解释雪莉的新男友,贩毒的魔术师Red毫无逻辑地出现?
前一秒还在为女儿愁眉苦脸的雪莉一下子脸上可开了花,但这对另外两个人则如同天打雷劈一般: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梦。
这就是那所谓的吞没力。
紧接着,一声枪响——双R餐厅中从来未曾遭遇如此的攻击。
鲍比立刻恢复了警察的身份走到门口,映入眼帘的只可能又是一群他者的梦,堵车与蜂鸣的交接,那个如丧尸般升起的女孩都是鲍比的梦魔。
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入侵,德勒兹所说的情形早已原模原样地现身了:在《双峰:与火同行》中,戴尔·库珀踏入到了劳拉·帕尔默的梦境中。
25年后,弗兰克·杜鲁门看着劳拉遗失的日记碎片,疑惑地说:“劳拉从没见过库珀,他是在她死后才来的。
” 但这正是我们的问题与困境的根源了,一切都不是对等的,偏偏是一个死者将一位骑士标记,让他走进了自己的梦中,留下那些满是碎片的线索,那些无法拼凑还原的时间,那些无法被感受的生命体验。
劳拉和其他所有人分隔于生与死之间,但这却让劳拉像还活着一样,这只是因为劳拉的梦入侵了所有人。
“那些做梦者的梦,真正关系到的实则是那些并没有在做梦的人。
”(德勒兹) 这种时空与生死,梦境与现实的分离,也是库珀的疯狂的开始,虽然他要等到很多很多年后才能意识到这点。
“要小心他者的梦。
” 为什么说《与火同行》既是一个起源又是一个终点?
只能是说它找回了他者之梦入侵的真正开始。
劳拉·帕尔默不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个在虚构中获得实体的形态,因此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梦。
大卫·林奇走进了劳拉·帕尔默的梦。
到了25年后,则是戴尔·库珀的梦。
如果把《双峰》-《与火同行》-《回归》的三大体系看作成梦中套梦,那么它们中每一个都循序渐进地向着前者的梦冲撞着,它一去不复返。
7 ) 《双峰》入门指南
特别不爱看电视剧,经常是看一两集就弃了。
原因是大部分电视剧信息量太少,看的时候只想快进和跳很多集。
后来干脆看都不看了,热门电视剧直接随便看个recap,二十分钟搞定,省时省力。
《双峰》作为普通剧集,非常离谱。
没有剧情主线,没有核心冲突,没有戏剧张力。
总而言之,没人会愿意变吃饭边看它。
从情节上来说,前两季就说明白了一件大概一句话就能讲明白的案件,然后从这件事展开了三十多集。
所以,我觉得这压根不是电视剧,应该是一部电影或者是那种非常琐碎绵长的小说。
有这样的心理预期之后,观看的过程就流畅很多了。
大卫林奇本人也说过(大概这意思):“电影更像是音乐,需要茫茫多的铺垫,对比和特定的排列……这不可能一步到位”。
我无比赞同这句话,也受益于这个想法。
《双峰》给我的观后体验,会远远大于任何一部电视剧(未来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可以参见后面我对第三季的评价)。
至此,我也想记录和梳理一下自己的观看体验。
双峰 第一季 (1990)9.01990 / 美国 / 剧情 科幻 悬疑 惊悚 犯罪 / 大卫·林奇 杜维因·邓纳姆 蒂娜·拉思伯恩 蒂姆·亨特 莱丝莉·琳卡·格拉特 凯莱布·德夏奈尔 马克·弗罗斯特 / 凯尔·麦克拉克伦 梅晨·阿米克后知后觉得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第一季一共八集,我恍惚以为在读红楼梦前八十回。
因为第二季中间莫名其妙的十几集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想法。
除了大卫林奇,Mark Frost 功不可没。
他创造的那种阴谋论主题,加上各种符号标志的诡异设定,配上大卫林奇诡异的叙事风格,简直不能再搭了。
双峰 第二季 (1990)8.31990 / 美国 / 剧情 科幻 悬疑 惊悚 犯罪 / 大卫·林奇 莱丝莉·琳卡·格拉特 托德·霍兰德 格雷姆·克利福德 凯莱布·德夏奈尔 蒂姆·亨特 蒂娜·拉思伯恩 杜维因·邓纳姆 乌利·埃德尔 黛安·基顿 詹姆斯·弗雷 乔纳森·桑格 史蒂芬·吉伦哈尔 / 凯尔·麦克拉克伦 迈克尔·昂吉恩毁誉参半的一季,也是给第三季拍摄埋了种子。
除了被迫圆上了第一季的案件,最后抛出一个长达25年悬而未决的疑问。
但是,哪怕中间一半导演大卫林奇中间跑路了,世界观立在那里还是保留了神秘的内核。
而且顺着Mark的补充小说,愣是毫不掉价得把整个剧情给圆上了。
双峰:与火同行 (1992)8.01992 / 法国 美国 / 剧情 悬疑 惊悚 恐怖 / 大卫·林奇 / 雪莉·李 雷·怀斯以电影为分界线,大卫林奇彻底接管了整个双峰后续。
除了罗列一些必要的提示线索,电影基本就是翻拍了一遍第一季核心剧情,而且个人比较喜欢的喜剧元素和诡异设定也被导演剔除了。
双峰 第三季 (2017)8.92017 / 美国 / 剧情 悬疑 犯罪 / 大卫·林奇 / 凯尔·麦克拉克伦 雪莉·李我更愿意叫它,《双峰:回归 大卫林奇导演剪辑版》。
基本上原有的设定被全部打乱了,据说这也是导演有意为之。
如果还拿红楼梦举不恰当的例子,感觉就是真正的后四十回续书重见天日了。
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割裂感,让整部剧都充满了黯然神伤的气息。
这完全是为爱发电的一部,所以我也认为这种电视剧在2017年就是没死透的活化石,而且林奇本人确实也把这种想法灌输进去。
至此,推荐在看完之余,再去鉴赏播主twin perfect四个半小时的解读。
我不太想评价整部作品是否一开始就埋了meta元素的线索,因为艺术作品都会无意间被投射上现实世界的残影。
我也赞成,如果有这么一部作品经得起这么解读与分析,无论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都不那么重要了。
有些东西,且看且珍惜吧。
8 ) 关于Dougie一角所包涵隐喻的些许思考和分析
看了一圈评论,似乎还没有专门讨论Dougie的。
不知为何,刷完本季已经好一阵了,这个有点诡异的角色却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干脆一写为快吧。
当然,这里想重点说的是作为Cooper分身的Dougie,而非Dougie本人。
本季一共有18集,分身之后一直处在没有¨wake up¨状态,被人们当作Dougie的Cooper其实贯穿了整季,一直到最后两集才变回“好”Cooper,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虽然每一集里乍看之下他最大的作用之一似乎都是给比较沉闷和慢节奏的剧情带来笑点 ——不会自己走路,需要别人推下车还不知关车门,甚至连基本的与人交流都难以胜任,只会重复其他人口中说出的几个词,等等—— 而之所以能达到这些让人觉得搞笑的效果,其实是因为Dougie的种种举动都是和我们习惯了的生活常态严重不符的,换句话说,简直是宛如自闭症患者一般(这里没有歧视的意思,我有和自闭症患者亲身生活的经历,只是觉得种种行为比较相似)。
其实普通自闭症患者如果没有帮助的话,是很难在社会上独立自主生存下来的。
所以刚开始看到Cooper/Dougie变成这样,我的心也不禁揪了起来,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如何继续生存,特别是在一个环境如此险恶的世界当中。
然而神奇的是,Dougie自从出场一直到最后,都是有如神助,一路披襟斩棘,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活得风生水起。
这也让我不禁去思考,这个Dougie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想要表达什么。
而我能想到的答案是,其实Dougie是一个镜像般的反射性隐喻。
接下来会具体解释。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一直追溯到Cooper分裂的那一刻。
其实如果严格按照道德的眼光去扫描每一个人,得出来的结果或许会是,大多数人都是一团善与恶的混合物。
我们的种种行为调和在一起得出的颜色,是模糊不清的灰色。
而Cooper在分裂成一“善”一“恶”两个分身之后,其实他所蕴含的这两个道德维度,就不再模糊不清,而是化身成了两个清晰可见的极端,分别由本季里的”坏”Cooper和“好”Cooper来代表。
“好”Cooper诞生之后又被投放到了一个普通的家庭之中,变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Dougie”。
之所以说Dougie是一面镜子,是因为他和其他人互动的过程,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你来我往的“二人互动”过程,而是这些人和他们自身互动的过程。
这在Dougie的说话方式中有很清楚的体现:不管别人对他说什么,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去重复对方说的话里的某个短句,或者某个词。
就像对着一面镜子说话一般,人们说出来的东西经过反射,又再一次呈现在了他们面前。
而讽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他人收到他们自身反射之后的反应。
可以看到,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和Dougie说过话的人,除了他妻子Janey以外(即使Janey最初也没有立刻反应,过了至少一天才送他去医院检查),都没有对他的这种奇怪行为表现出丝毫的关切。
虽然觉得Dougie有点怪异,但是仍然选择假装没看到,而去延续自己的工作职责或者继续追求他们想要达到的自身利益目的,把这种自说自话的“对话”进行下去,得到的结论也自然是他们自己想要的结论。
也许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Dougie可以安然度过整季而毫发未损,为什么明明一眼就能看出Dougie哪里不太对劲,人们却无一例外地选择睁眼瞎,装作一切正常似的对待他。
因为在和他的这种反射性互动之中,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是自己想看的结果,得到的都是自己想要的答案,Dougie所做的只是呈现并满足了他人自身的欲望。
而这些欲望归根结底,也基本上都是和金钱有关的,包括Janey掌管了家庭财务之后的意气风发,赌场老奶奶经过他的指点以后重返贵族生活。
而进一步体现Dougie身上这种镜面效果的,是他的一系列“超能力”:能看出哪一台老虎机会中大奖,能看出公司同事在文件之中的造假,能看出谁说了谎,谁心怀歹意,要对他造成伤害。
总结一下,其实Dougie的超能力,就是可以看破虚无的表面,直达反映善恶的本质。
而让我比较欣慰的是,在这些本质被揭露之后,人们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老板耐着性子看懂了他的批注,对他大加赏识;造假的同事公开承认悔过,而且良心发现,向他本来打算投毒杀死的Dougie道歉。
因此,实际上这个怪异又充满笑点的Dougie角色,也包含着“镜子”这个影视和文学中的常见隐喻,让我们通过对他的观察,也顺便一览了剧中各种其他角色内心需求与欲望的反射。
9 ) 金色木屋 · 评论翻译|觉醒:斯德潘·德罗姆论《双峰:回归》
原标题:Le réveil作者:Stéphane Delorme原文出自《电影手册》第737期(2017年10月)。
翻译 / 船夫 校对 / desi 全文约5400字 阅读需要14分钟!! 文章可能涉及对《双峰》系列及林奇其它作品的重大剧透 !!“You have to wake up.”:“你得醒来。
”尽管第三季标题是“回归”(The Return),主题却是觉醒。
“库珀究竟何时醒来?
”成为了自始至终萦绕的疑问。
林奇把悬念拉得很长,直至我们对道奇的喜爱不亚于库珀。
但道奇周围所有人(家庭、同事、朋友)都没意识到他的反应如提线木偶,还会在心里补全他的行为以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什么时候会醒来呢?
全然的自动化(automatisation)。
人们不再能看见彼此。
道奇那种毛绒玩具般的柔和藏不住对家庭和工作的尖锐讽刺:一个木偶便可应付一切。
然而剧中的所有人物都陷入了自己的小泡泡,他们经历了信号干扰(戈登·科尔)、旅程(杰瑞·霍恩、史蒂芬),甚至,完全否认其他人的存在:理查德打自己的祖母,贝基把自己的母亲推出车外。
但有时,只需一点刺激便能把人唤醒:当贝琪在双R餐厅与诺玛四目相对,她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对母亲做了什么,向她道歉。
只需轻轻触碰(道奇按摩想杀他的人的后颈),剧中人物就如同起死回生般重焕生机。
Twin Peaks: The Return- 道奇按摩想杀他的人的后颈“觉醒”早已是《沙丘》(Dune, 1984)的主题,在那部电影中,凯尔·麦克拉克伦(Kyle McLachlan)饰演的主角必须明白自己是天选之子,并在自己身边组建一支军队(“沉睡者必须觉醒[The sleeper must awaken]”)。
而在这里,戴绿色手套的非凡英国人弗雷迪,心地善良的安迪和露西,霍克和他的印第安血统,都为这支小小队伍倾其所有。
林奇一如既往地直白。
木头女士敢于在临死之际说出一个双关语:“杜鲁门兄弟都是真正的男人。
(The Truman brothers are both true men.)”真正的男人要对抗叛徒、腐败分子、暴力分子、大男子主义者:可以像但丁的《地狱篇》那样列一长串恶人的名单。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迷人的,他们都被嘲弄,被当成小孩、恶霸、白痴——林奇在这方面无可指摘。
他那始终如一的幽默感让他可以挥舞着一把铁锹和一只园艺手套去对抗邪恶。
那(金色的)铲子是用来把人们从烂摊子里铲出来的(杰科比医生是导演的荒诞替身),获得解放的纳丁英勇地扛着它走进城里。
那“拳击手套”则是用来击打泡泡里的鲍勃的,它像是从布什内尔·穆林斯的海报上摘下,戴在那位小小英国人的手上脱不下来,对抗着莎拉客厅里循环播放的拳赛中拳手们那原地踏步的无能。
至于道奇,他迈着自己的缓慢步伐开展调查,效果却和库珀一样好,他在周遭传播善意,解决了侵蚀至警局内部的腐败问题。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人的行为和机器人别无二致的自动化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白痴(就像塔可夫斯基在《潜行者》[Stalker, 1979]中所塑造的,是他那个时代——那个陷入物质主义困境的时代——的白痴)。
Twin Peaks: The Return- 扛着金铲子的纳丁为什么尽管如此,一切还是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奥黛丽醒过来了,但她在哪儿?
库珀苏醒了两次:一次是在医院(那句自豪的“我是FBI”),他短暂地回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然后通过警长办公室中的叠化,他从另一个世界觉醒,前往寻找劳拉。
“我的灵魂很孤独”,特雷蒙德夫人的孙子重复道,林奇的儿子在第二季里出演了这个角色。
库珀就是这样一个永不停歇地觉醒并踏上征途的人。
如果库珀真的如其所自称的那样——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那么他必须一直走下去。
“我是FBI”这句话,意味着他化身为了这个机构的座右铭:“忠诚(Fidelity)、勇敢(Bravery)、正直(Integrity)”。
库珀是一种理念。
他怎么可能穿着伐木工的衬衫在双峰镇定居呢?
他永远不会停止脚步。
Twin Peaks Season 2- 特雷蒙德夫人的孙子,奥斯汀·林奇饰演
Twin Peaks: The Return- 不断觉醒的库珀 重复与层叠(télescope) 剧集开篇,那对在玻璃立方前消磨时间的年轻情侣,其实是我们的倒影。
他们的存在警告我们:我们这些观众,才是《双峰》的真正对象,而我们将被彻底摧毁。
被摧毁,还是被唤醒?
那句“你必须醒来”,正是对我们发出的召唤。
Twin Peaks: The Return- 玻璃房前的年轻情侣但该如何唤醒我们?
如何触动我们?
怎么做才能进入我们内心深处?
必须剥离表面的观看惯性。
林奇从一些简单或典型的情境中,构建出了巨大的块体。
他不断深挖、下潜,直至触及到令人难以承受之处:正因这种反复的坚持,才让它终于进入了我们的内心。
他有两个最具亲缘性的敌人,一是说教,那会将一切都简化为教训,二是淫秽,那压倒一切的感官刺激会摧毁本应传达的信息。
如何表现一对情侣(奥黛丽和查理)之间的疏离和停滞?
通过一场陷入僵持的对话,以及字面意义上无法离开房间的困境。
林奇拍摄的是操控(l’emprise),其它一切都并不重要。
也许他自己比我们更不知道奥黛丽究竟身处何方,而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解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剧不仅仅是慢,它将重复推向极致,直至令人抓狂。
Twin Peaks: The Return- 被困在房子里的奥黛丽这种坚持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那可以称之为层叠嵌套(télescopique)的场面调度。
最颠狂的场景当属雪莉、鲍比和女儿的家庭重聚。
原本温馨的家庭场景,却因毒贩雷德的介入而走向梦魇——雪莉为了他而冷落了自己的家人,接着是双R餐厅被枪击,然后鲍比走到外面,发现开枪的是一个小孩,这个穿着迷彩服的小鬼在他父亲注视下摆着架子,接下来是那个女人没完没了地尖叫、按喇叭,正当我们以为紧张混乱已达顶峰,副驾驶座上竟冒出一个面容惨白的、呕吐不止的身影,一个恶心得让人难以直视的恶鬼。
这恶鬼正是我们的恐惧的具象化,如同望远镜般层层深入,直达我们最深的恶梦。
一如那位母亲和即将出车祸的孩子之间的游戏,空间被一点点拉深,直到事故发生。
最深处,永远是那难以承受之物——一个死去或病弱的孩子,一声痛苦的啼哭。
Twin Peaks: The Return- 鲍比处理双R餐厅外的混乱另一次层层展开,另一次尖叫:路屋酒吧里,两个男人粗暴地拎起一名坐在桌前的女孩,像放下物品一样把她放到地上。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但并没有:她四肢着地,爬行在冷漠的人群间,情感忽然爆发,她尖叫——第十五集结束。
这个角色构成了双重象征:象征着对女性的暴力,也象征着弱者被强者所碾压。
我们已习以为常的情况,必须重新变得难以承受:这就是我们需要理解的。
这个场景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e)建铸了姿态的失调与空间的混乱。
但林奇摒弃了现实主义与幻想、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的界限。
这依然是现实主义,但被推到了极致——对现实主义的深化。
从日常出发,释放想象的力量。
Twin Peaks: The Return- 女孩尖叫了起来一个场景(本剧重新赋予“场景”这一概念以全部的重量)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观众的影响力。
它让我们沉入深处,如同一次冥想练习一般(“喝饱水,向下沉”)。
这就产生了催眠般的效果:第六集里,当道奇涂涂画画时,我们陷入了恍惚,仿佛被某种非常强大的ASMR所操控。
第十八集末尾:还有什么比夜晚行车这事更庸常?
然而,我们却觉得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乘客沉默无声,夜色的包裹让行车变得超验,被剥离于世界和时间之外。
这种感觉,我们曾在现实中体验过,但从未在电影中感受到,而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了。
一位伟大的电影作者创造情感,但也复原情感。
唤醒我们,就是要让我们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给予时间。
在我们以为故事结束之时,一切才真正开始。
正是在那个瞬间,我们被击中,终于睁开了双眼。
Twin Peaks: The Return- 道奇的涂鸦 神秘与解读 网上关于这部剧的各种解读叫人读起来兴味盎然,有无数的线索等着拼接。
但这些解读往往忽略了,《双峰》真正独特之处在于潜入场景深处所带来的身体性感受。
而且,它们也忽略了全剧层叠嵌套的结构,这让林奇可以随时从任何地方切入。
这部剧由不可预测的分支与短路构成。
连林奇自己都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并刻意保持无知。
这正是灵感产生的前提。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与碎片化或整体性的解读保持距离,不被其左右。
每周追剧的观影体验本身,就促成了一种碎片化的记忆,把某些时刻孤立出来,如一座座孤岛。
事后尝试串联所有情节、将片尾解读为团圆结局的尝试,虽然很有趣(比如“劳拉的尖叫让房子跳闸,从而杀死邪恶实体朱迪”——正如开头所预示的:“她现在在我们的房子里”),但与我们的真实观看体验背道而驰。
而这种情感的逻辑,才是唯一真正值得相信的。
体验不应该被解释所抹杀,即使我们难以用语言准确表达内心所感。
Twin Peaks: The Return- 房子跳闸林奇喜欢漂向那未知的领域,他日后可以重新回到那些领域,从那里重新出发。
看看他是怎么将《双峰:与火同行》(Twin Peaks: Fire Walk with Me, 1992)中的一切素材都化为可用之物,他是如何回收朱迪这个线索(鲍伊[David Bowie]的角色仅仅说了句:“我不会谈论朱迪”),又或,他是如何在劳拉的惊恐目光后安插一个库珀的反打镜头。
通过图像的不断深化,谜题一次次被挖掘得更深。
Twin Peaks: Fire Walk with Me- 菲利普·杰弗瑞斯,大卫·鲍伊饰演同样,“她就是那个人(She is the one)”这句话出自在第一季试播集的“木头女士开场白”,它原本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剧集从一个人(one)出发,讲述许多人(many)的故事,劳拉则是“那个人”(the one)。
而到了第三季,这句话的含义变得近乎是基督式的。
林奇回溯那些遗留的线索,收集散落的白色石子。
这部剧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结局,因为没有什么会终结,而都仍然有待挖掘。
Twin Peaks: The Return- 木头女士的开场白许多狂热的解读往往忽略了另一种逻辑——演员的逻辑。
林奇绝不会闭门造车,他的电影是与他身边的人共同完成的。
是凯尔·麦克拉克伦主动找到他,希望能重启《双峰》。
劳拉·邓恩(Laura Dern)曾经透露,几年前她曾和娜奥米·沃茨(Naomi Watts)一起去林奇家敲门,希望能再次合作,而林奇告诉她们自己已经在酝酿新计划。
两位女演员站在他门前的场景,这是否启发了他在剧中安排两人饰演同父异母的姐妹?
两人各分一个库珀:一个给戴安,另一个给珍妮-E。
“现实生活”对虚构的闯入在这部剧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这有时形成了一场告别——我们无法忘记凯瑟琳·E·考尔森(Catherine Coulson)的脸和声音。
还有其它细节也显露出了此种现实的闯入,比如副导演斯科特·卡梅伦(Scott Cameron)扔出一个瓶子,打断了奥黛丽的舞蹈,就好像他是在打断电影本身的拍摄一样。
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真实感,才最让人难以忘怀。
Twin Peaks: The Return- 戴安,劳拉·邓恩饰演
Twin Peaks: The Return- 珍妮-E,娜奥米·沃茨饰演剧中最动人的搭档是戈登与塔米:导演对这位自己一手提携的女演员充满爱意,尽管影评人对其冷嘲热讽,她还是令人难以忘怀。
在阿尔伯特向她揭露“蓝玫瑰计划”的那场戏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是他披露的信息,还是女演员连连发出的难以置信的惊叹,仿佛一切对她来说都太过沉重,而这些惊叹赋予了这场戏一种催眠般的节奏?
林奇总是和观众做游戏,但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睁开双眼,看见了他身边的人们。
Twin Peaks: The Return- 塔米、艾尔伯特、戈登当戈登像个孩子一样,沉醉于那位法国女子用眼神、嘴唇和腿部做出的夸张的离场动作时,真的需要去解读其中隐藏的“暗号”吗?
这些动作与表情完全出于表演的纯粹欢愉,角色、场景、对白的设计都是围绕着演员而创造的。
当理查德·张伯伦(Richard Chamberlain)在两扇门之间短暂客串时,戈登/林奇向他喊道:“玛莎怎么样?
”,这正是他现实中的妻子玛莎·克鲁姆(Martha Crum)的名字。
而莎拉·帕尔默(Sarah Palmer)的戏份之所以如此重要,可能也只是因为林奇深深欣赏格蕾丝·扎布里斯基(Grace Zabriskie),以至于想看她多演一点。
林奇召集了所有的老朋友,构建起一座宏伟的“友谊之塔”。
在这部剧里,一切都在崩塌,爱情、家庭、企业……唯独友谊未曾破碎,唯独朋友间的合作不曾改变。
这种充满情感的联盟得到了保护。
Twin Peaks: The Return- 戈登沉醉于法国女子的眼神 驱魔 问题总是一样:如果目标是觉醒、而解法唯有爱,为何还要经历如此的黑暗?
在他的书《钓大鱼》(Catching the Big Fish)中,他回答道:“因为作品反映它们所处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黑暗的,作品便同样黑暗,尽管作品是在对抗着黑暗。
《双峰》中浮现出了另一个答案:在林奇的作品中第一次,世界本身成为了对象,不再只是要拯救劳拉,还要拯救世界。
整部剧宛如一场巨型的驱魔仪式。
如果说这部作品如此特别,那么是因为其中那些符号交织,那些重复,那些层层展开,以及那些表演性的信仰,更多让我们想起魔法艺术(œuvres magiques)或原始艺术(art brut)。
层叠嵌套的、而非有机统一的作品,让元素相互孕育催生,叫人想起艺术家阿洛伊斯·科巴兹(Aloise Corbaz)画作的“太阳漂掠”(ricochets solaires)风格。
翻开布鲁诺·德沙姆(Bruno Decharme)和芭芭拉·萨法洛娃(Barbara Safarova)编选的精彩画册《原始艺术》(Art Brut),你会看见许多与林奇作品直接相通的图式。
不妨逐一摘取章节标题:“起初,是混沌 / 太阳漂掠 / 神奇之物 / 语言游戏 / 心灵图鉴 / 血与怒 / 肉体晕眩 / 天空史诗 / 拯救世界”。
阿洛伊斯·科巴兹的画作,出自展览“太阳漂掠”是的,拯救世界。
芭芭拉·萨法洛娃写道:“这些作品大多体现了一种修复和拯救的意图。
”怎能不叫人想到穿越到过去、拯救劳拉的库珀呢?
桑德拉·亚当·库哈雷(Sandra Adam-Couralet)将原始艺术类比为想要“理解错误发生在何处”的萨满。
”她补充道:“创作,就是用作品去定位我们内在的或集体的失衡,并将之限制于作品之内:将疾病框限在字里行间,将邪恶囚禁在勾画的线条当中,在那些逃脱我们控制的黑暗事物中危险地跋涉,从而洽谈出世界的平衡。
……艺术的能动力量,只有在我们如同信仰神圣之物般信仰它时,才会真正发生。
于是这就关乎去相信创造性虚构的情感力量。
所以,想象力的注入绝非逃避,或单纯的脱身之道,而是真正关乎世界存续的必要过程。
”
阿洛伊斯·科巴兹的画作,出自展览“太阳漂掠”《双峰》并非原始艺术,林奇也不是疯子,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文字竟然引起了如此深刻的共鸣:“在那些逃脱我们控制的黑暗事物中危险地跋涉,从而洽谈出世界的平衡。
”这便是《双峰》的驱魔仪式,将邪恶囚禁于笼中。
艺术的能动力量,在于进入我们的生活,唤醒我们。
我们能通过“蔓延扩散”(contagion)来拯救世界吗?
《双峰》既是我们世界的一面镜子,也呈现出了一个“对立世界”(contre-monde)。
Twin Peaks: The Return- 劳拉和库珀在《电影手册》第700期(2014)里,为“心头萦绕的情感”的主题供稿时,林奇选择了罗伯特·本顿(Robert Benton)《我心深处》(Places in the Heart, 1984)的结尾:整个村子聚集在教堂里,活人和亡灵齐聚一堂。
他写道:“这个场景层层展开,唤醒了一些东西,而当这东西被唤醒之时,我忍不住泪如雨下。
这份感受是辽阔而深邃,它混合着人类统一的那种喜悦与光辉的承诺,以及现实中它尚未实现的悲伤。
”层层展开(dépli)、深邃、结合、觉醒——所有关键词都在这里了。
一种对存在之谜的广袤感受,既没有被简化,却又在其全部的矛盾之中获得了统一。
但仍有一丝微光,那种“已然(déjà)”的预兆,让我们在一切逆境中都仍愿意相信,共融是可能的,并且即将到来。
Places in the Heart(1984)全文完金色木屋:致敬大卫·林奇
本次大卫·林奇纪念展映活动由异见者编辑部联合杭州、北京、上海的高校电影社团发起,放映排期跨时三周,于三地同步进行。
放映属于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活动,并非版权放映;观影免费,并且向校外观众开放。
本次活动共安排了九场映后交流,其中部分为开放给场外观众的线上映后,具体嘉宾信息将择日公布。
每周还将配合当周的主题及展映片目,在本号平台上推出相应文字内容,包括单元导赏、原创电影评论、相关精选译文。
「波长cinema」播客也将会呈现特别策划节目。
同时,我们还为本次活动专门设计了有场刊、海报、票根、纪念小卡等周边,观众可以在现场免费领取。
展映片单内有部分影片是首次译介为中文,届时字幕也会同步发布。
*目前所有放映已圆满结束。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会陆续发布一些总结性质的推文,感谢大家的支持。
金色木屋 活动往期推文学术放映|金色木屋:致敬大卫·林奇金色木屋·导赏|放映大卫·林奇 WEEK 1:我回来作祟金色木屋 · 长评|论纯真和卑鄙:大卫·林奇《蓝丝绒》金色木屋 · 长评|物质的观感:大卫·林奇《橡皮头》金色木屋 · 导赏|放映大卫·林奇 WEEK 2:路直路弯金色木屋 · 访谈翻译|唯一的雪莉·李:《劳拉幽魂》访谈选文金色木屋 · 长评|另一种速度与归途:从阿尔文·史崔特到戴尔·库珀金色木屋 · 长评|肥皂剧与世界:大卫·林奇《双峰》系列金色木屋 · 导赏|放映大卫·林奇 WEEK 3:地图和坐标(以及更多)金色木屋 · 长评|从片场大门到电影院:大卫·林奇《内陆帝国》金色木屋 · 评论翻译|幻想的解体:齐泽克论大卫·林奇《妖夜慌踪》金色木屋 · 圆桌|关于《双峰》的那些档案金色木屋 · 长评|梦的六块拼图:大卫·林奇《穆赫兰道》金色木屋 · 长评|无尽的公路与泪痕:大卫·林奇《穆赫兰道》排版设计 / desi 封面设计 / 阿崽 责任编辑 / 石新雨
10 ) 人工智能时代的情动宣言
1.人工智能正在到来的时代,留给人类的还有什么,唯有情动。
2.情动,作为非表象性的思想样式,预设了观念,但非观念。
3.三种观念:情状、概念与本质。
从情状到本质,跳脱概念。
4.我们需要情状,不需要充分的观念。
思想不再有未来,唯有艺术。
5.描摹情状,不寻原因,不归其以概念。
从情状直接跃至本质(积极情动),一个纯粹强度的世界。
6.在小说,虚构不再有价值,这是概念的生产。
留给人类的是情状,是情绪、情感与情态,是普鲁斯特、奥兹和托宾。
7.在电影,是动作的消失,是完全的情境。
观众只能产生无法归于概念的情状,情动本身即是价值。
8.对存在之力流变的体验,是《利维坦》(2012)和《双峰》(2016)告诉我们的东西。
9.不再需要充分的思想样式,需要不从分、不完整、不可解等反理智的东西。
10.只有纯粹强度的流变,本质的世界。
一切彼此相合,上帝的至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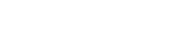


















































































时隔25年的回归,林奇以惊人想象力把当年《双峰》迷案剧情上升到如此高度,成为第一科幻神剧。他对梦境与现实相互影响的抽象诠释,让他在影史中第一造梦师地位不可动摇。固定镜头中的缓慢动作、缓缓推进的特写镜头,动与静之间表现出相对停滞的状态,静谧小镇被恐怖梦魇笼罩着;不同时空、相同情景的生活碎片细节混剪,时间缓慢的流逝,过去改变未来,我们想改变过去拯救未来。恶魔Bob和坏Cooper死后,叠化处理的好Cooper凝视自己、回忆过去、思考挽救,人生也是如此,我也想拥有机会找到入口努力完善自己。我们“与火同行”,摆脱邪恶的控制。校正:八倍镜。
说实话林奇是cult导演并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追求的高智慧生物,你们口中的装神弄鬼只不过林奇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已,至于你们懂不懂那就不关他和真正喜欢新双峰风格的人们的事了。(喝醉以后的评论,如有错别字以后更正)
十八小时时长的林奇盛宴,开吃。吃到半路发现此双峰非彼双峰,双峰不是双峰镇,而是红厅。观看途中,大量的空白有点让我恼怒,很多人老了也难以辨认,但是美人们的眼睛和声音都没有变。Audrey dance那一段鸡皮疙瘩起来了。最后一集确实挺骚瑞的。回头看最喜欢的还是FWWM与火同行
2017 No.1(?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看《双峰》后遗症:酷爱甜甜圈;可以对着墙上的插座发呆一整天;再也无法直视宜家买的猫头鹰玩具;看任何美女都毫无魅力。 “We are like the dreamers who dream and then lives inside the dream. ”
评论里居然还这么多捧臭脚的。rage quit.
【个人21世纪影史最佳】极善、极恶、以及它们的中间的混沌部分,由林奇为观众娓娓道来,最终我们被留在混沌中,导演退居幕后,四周充满了谜团,极善与极恶得到了各自的答案,而新的善恶又进入新的循环中周而复始,即便在一切终结之后,依旧像梦一样缠绕。【18.1.5-1.7 MoMA大银幕重温,发现还是部天才喜剧】
完全看不懂,可能是我智商不够,打个中性分数3分。林奇的大脑构造可能跟常人不一样。
电视剧这么拍很折磨观众。。。但风格变了一些,很多情节居然很搞笑。
这真的是大卫·林奇导的;之前都是Bob导的
加长版电影
真的比天线宝宝还要深奥难懂。大卫林奇是宇宙奇才
看剧看得累,很有WTF的感觉。然后看评论,发现很多人也看不懂,但竟然各个是5星,我就不懂了,拍个让人看不懂的电视剧,还就有成就了?还就有那么多捧臭脚的?
老头子是不是看过热海搜查官?!
大卫林奇拍剧,依然想象力炸裂,看了几集,刺激
把自己生涯的作品好好炖了一下。有些地方节奏还是该收敛一下
Cooper最后今夕是何年的疑问堪称punchline,这套神(秘主义)剧的结尾所需要的确实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我看了一下开播时记的简评,现在依然适用——坑更大了,洞更深了……
林奇这样的没挨枪子真是
not gonna lie, 看不懂. with Sam